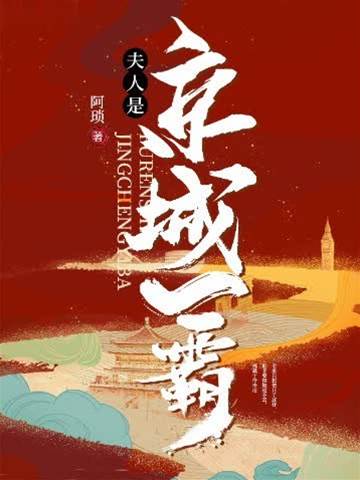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上京春事》 [上京春事] - 第66節
不曾防備你,本宮卻是有話要說。”
“所謂家族,便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脈,你真以為不用靠我,憑自己就能拿這李家大姓?”
“聖人疼寵我,故而也偏你,一旦我失勢,你以為你的下場會好到哪裏去?”
李景乾安靜地聽著,眼前莫名就浮現出沙場上逆著濺出三尺豔的場麵。
他殺過很多人,劍豁口了用刀,刀卷刃了用矛,每一場仗回去,自己都渾是。午夜夢回,他時常看見自己被圍在重重敵軍之中,一生路也無,窒息之從子夜一直蔓延到天亮。
饒是如此,第二日他依舊能衝頭陣,依舊長槍指天,為大盛打回來一張又一張的求和書。
大盛的山河,是用無數將士的骨鋪開去的。
但現在,眼前這個穿金戴銀的子說,他靠的是。
李景乾笑了一聲。
他說:“我還真好奇自己會以什麽樣的形狀死去。”
中宮愕然地看著他。
眼前這人不過剛要弱冠,上的氣息卻死氣沉沉,一雙眼不帶任何地看向的脖頸,指尖還微微了。
“……來人!來人!”中宮驚。
外頭的衛一腦地衝了進來,為首的廖統領卻在看見李景乾之後拱手:“侯爺?”
“娘娘心緒不穩。”他似笑非笑地道,“爾等可得好好守著才行。”
“是。”
他拂袖起,慢吞吞地道:“長姐,愚弟這便告辭了。”
皇後著扶手,臉上震驚未散,一時都忘了應聲。
李景乾倒也不在意,施施然轉就往外走。
七月驕當空,炙熱的落在他上也不見什麽溫度,陸安在一旁嘀嘀咕咕地與他說著朝事,他漠然地聽著,思緒卻開始飛遠。
方才那話不是衝著下人去的,是他的心裏話。
Advertisement
與別人都想著怎麽長生不同,李景乾時常會想到自己的死。他手上沾的鮮實在太多,料著自己的下場也不會太好。
在那之前,他想送鎮遠軍踏上東伐之路。
皇後說聖人沒有東伐之心,那他就努力讓他有。如果努力還是不行,那他就給自己找個最轟轟烈烈的死法。
五馬分,亦或是淩遲死。
他生來不凡,死也應當不平靜。
甚好。
路上的宮人像是被誰嚇著了一般,在前頭紛紛回避朝牆,就連邊聒噪不已的陸安也漸漸安靜,且刻意落後了他幾步。
他覺得奇怪,但也沒多問,一路出宮,去暗樁換了裳,再從仁善堂一路回寧府。
剛進東院,他就看見寧朝正在給花壇裏的紫蘇澆水。
才不會養藥材,那麽大一壺水澆下去,都要被泡壞了。
但從的另一側照過來,照得的側臉恬靜又溫。他站在門口怔怔地看著,一時沒有挪步。
察覺到門口有人,寧朝回頭,接著就是眉心一跳:“你怎麽了?”
第113章寧大人的藥方
江亦川對這反應有些莫名:“我怎麽了?”
不是好端端的嗎?
寧朝皺眉走近,緩緩抬手按上他的額角。
溫熱又的♪,瞬間將他一直繃著的筋給鬆了下來。
江亦川這才發現自己的緒不太對。
“無妨。”他住的手,垂眼道,“緩緩即可。”
向來要他主的寧大人,在看了他一會ᴶˢᴳᴮᴮ兒之後突然牽起了他的手。引著他進屋在榻邊坐下,又給他倒了杯熱茶。
“中宮為難你了?”問。
他搖頭。
這些緒每隔一段時日就會冒出來,中宮那一番話不過是因,真正的癥結在他自己。
見他不想說,寧朝便了一食指給他。
Advertisement
他茫然了一會兒,而後手握住的食指,乖乖地跟著起。
寧朝帶著他去沐浴,寬大的浴池裏,兩人一人一邊,中間隔了一道紗簾。
江亦川想不通這個紗簾是做什麽用的,但對麵那人沒說話,他也就沒。
沐浴之後,心裏似乎輕鬆了些,他抱扇帳,輕輕與送著涼風。
“時辰還早,我與你講個故事。”道。
江亦川嗯了一聲,不是很興趣,但的聲音很好聽,低低淺淺地道:“從前有一森林,裏麵住著很多小鹿,它們以花為食。”
“可是到冬天的時候,花就了,大家都腸轆轆,變得沮喪又絕。”
“這時一頭最快樂的小鹿出現了,它活蹦跳,給大家唱歌,給大家引路。”
“大家都很羨慕它,也很喜歡它。但是同行一段路程之後,這頭小鹿突然被大家揍了一頓。”
江亦川聽得愣住:“為何?”
寧朝一本正經地道:“因為它很早就找到了一片花穀,但沒有告訴其他的小鹿。”
江亦川沉默。
他開始思考這個故事是想告訴他人不能太自私,還是想教他要合群。
但是邊這人接著就道:“那頭快樂小鹿後來終於明白了,想要一直快樂,得有花就說。”
——有話就說,不要憋在心裏。
反正他們這個東院裏,什麽規矩也沒有。
江亦川呆滯地抬眼看。
寧朝與他對視,良久之後也有點不好意思:“是不是太直接了些?”
改小鹿嗦花好像更好,有花就嗦什麽的。
呆滯片刻之後,江亦川倏地笑了出來。
他手抱住的腰,額頭抵在的肩上,笑得整個榻都在抖。
朝惱了,狠狠地掐他一把:“我想半天呢,方才泡澡都一直在想。”
Advertisement
怪不得一直不說話。
心口溫,他抿問:“大人想知道什麽?”
“隨便。”掙紮了一下,見無法從他手臂間掙,便幹脆舒服地躺著,“說什麽都行。”
認真地想了一會兒,他低聲道:“我一直想不明白,殺人犯法,但沙場上殺人,為何卻是有功?”
寧朝拍了拍他的背:“因為弱強食,你不殺那些人,就會有更多的大盛子民死在別人手裏,所以你對別國來說有罪,對大盛來說就是有功。”
“那對我自己來說呢?”
朝低眸看他。
現在還記得當初的永昌門下定北侯是何等意氣風發,一將功萬骨枯,他這樣的元帥,竟也會心裏有愧嗎。
輕輕搖頭,道:“每個人都有自己該做的事,就算你不是武將而是文臣,也還是會有人唾罵你。不要妄圖去為所有人心裏的好人。”
“天下未平,所以需你提刀而起。待天下平時,你自可以卸甲焚香,告亡靈。”
“不要折磨自己。”
江亦川定定地看著,突然問:“你以前,也是這般安自己的?”
一頓,接著就撇:“我從來問心無愧。”
想達到自己的目的就得為之付出一些東西,隻要能得償所願,從不在意自己付出的是良知還是廉恥。
“不對。”他道,“你問心有愧,隻是不敢去想。”
“……”微微瞇眼,寧朝推開了他。
沒好氣地道:“我寬你,你反過來我心窩子?”
“沒有。”江亦川低笑,“我隻是覺得,你太豁得出去了,有時不做那麽絕,也未必不能事。”
說得輕巧。
寧朝冷哼。
場如戰場,不對別人絕,那就該別人對絕。
才不要為人魚。
翻背對著他,氣哼哼地扯了涼被裹。
Advertisement
這人欺上來,將整個人抱在懷裏,寬大的手掌上的頭頂,溫熱地挲了幾番。
意外地讓人覺得安心。
寧朝瞇眼看向遠貓窩裏打著嗬欠的貍奴,心想才沒那麽好馴服,隨便給人一腦袋就消氣。
但涼風拂,竟很快有了困意。
“程又雪們說,你那日在書房裏與青雲臺的人吵架,是因為看上了邊州的哪個小郎君,不想他做我側室。”迷糊地喃喃。
江亦川扇著扇子,哼聲問:“你信?”
“不信。”含糊地道,“你怎麽會看上小郎君,你看上的應該是……”
話漸漸沒在了平穩的呼吸聲裏。
他等了一會兒,沒好氣地道:“這時候倒睡得快了。”
懷裏的人雙眸平和地閉攏,雪白的鼻翼幾不可察地微微張合著。
手裏的扇子未歇,他埋頭抵在後頸上,略帶怨氣地道:“知道我看上的是誰,還總磋磨我,寧大人真是好生惡劣。”
說是這麽說,手卻抱著人不肯鬆。
他有很多個家,打仗的時候一天換一個帳篷,在上京裏也有將軍府和別院。
但,寧朝不會知道,他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家是給的。
他也不打算讓知道。
抵著慢慢閉上眼,江亦川很清楚隻要在邊睡著,自己就不會再陷被圍攻的噩夢之中。
他會有一個平靜且溫的夢鄉。
以前他總給開藥方,但後來江亦川發現,才是他的藥方。
他至今為止還是覺得婚是一件很沒有必要的事,麻煩且虛偽,熱鬧都是給旁人的,自己隻有疲憊。
可是,他想,如果著同心結另一頭的人是。
那還好的。
第114章打工人不容易
擴修中宮之事給了唐首輔,龐佑一邊憾,一邊在自己宅子裏擺了酒席,宴請親朋一起慶賀。
作為被定北侯一手保下來的人,龐佑很是懂規矩,開宴之前特意將賓客名單往後也那兒送了一份。
定北侯沉默地看了一會兒之後問他:“你跟翎閣的人不太?”
龐佑連連擺手:“那怎麽能呢,下雖然不才,卻也是清流世家子弟,翎閣那些狂妄不知禮數……”
瞧著侯爺的眼神越來越不對,他的聲音也跟著越來越小。
背後的陸安輕輕咳了一聲。
龐佑恍然,接著就道:“……卻更顯豪放不羈!下就算有心想結,也沒有路子,不知侯爺可否引見一二?”
定北侯不甚在意地抿:“有什麽好引見的,們不來倒也清淨。”
話是這麽說,著名單的手指卻是卷了卷紙角。
於是龐佑馬不停蹄地就往翎閣各位的府上送了數張請柬。
程又雪一接到就“哇”了一聲。
葉漸青站在隔壁的側門邊,對反應實在是無奈:“有什麽好哇的?”
“龐大人誒,祖上三代都是狀元,代代清流名門,他家的宴帖可難拿了,黑市上都賣二十兩銀子一張!”雙眼放,“我現在拿去賣,今年的租錢就都有著落了!”
眼角一,葉漸青道:“龐佑的請柬,你想拿去賣?”
“我倒是也想去。”程又雪
猜你喜歡
-
完結711 章

惜花芷
藏拙十五年,花芷原以為自己可以做一個最合格的世家千金安穩一輩子,可當花家大廈將傾,她不得不展露鋒芒出麵撐起這個風雨飄搖的家,拋頭露臉是常態,打馬飛奔也常有,過不去了甚至帶著弟妹背著棺材以絕戶相逼,不好惹的名聲傳遍京城,她做好了家族一朝反目戳她刀子的心理建設,也做好了孤獨終老的準備,獨獨沒想到會有人在出征前盔甲著身向她許終身!好稀奇,這世上竟然還有人敢娶她!?
132.4萬字8 211843 -
連載7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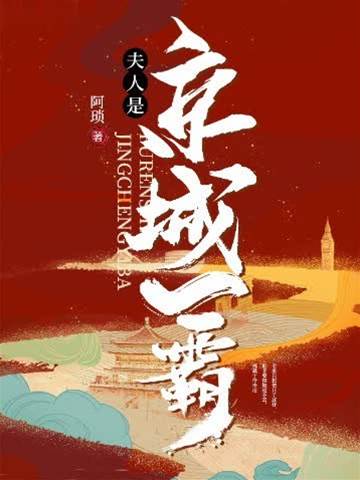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0.8萬字8 12111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9 -
完結123 章

我不做妾
沈瀾穿成了揚州瘦馬。 雲鬢花顏,瑰逸絕倫,當得起江南第一美人之稱。 正因這份美貌,她要被送去給巡鹽御史裴慎做妾。 沈瀾不願意做妾,千辛萬苦逃了出去。 陰錯陽差,成了裴慎的丫鬟。 對丫鬟這份工作,沈瀾尚算滿意。 雖然全年無休007,但薪俸極高,常有外快。 更讓她滿意的是裴慎快要成親了。 只等裴慎成婚後,她便能銷去奴籍,靠着自己積攢的人脈、錢財,快快樂樂過完這輩子。 就在她滿心歡喜,只等放良之時,忽然發現,裴慎想納她爲妾。 沈瀾:我不做妾。 * 裴慎三年前就想納沈瀾爲妾,只是因爲守孝不得已忍了三年。 越隱忍,越剋制,想得到她的心思就越強烈。 如今三年已過,將要成親,正是納妾的好時候。 * 裴慎一生順風順水,官路亨通,遇到沈瀾,才知道世間唯情愛二字,最是摧心折肝。
39.9萬字8 74912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1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