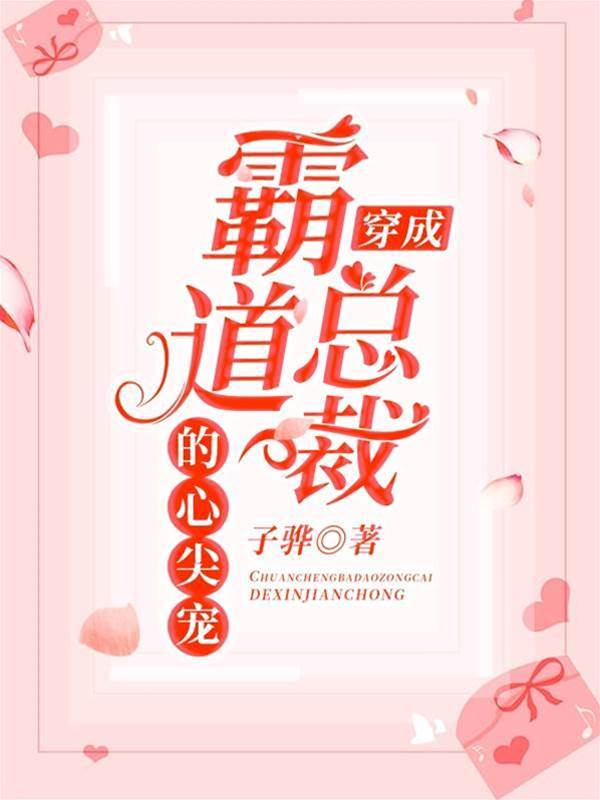《寵妃的演技大賞》 第58章 夫妻 朕這輩子,隻與你做夫妻。
風吹著綠葉簌簌作響,窗牖外紛的腳步聲來來回回。
景仁宮的太監宮們湊在角落裡眉飛舞。
小太監將手平攤於前,做了個抱人的姿勢,“聽說了嗎?”
“這等新鮮事,誰能不知道!”
小太監連連“嘖”了幾聲,道:“如今六局一司那幫人,看咱們景仁宮,眼神都變了。”
“可不是嗎?”
宮琥珀唏噓:“誰能想到皇上疼起人來竟是這般樣子。”
小太監又笑道:“如此恩寵,用不了多久,咱們就要改稱娘娘了……”
“那將來的日子倒是好過了。”宮翡翠幽幽道:“不過婕妤的子也忒冷清了,好像除了大皇子什麼都不在乎,便是跟竹蘭竹心兩個近伺候的姐姐,也不大敢與親近。”
另一人又道:“但婕妤可從沒虧待過咱們這些下人。”
“就是!咱們不過是做奴才的,能討到賞還有什麼不知足。”
們如何能想到,曾經的坤寧宮,日日語笑喧闐,皮點的奴才,偶爾還敢與皇后調侃兩句。
外面窸窸窣窣聲不斷,蕭韞的目從手中的千字文移向窗外,耳朵都快到窗紙上去了,似乎很像聽清外面在說什麼。
秦婈兩指一,輕輕提了下他的耳朵,蕭韞立馬回頭,秦婈用眼神示意他繼續背書。
蕭韞乖乖坐直,極輕地歎口氣。
書看了沒多大一會兒,蕭韞揚起臉,道:“阿娘。”
秦婈“嗯”了一聲,“又怎麼?”
蕭韞一本正經道:“我想如廁。”
又如廁。
秦婈忍不住了下角,“去吧。”
蕭韞屁一扭,短落地,跟著袁嬤嬤噠噠地走了出去,秦婈看著他歡快的背影,忍不住彎了眼睛。
到底是未滿四歲的孩子,玩本就是天。
Advertisement
以前也是如此,一學那些閨閣禮數就犯困,窗外有隻鳥都要仰頭看一眼,也只有蘇淮安帶去拍球、捶丸、投壺時,才能做到兩耳不聞窗外事。
秦婈來竹心道:“尚食局送碗冰過來。”記得,尚食局的冰做的極好。
竹心躬應是。
俄頃,蕭韞“如廁”回來,端起書,繼續默念:“……篤初誠,慎終宜令。榮業所基,籍甚無竟。學優登仕、學優登仕……攝職從政。存以甘棠,去而益詠,樂殊貴賤……”
念著念著,蕭韞打了個呵欠,黑黢黢的瞳仁泛起淚,朝秦婈眨了眨眼,似乎是忘了接下來。
秦婈道:“禮別尊卑。”
蕭韞重重點頭,又打了呵欠,“禮別尊卑。”
這廂正背著書,竹蘭推門而,端著食盒緩緩走了進來。
秦婈抬手刮了下他的鼻子道:“不念了,過來吃點東西。”
蕭韞立馬走了過去。
秦婈打開食盒,拿出一碗冰,舀了一杓,抵試了下溫度,然後遞到蕭韞邊,“有點涼,慢點吃。”
皇子的膳食都是由尚食局定好的,說起來,這冰他還是第一回 吃。
蕭韞一口飲下,蓮子的香味在口中蔓延浸,齒間還有微微冰麻,他的眼睛頓時一亮,困意全無。
“好吃嗎?”
蕭韞點頭。
秦婈笑道:“那也不能多吃。”
眼下天還沒熱起來,冰吃多了容易涼著,秦婈隻喂了他幾口,就將碗盞放置一旁,用帕子給他了。
蕭韞悄聲道:“阿娘。”
秦婈低下頭,蕭韞的上了的耳朵,也不知是說了甚有趣的話,還是小孩子溫熱的氣息磨得耳朵。
秦婈忍不住一躲,並發出了笑聲。
Advertisement
正是其樂融融時,門口突然傳來悉的低沉嗓音,“說什麼呢?”
秦婈心裡頓時“咯噔”一聲。
娘倆同時收起笑意,起。
蕭韞雙手疊,拱起,福禮道:“父皇萬安。”
秦婈屈膝道:“臣妾見過陛下。”
蕭聿襯金線日月紋白中單,外著玄蟠圓龍長袍,以玉冠束發,腰配素帶,下頷白皙乾淨,不見一烏青,顯然是剛剔了須,瞧著格外清雋雅正。
男人走來時腰間琮玨晃,他先扶起秦婈,而後了蕭韞的後腦杓。
蕭韞抬頭,眼中倒映著他最敬重的父皇。
蕭聿低頭與他對視,又道:“方才說什麼呢?”
小皇子指了指案上的碗盞,“兒臣與母妃用了冰。”
蕭聿隨著小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忽然想起以前就吃這些。
他下意識對秦婈道:“眼下天氣還涼,你子一向……”怕涼,吃些。
話還沒說完,空氣似乎都凝結了。
蘇後的子如何,同眼前人大概都無甚關系了。
正是尷尬時,小皇子把剩下的那碗冰捧過來,小心翼翼道:“父皇,要嘗嘗嗎?”
見此,一旁的竹心皺起眉頭。
忍不住腹誹:小皇子呦,皇上怎麼可能吃剩下的東西。
竹心正準備上前將冰收走,只見皇帝接過,竟是,全吃了。
蕭韞驚了一下,喃喃道:“母妃說,這不能多吃……”
說罷,他又去看秦婈。
秦婈答:“陛下與大皇子不同,多吃些也是沒事的。”
蕭韞不解道:“為何?”
秦婈想說因為他年紀大,但這話顯然不合規矩,於是到邊就變了,“因為大皇子年歲尚淺。”
這話,三歲過半的小皇子聽不出深意,但二十有七的蕭聿卻能。
Advertisement
蕭聿輕咳了一聲,話鋒一轉,開始問詢蕭韞的功課。
風景就是這麼煞沒的。
蕭韞老老實實地站在皇帝面前作答,垂於兩側的雙手握拳,過分張時,忍不住結兩回。
皇子在皇帝面前自然是想表現的,可越張越說不出,憋的他耳朵都紅了。
雖說秦婈看不得他冷著一張臉嚇唬孩子,但父問子功課,也確實不該置喙。
便無聲地歎了口氣。
然而就這輕飄飄的一口氣,歎的蕭聿太一跳,他至今也忘不了這孩子是怎麼生下來的。
蕭聿了他小小的肩膀,語氣和了不,“不錯,有長進。”
蕭韞的小臉瞬間紅了,喜悅之溢於言表。
——
夜幕沉沉,景仁宮四周燃起了燈。
袁嬤嬤將小皇子抱回暖和,殿只剩他們二人。
昨日之前,秦婈尚能笑著討好於他,當個恭順的妃嬪,眼下撕破了這層偽裝,真是都別扭,怎麼都不對勁。
這男之間關系總是十分微妙,空氣好像會說話,一個疏離抗拒,另一個定然覺的到。曾經親無間的夫妻尤甚。
蕭聿見眉間寫著抗拒,便主出手,攬過的腰,輕輕地挲了兩下。
兩人同時開了口——
秦婈道:“陛下今夜不用議事嗎?”
蕭聿道:“你好像瘦了。”
“今夜無事。”他也不管眼前人用不用他陪,垂下眸,低頭輕啄的鼻尖,看著的眼睛道:“我在這陪你。”
秦婈偏過頭,蕭聿的視線撲了空,目所及變了白皙纖細的頸。
男人的不由自主地落在上面,蹭了蹭,有些討好地意味,鼻息間的熱氣噴灑在頸間,格外燙人。
這回秦婈沒躲,但無甚反應,大有一種“任爾千磨萬擊,我自巋然不”的意思。
Advertisement
他們針鋒相對過,繾綣熱烈過,福禍相依過,並肩攜手過。
誤會、錯過、失、絕、生死、離別、後悔、思念,仿佛這世上所有熱烈的他們都經歷過。
初識至今,已近七年,他不是不清楚,他眼中的人眼中已無他。
可那又如何?又如何?
蕭聿握著的手道:“阿菱,你腹中無子,秦家也無功績,我不好直接封你為後,先提為昭儀可好?”
皇后,他也真敢想。
秦婈看著他道:“陛下就不能如之前那般待臣妾嗎?”
聞言,蕭聿蹙起了眉。
他的脾氣一向沒多好,知道。
蕭聿結一滾,一字一句道:“朕這輩子,隻與你做夫妻。”
他的手越來越,攥的秦婈有些疼。
說實在的,也不想惹他生氣,輕輕了口氣,聲道:“時候不早了,臣妾伺候陛下更吧。”
秦婈勾著他起,替他解素帶更,蕭聿頷首看著的無比練的作,怔怔出神,如同在看無數個回不去的日日夜夜。
秦婈將裳疊好,放置在矮幾上,踮起腳,抬頭替他拆卸玉冠。
但就是這樣平淡無奇的對視,蕭聿的眼眶莫名紅了,他低下頭,極輕地“嗬”了一聲,嗓子發,“我自己來吧。”
秦婈手腕一滯。
沐浴盥洗,同榻而眠,蕭聿還是給留了一盞燈。
燭火搖曳,闔眼之前,蕭聿低聲道:“過些日子,我帶你見個人。”
猜你喜歡
-
完結1340 章

梧凰在上
斬靈臺前,眾叛親離,被誣陷的鳳傾羽仙骨被剔,仙根被毀,一身涅盤之力盡數被姐姐所奪。寂滅山巔,她的未婚夫君當著她好姐姐的面,將變成廢人的她打進葬魂淵中。挺過神魂獻祭之苦,挨過毒火淬體之痛,人人厭棄的她卻成了淵底眾老怪們最寵愛的掌上珠,而她卻放棄了安逸生活,選擇了最艱難的復仇之路......
192.8萬字8 14941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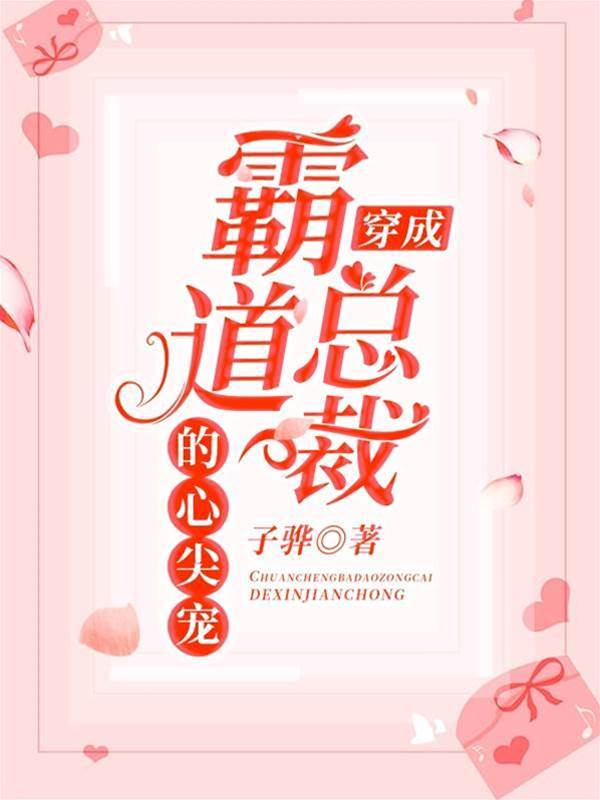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506 -
完結165 章

名門醫妃
韓雪晴穿越到古代,成為寧瑾華的王妃,安然病了,韓雪晴是唯一一個能救她的人,生的希望握在她的手里。不過慶幸的是她曾是一名現代的優秀外科醫生,是一個拿著手術刀混飯吃的她在這里一般的傷病都難不到她,只是這個世界不是那般平靜如水,有人在嫉妒她,有人想讓她死……
44.6萬字8 8253 -
完結179 章

病美人嬌養手冊
南楚攝政王顧宴容操持權柄,殘暴不仁,其兇名市井盛傳。 皇帝爲攝政王選妃之宴上,世家貴女皆人人自危,低眉斂目不願中選。 獨獨鎮國公府裏那位嬌養深閨的病弱幺女,意味不明地抬了抬眼。 謝青綰天生孱弱,卻偏生一副清幽流麗的美貌,怎麼瞧都是懨懨可憐的模樣。 顧宴容奉旨將人迎入了攝政王府,好生供養,卻待這病美人全然沒甚麼心思。 只是他日漸發覺,少女籠煙斂霧的眉眼漂亮,含櫻的脣瓣漂亮,連粉白瑩潤的十指都漂亮得不像話。 某日謝青綰正噙着櫻桃院裏納涼,一貫淡漠的攝政王卻神色晦暗地湊過來。 他連日來看她的目光越發奇怪了。 少女斜倚玉榻,閒閒搖着團扇,不明所以地咬破了那枚櫻桃。 男人意味不明的目光細密地爬過她溼紅的脣瓣,聲色暗啞:“甜麼?”
27.7萬字8.18 58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