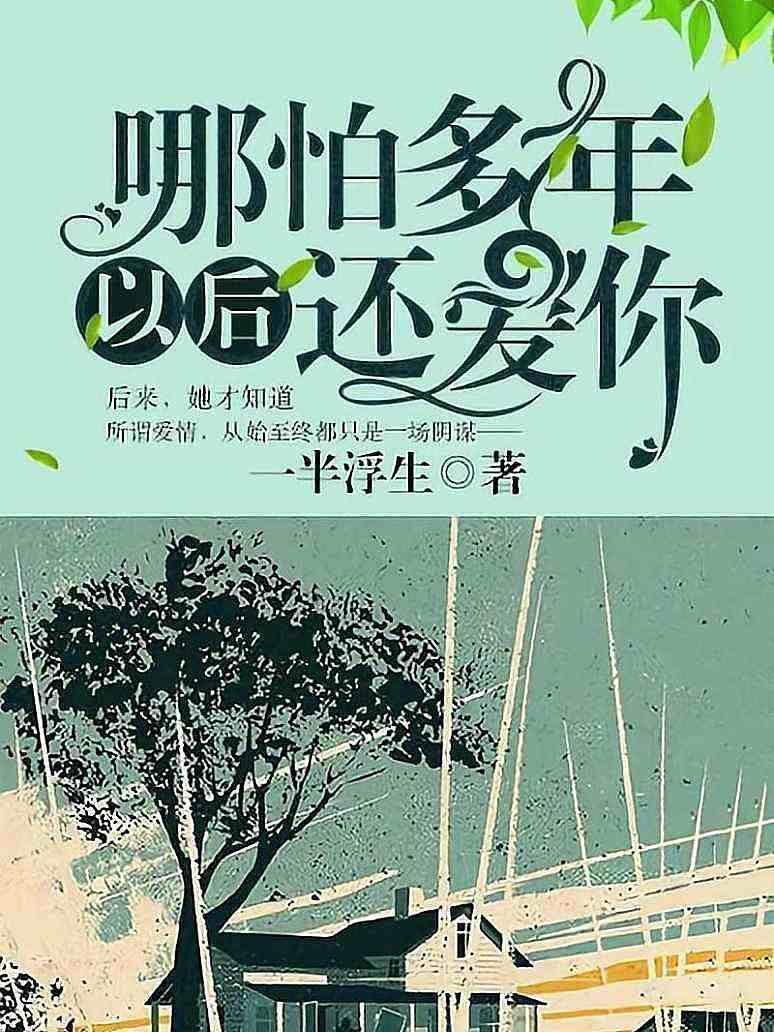《極致掌控》 第3章 我似乎又幫了虞小姐一次
江年宴手旁放著厚厚一摞文件,其中一份是攤開的。
他頭也沒抬,隻是淡淡問,“去哪?”
虞念坐在冷氣裏到無所適從,說了喬敏家的住址。
江年宴命司機開了車。
後麵那輛明顯是保鏢車,前車走了,後車不疾不徐跟上。
再後麵還有車子尾隨,狗仔們鍥而不舍的。
虞念下意識看了一下後視鏡。
江年宴的視線從文件上移開,掃了一眼。許開口,“老劉,叮囑一下後麵的車。”
“好的,宴。”司機老劉聽命,立馬撥了通電話,“有記者跟著,理一下,另外,宴不喜歡車牌號被拍。”
辦事幹脆利落,虞念看在眼裏,敏銳發現老劉把控方向盤的手有老繭,心知肚明了。
可不是簡單的司機,想來手了得。
許是常年跟著江年宴的,學得跟他一樣冷冰冰。
虞念心想,能比江年宴的手還厲害嗎?想當初遇上危險那次,他生生是一人挑了二十人沒在話下。
很快,尾隨的記者車不見了。
這期間江年宴始終在理文件,像是邊人不存在似的。
虞念坐在車上別提多別扭了,下意識看了邊的江年宴一眼。他靠著車座,右優雅地疊放在左上,攤著文件,抬手簽字時,襯衫上的袖扣閃耀一下。
微弱的亮落在他的眉骨之上,俊無儔。
“想說什麽?”冷不丁的,江年宴開口。
車子隔音效果極佳,就顯得車極其安靜。男人的嗓音淡而沉,不怒自威,可又在這種封閉的環境下出了奇的蠱。
虞念收回目,說了句,“今天謝謝你……宴。”
江年宴執筆的作微微一滯,再開口時有幾分嘲弄,“車都走出幾條街了才想起道謝嗎?”
“今天這種況,我是真心謝宴的。”
Advertisement
“謝字不必提。”江年宴麵又恢複如常,“畢竟我想要的也不是虞小姐的謝。”
虞念又想起他的三天之約。
臨近了。
虞念覺得不過氣,是那種悶到難,又心惶到不安,從未有過的不安。
“聽說……”
車子又行駛了一段路,開口。
江年宴頓筆,轉頭看。
司機老劉是個眼明心明的人,不聲地將隔音板升起。
頓時了隻有和他的封閉空間。
虞念對上他的目,問,“當時伍爺是接到了一通電話……”
這是喬敏之後打探出來的消息,說是伍爺剛開始沒想求宴出手,那麽高位置的人他哪能夠得到?
“當時伍爺一聽對方是江年宴本尊,嚇得都抖了。”喬敏將查到的事都跟虞念說了。
也別怪伍爺張,像是江年宴這種人向來都是通過別人的和手辦事,自己極麵,卻是一個電話直接打給他。
江年宴將文件一闔,“是我打的。”
虞念隻覺頭一忽悠,像是被人從後麵悶了一子似的。
他凝視,“有些閑事不該他管。”
“我們虞家到底欠了你什麽?”
曾經對那麽好的人,豁出命都要護周全的人怎麽就變了?
眼前這張臉的冰冷,就跟當年跟父親決絕時的一樣,令人不寒而栗。
江年宴的眉梢似有冷笑,“看來,虞冀遠什麽都沒跟你說,許是怕損了慈父的形象?”他頓了頓,再開口語氣森冷,“虞家欠我的,用十個你來填都填不滿。”
虞念頭皮一,“什麽?”
“不過,十個倒不必,一個你就夠了。”江年宴忽地湊近,似笑非笑,目順著的臉頰遊弋到的紅上,“你就當我見起意,想要你罷了。”
他得近,男冷冽的氣息席卷而來,的後背著後座,避不開。
Advertisement
都說他是無無的佛子,就連上氣息都不沾染一塵埃之氣,可虞念看得清楚,他眸底深有深沉而強烈的在湧,那就跟洪水,將人吞噬湮沒,而他自己卻始終能夠巋然不。
車子就在這時停了。
到地方了。
虞念唯一的念頭就是想下車,避開男人的氣息,剛要開車門,卻在瞧了一眼車窗後渾一僵。
車門就遲遲沒打開。
江年宴順著的視線看過去,見狀角微微一挑。
竟是江擇。
比他們先找到了喬敏這裏,停好車後就瞧見了江年宴的車,朝著這邊過來了。
虞念有一瞬的張。
可為什麽張自己都說不出來,不是做了虧心事的那個,本該大大方方走下車,順便踹上江擇一腳。
可下意識喃喃,“開車……”
“晚了。”江年宴嗓音慵懶,不疾不徐的。
本沒有避嫌的架勢。
於是,虞念就眼睜睜地看著江擇越走越近,直到車門前。
“叩叩叩”,敲了三下。
在車窗落下的瞬間,虞念條件發地扯過江年宴搭在一旁的西裝外套,猛地將頭一蒙。江年宴手順勢將往懷裏一拉,就結結實實地枕在了他的大上。
車窗微開,出了江年宴半張臉。
江擇驚訝,“小叔?還真是你啊,你怎麽來這了?”
說完順勢往車瞧了一眼。
車窗開得有限,地下車庫的線又不足,江擇就隻能約瞧個大概。
是個人躺在江年宴的上,連臉帶大半個子都被男人的西裝外套給蓋住了,隻出纖細的小。
小的弧線漂亮極了,皮也白皙得很,再往下就看不見了。
江年宴一手隔著外套搭在人上,語氣輕淡,“來送位朋友。”
“朋友?是……朋友?”江擇說著就想探頭往裏看。
Advertisement
被江年宴的眼神生生給回去了。
不敢再探究。
江擇在外界眼裏向來就是灑不羈又不服管教的,做事肆意而為,哪怕是自己的親爹都降不住他,唯獨江年宴。
他不敢得罪隻比他僅僅大了幾歲的江年宴,不是輩分問題,而是江澤懼怕江年宴周散發出的寒涼和人捉不的心思,像是靠近一座冰山,人不寒而栗。
“你是怎麽回事?”江年宴淡淡地問。
服下的虞念真是又急又悶的,怎麽還聊上了呢?
江擇一副畢恭畢敬的模樣,又有點臉麵掛不住,“我是來找念念的,今天這不是……鬧了點事嗎?我怕誤會。”
江年宴眼皮一抬,瞅了他一眼。
見狀江擇趕忙說,“哦,就是那位虞家千金,跟我有婚約的那位。”
“虞家千金?”江年宴搭在人上的手輕輕挲了兩下。
服下的虞念到男人掌心的力量,真是恨不得甩開他的手。
“小叔。”江擇支吾,“我聽到一件事……”
江年宴眼皮微抬,“想問什麽?”
一句話輕描淡寫卻不怒自威,江擇不敢問了,連連說沒什麽。
心想著,不會的,虞念又不認識小叔,怎麽可能貿貿然越過他去找小叔呢?就是謠傳。
“前陣子你父親發話了吧?關於你跟虞家千金訂婚的事,你是怎麽想的?”江年宴沒理會剛剛的話題。
虞念一僵。
“我……”江擇遲疑,“虞家現在這樣,父親的意思是不宜再聯婚了,我這邊……”
江年宴微微挑眉,眉眼就許肅穆了,“既然怕虞家千金誤會,說明你心裏還有,真是這樣不妨跟你父親說清楚。”
江擇,“心裏吧,肯定惦記著,畢竟……”
江年宴看向他。
他清清嗓子,笑得不自然,“畢竟沒得到,就總是人念念不忘。”
Advertisement
服下的虞念心如死灰。
許是江年宴也沒料到他會這麽照實了說,眼底劃過一淺愕,忽而就笑了,“原來啊。”
大手漸漸下移,似有似無地在人上拍了拍。
江擇見江年宴這麽笑,心裏沒底的,“小叔……”
“你過來。”
江擇走近。
江年宴手衝他示意了一下,江擇見狀就彎下來。
下一秒領帶就被江年宴給扯住,力道不小,江澤大半個臉都猛地在了車窗上,疼得齜牙咧連連求饒,“小、小叔……”
江年宴微微瞇眼,笑裏沁著寒,“我大哥怎麽能生你這麽個兒子?可真是江家的好大兒。”
江擇都不知道自己錯在哪了,隻能連連道歉。
“把你在外麵的那點爛事理明白,別給江家丟臉,聽見了嗎?”
江擇趕忙發誓,“放心小叔,我、我肯定能理明白,不、不會給江家惹事的。我就、就是一時間沒把持住,不重要,、就是個戲子而已。”
“走。”江年宴鬆了手,麵冷肅的,“別讓記者跟著你跑。”
江擇一聽這話,連喬敏家的門都不敢登了,忙不迭地開車離開。
“危機”算是解除。
虞念掀開上西服時才發現此時此刻兩人的姿勢有多曖昧。
幾乎是將臉埋在他的小腹上。
江年宴低頭凝視著,麵波瀾不驚。可虞念也不知道是不是車窗折的亮,他眸很沉,沉得能將人拖深淵的那種。
驀地起。
前麵的司機也不愧是江年宴的多年心腹,都不等下命令就將車門一開下了車,以煙為由稍稍遠離了車子。
瞬間車陷死寂。
虞念一時間呼吸不暢,江年宴倒是開口了,慵懶、涔涼,“我似乎又幫了虞小姐一次。”
虞念心說,這個忙也不是我要求你幫的吧?
但腹誹咽下,不想跟他牽扯太深,於是就說,“謝謝。”
話畢手要去開車門,跟著就聽“咯噔”一聲,車門上了鎖。
猜你喜歡
-
完結572 章

一吻成癮
那一夜,她大膽熱辣,纏綿過后,本以為兩人不會再有交集,卻在回國后再次重逢,而他的未婚妻,竟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姐姐!…
126.6萬字8 61855 -
完結73 章

過分偏愛
京州圈人人皆知,季家二少,薄情淡漠,不近女色。年初剛過24歲生日,卻是個實打實的母胎單身。圈中的風言風語越傳越兇,最后荒唐到竟說季忱是個Gay。公司上市之際,媒體問及此事。對此,季忱淡淡一笑,目光掃過不遠處佯裝鎮定的明薇。“有喜歡的人,正等她回心轉意。”語氣中盡是寵溺與無奈。-Amor發布季度新款高定,明薇作為設計師上臺,女人一襲白裙,莞爾而笑。記者捕風捉影,“明小姐,外界皆知您與季總關系不一般,對此您有何看法?”明薇面不改色:“季總高不可攀,都是謠言罷了。”不曾想當晚明薇回到家,進門便被男人攬住腰肢控在懷里,清冽的氣息占據她所有感官,薄唇落到她嘴角輕吻。明薇抵住他的胸膛,“季忱我們還在吵架!”季忱置若未聞,彎下腰將人抱起——“乖一點兒,以后只給你攀。” -小劇場-總裁辦公室新來一位秘書,身段婀娜,身上有股誘人的香水味。明薇翹起眉梢笑:“季總,那姑娘穿了事后清晨的香水。”季忱:“所以?” “你自己體會。”當晚,季忱噴著同款男香出現在明薇房間門前,衣襟大敞鎖骨半遮半掩,勾人的味道縈繞在她鼻尖。明薇不自覺撇開視線:“……狐貍精。” 【高奢品牌公司總裁x又美又颯設計師】 一句話簡介:悶騷一時爽,追妻火葬場。
19.6萬字8 20071 -
完結207 章
壞男強吻:契約甜心
她失戀了,到酒吧買醉後出來,卻誤把一輛私家車當作了的士。死皮賴臉地賴上車後,仰著頭跟陌生男人索吻。並問他吻得是否銷魂。翌日醒來,一個女人將一張百萬支票遞給她,她冷笑著將支票撕成粉碎,“你誤會了!是我嫖的他!這裏是五萬!算是我嫖了你BOSS的嫖資吧!”
41.3萬字8 38648 -
完結485 章

感化暴戾大佬失敗后,我被誘婚了
桑家大小姐桑淺淺十八歲那年,對沈寒御一見鐘情。“沈寒御,我喜歡你。”“可我不喜歡你。”沈寒御無情開口,字字鏗鏘,“現在不會,以后也不會。”大小姐一怒之下,打算教訓沈寒御。卻發現沈寒御未來可能是個暴戾殘忍的大佬,還會害得桑家家破人亡?桑淺淺麻溜滾了:大佬她喜歡不起,還是“死遁”為上策。沈寒御曾對桑淺淺憎厭有加,她走后,他卻癡念近乎瘋魔。遠遁他鄉的桑淺淺過得逍遙自在。某日突然聽聞,商界大佬沈寒御瘋批般挖了她的墓地,四處找她。桑淺淺心中警鈴大作,收拾東西就要跑路。結果拉開門,沈大佬黑著臉站在門外,咬...
87.4萬字8.18 30340 -
完結897 章

蝕骨囚婚
追逐段寒成多年,方元霜飛蛾撲火,最後粉身碎骨。不僅落了個善妒殺人的罪名,還失去了眾星捧月的身份。遠去三年,她受盡苦楚,失去了仰望他的資格。-可當她與他人訂婚,即將步入婚姻殿堂,段寒成卻幡然醒悟。他動用手段,強行用戒指套牢她的半生,占據了丈夫的身份。他畫地為牢,他與她都是這場婚姻的囚徒。
119萬字8.18 15407 -
完結2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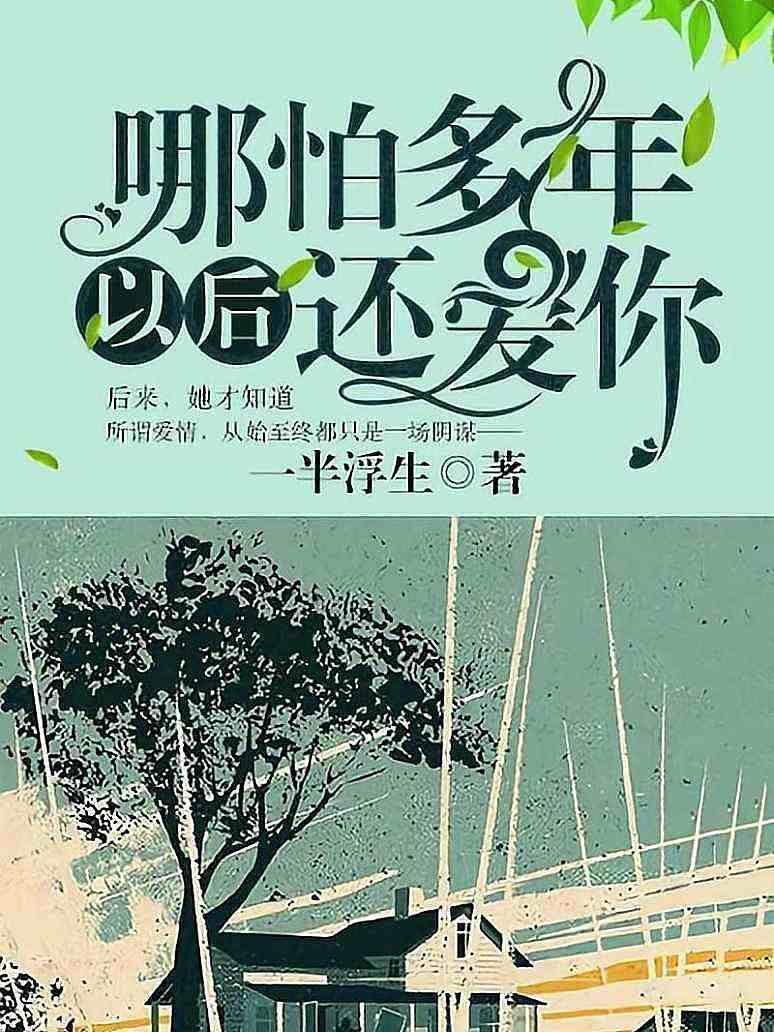
哪怕多年以后還愛你
“生意麼,和誰都是談。多少錢一次?”他點著煙漫不經心的問。 周合沒有抬頭,一本正經的說:“您救了我,我怎麼能讓您吃虧。” 他挑眉,興致盎然的看著她。 周合對上他的眼眸,誠懇的說:“以您這相貌,走哪兒都能飛上枝頭。我一窮二白,自然是不能玷污了您。” 她曾以為,他是照進她陰暗的人生里的陽光。直到最后,才知道,她所以為的愛情,從頭到尾,都只是一場陰謀。
107.8萬字8 35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