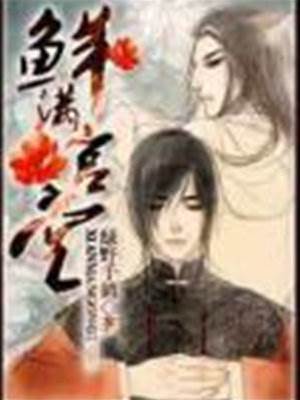《頂級掠食者》 第34頁
這些他比誰都清楚,那次忍不住央求瞿末予標記他,也是作祟、腦子糊塗了,瞿承塵的這段話,無疑是廢話。
沈岱的口氣已經極差:“你到底想說什麼,想幹什麼。”
“我可以幫你。”瞿承塵別有深意地凝視著沈岱,“幫你得到瞿末予的標記。”
沈岱自詡修養不錯,忍住了就要衝口而出的髒話,諷刺道:“我說了,去找跟你同量級的對手,何必自降段來消遣我。”
“我們還沒到正面鋒的時候,兵不厭詐嘛,誰他比我早生了八個月。”瞿承塵撇了撇,“區區八個月而已,他出生時還是祖上有,到了我出生,就是‘福兮禍所伏’了。”
“你們家的事,實在與我無關,你跟我說這些,就不怕我告訴瞿末予?”
“你會嗎?”瞿承塵依然掛著冰冷的笑,“你問問自己,難道我說的話你不心?就算你沒那個膽子,你也同樣沒膽子把今天的對話告訴瞿末予,他生多疑,會怎麼想你?”
沈岱狠狠瞪了瞿承塵一眼,一刻都不想多留,轉走了。
瞿承塵的手段看起來不磊落,但卻都直指要害,無論是利用尤柏悅,還是利用自己,都是為了打瞿末予,正如他說的,他們礙於緣關系、礙於家族和公眾的限制,不能正面鋒,所以就玩兒的,而他難以避免地被卷其中。
Advertisement
雖然瞿末予說過,瞿承塵有任何作都要告訴他,但是沈岱確實沒法說,因為“標記”這個話題太敏了,他本不敢在瞿末予面前提起,一旦說出口,就好像在覬覦什麼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畢竟,瞿末予“警告”過他。
同時他也很清楚,瞿承塵不會善罷甘休,他必須小心翼翼,在這場漩渦中保護好自己。
周五下午,沈岱接到了一個電話,是瞿末予的助理程若澤打來的,要為他安排他姥姥就醫的事,他在電話裡特意請求程若澤裝幫他忙的朋友,不要讓姥姥知道太多細節。
周六早上,程若澤帶著司機來接他們去醫院。
姥姥知道要換醫院和醫生,多有些張,沈岱一直安,但一路上憂心忡忡,從昨晚到現在,不管沈岱說什麼,都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
程若澤去辦理手續的時候,沈岱陪姥姥在休息區等待,見姥姥還是緒低落,就給找了個熊貓崽的視頻看,想逗逗。
姥姥勉強笑了一下。
“姥姥,你不要害怕呀,咱們有更好的醫院和更好的醫生,你的手肯定會特別功,這是好事兒啊,對不對。”
“我沒有害怕,我不得早點切了算了。”姥姥拍拍沈岱的手,“你不用擔心。”
Advertisement
“那你怎麼一直很不安的樣子。”沈岱調侃道,“這麼大的人了,還怕見醫生啊。”
姥姥輕歎一聲,看著沈岱,言又止,眼神稱得上哀怨。
“到底怎麼了?”沈岱的心也跟著忐忑起來。
“你爸昨天給我打了個電話。”姥姥像是扛不住了,快速地將這重負扔了出來。
沈岱的臉頓時沉了下去,他很想譏諷一句“他居然沒死”,但他不忍心,哪怕那個人已經不配稱為人子,但他知道,有幾個母親能真的放下自己的兒子,他倒吸一口氣,平複過快的心跳,悶聲說道:“他已經失蹤好幾年了。”
“嗯,但我心裡一直有種預,他早晚會回來的。”
沈岱咬牙道:“回來做什麼,混不下去了?家裡還有什麼能讓他騙的。”
姥姥紅了眼圈:“他沒說他在哪裡,也沒說他想幹什麼,就是說……說想媽媽了。”
沈岱的腔窒悶得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他知道,那是憎惡。
七年前,他正在準備畢業論文,同時在研究所實習,爭取人才計劃的名額,得到高薪職星舟集團稀土研究所的機會,那是每個稀土人都夢寐已求的發展。那時候的他,二十歲,績優異,前途無量,有他的姥姥和姥爺,有溫暖漂亮的家,對未來充滿了好的期。
Advertisement
可是這一切都被他的親生父親毀了。
那個自私的畜生,騙了家裡的所有財產去為男友做抵押,他們一夕之間失去了所有,還背負上巨額的債務,姥爺傷心至極,病倒了,不到半年就走了,一輩子生活優越的姥姥被迫搬到廉租公寓,往後所有的開支都由他的工資來承擔,房租、生活費、醫療費,得他難以息,如果那時候沒有老師的幫助,他不知道要怎麼熬過去。
最艱難的那幾年,沈岱不願意回憶。他邊有從非常貧苦的地方來的同學、同事,一樣在努力把生活過好,他並不覺得自己可憐,工作累、力大、貧窮,這些他都能承,接自己無法像正常人那樣結婚、組建家庭,也不難,他真正的、至深的痛苦來源於至親的背叛,以及看著最的人痛苦卻無能為力。
後來他漲了薪,還拿過項目獎金,生活有所改善,再後來,瞿末予戲劇化地從天而降,徹底把他拖出了泥沼。
他以為一切都會變好的,可為什麼那個罪魁禍首還要再出現?!
姥姥握住了沈岱的手,輕聲說:“阿岱,你不要生氣,我知道你不想見他,我不讓他回來,對我來說,他……他就算死了。”
Advertisement
沈岱反握住姥姥的手,細瘦的指骨,乾癟的皮,這是一雙蒼老的手,也是在無數個夜晚安他眠、為他做好熱騰騰的飯菜、給予他不求回報的扶持的手,他能真切地到,姥姥心中那從未愈合的傷痕,被撕扯得更大了。他鼻腔酸,心痛不止,他摟著姥姥的肩膀攬進懷中,他很想說一些寬的話,卻不知道該說什麼。
猜你喜歡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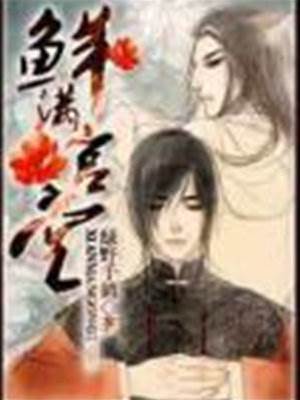
鮮滿宮堂
海鮮大廚莫名其妙穿到了古代, 說是出身貴族家大業大,家里最值錢的也就一頭灰毛驢…… 蘇譽無奈望天,為了養家糊口,只能重操舊業出去賣魚, 可皇家選妃不分男女,作為一個貴族破落戶還必須得參加…… 論題:論表演殺魚技能會不會被選中進宮 皇帝陛下甩甩尾巴:“喵嗚!”
35.5萬字8 7357 -
完結267 章

你確定要和我離婚?
溫少日常,懟天懟地懟老公 韓董寵溺三連,你行很好你說得對 溫少:……還能不能正經地吵架了? —————————— 以下為湊合著看的簡介: 飛揚跋扈的溫家大少要和大佬結婚了。 大佬顏好腿長賊有錢,可是他溫文曜就是看不上!奈何父母之命不可違,雞飛狗跳的同居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溫大少:姓韓的!你就是個泥腿子、暴發戶,配老子還差一點! 韓大佬:你說得對。 溫大少:姓韓的,你指望我愛你,還不如指望你家的母豬會上樹。 韓大佬:我家沒有母豬只有你。 溫大少:-_-|| 一年后。 “我男人真帥!演講的姿勢就是撩人!” “馬勒戈壁!.”溫大少示/威一樣地圈住那人的腰,下巴一揚,十分倨傲,“老子的人,再敢惦記一下試試?” PS:1、受前期有點渾,且看小狼狗如何被攻調 教成黏人小甜心; 2、帶感的雙總裁,強強對決,攻是創一代,受是富二代; 3、本文小說非現實,有夸張部分請勿較真啦; 4、可能有兩對cp。 沉穩深情套路王攻X叛逆炸毛偽紈绔受
42.6萬字8 7886 -
完結170 章

傅律師別虐了,溫醫生不要你了
【離經叛道狼崽子律師×爹係清冷美強慘醫生】【雙男主 雙潔 破鏡重圓 追妻火葬場 年下 虐戀 HE】提分手的時候,傅知越掐著溫楚淮的脖頸,譏諷他沒心沒肺,唯利是圖。“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惡心得想吐。”“溫楚淮,看著你現在這樣半死不活,你知道我有多痛快嗎?”看熱鬧的不在少數,“溫楚淮比傅知越還大,老男人有什麼好?”“溫楚淮這樣的人,就活該被唾棄一輩子,最後孤獨終老。”溫楚淮什麼也沒說,看著傅知越把所有的東西拿走,看著傅知越身邊有了溫順聽話的新人。可到了最後,跪在溫楚淮靈前的也是傅知越。“溫楚淮,我不跟你鬧了,你回來好不好?”
30萬字8.18 52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