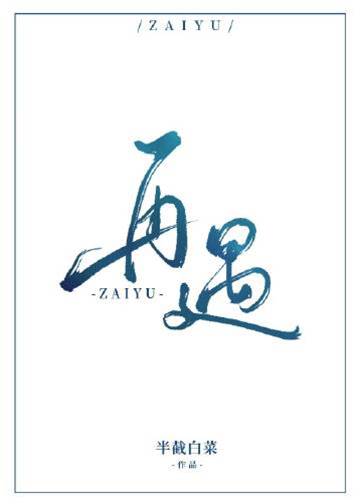《戀愛從結婚開始》 第75章 第七十五章
聽說隔壁間才是檔次最高的,只可惜有比這位客戶面子還大的人,提前一步。
在律所不比先前,宋婉月沒有像在談一時那樣,整日花費心思在打扮上去了。而是盡量讓自己看著些。
穿著上是下了功夫的,珍珠領面白襯衫,黑高腰魚尾長,一雙八公分的細高跟。妝容很淡,出門在外,化妝是基本禮儀。
今天這頓飯是地道的中餐,按國宴那套標準來的。
松鼠桂魚、文思豆腐、佛跳墻和東坡。更不用提這兒的招牌菜,北京烤鴨。
味道正宗的,地道的本地口味。
廚子應該也是花重金聘請來的,味道很不錯。就連宋婉月這個南方長大的也覺得好吃。
桌上酒過三巡,場子稍微熱絡起來。
這些大人也不知是否平日“走鋼索”習慣了,說起話來慣常三分留七分。宋婉月莫名想到了段柏庭,他也是這樣。
一番話說的迂回曲折,語氣和眉眼又寡淡如水,人猜不出他當下的
真實想法。難怪那些人背地里都說他城府深。
宋婉月以一個律師的角度來看,段柏庭若是在的對立方,完全沒有把握能打贏這場司。
畢竟這人算無策,輕易不會留下任何話柄。
宋婉月的走神被一道帶著笑的溫和問話給打斷,桌對面的男人看著五十有幾了,和宋婉月父親的年齡差不多。
此時笑著詢問: "聽說宋小姐是滬市人,那這北城本地菜可還吃的習慣?"
宋婉月沒想到大佬們談正事居然還會空關心自己一個小嘍啰。點了點頭: “吃的習慣,很好吃。”
笑容雖淺,但又帶著這個年齡段才有的真摯。男人有個兒,與同歲,所以笑容里更多些慈。
不過是見一人坐著,無聊到走神,所以就隨口問了句,讓不至于覺得自己被冷落了。roman笑道: "在這邊也快生活兩年了,該吃習慣了。"
Advertisement
湯是野生紅菇湯,最后端上來的。宋婉月意興闌珊,反而對這道軸湯品的興趣不大。
自從上次中醫把脈后,說氣有點虛,覃姨便常給做這個湯。起先覺得味道鮮,還喜歡。但再好吃的東西吃得多了也會膩。
見也不勺,男人笑了笑: "想來是喝不慣這湯。"宋婉月也笑,到底沒開口。
總不能直接說,是因為喝太多,喝膩了吧。未免有些過于凡爾寒了。
飯局上兩人聊了些公事,宋婉月在旁邊默默記錄著。其實委托說大也不大,但因為是私事,加上對方份特殊,所以不希被他人知道。
男人說著話,慢吞吞地點了煙。宋婉月被嗆到,偏過頭忍著咳嗽。
他朝書遞去一個眼神,書立馬也給roman點了一。
這煙沒牌子,外面是買不到的。男人笑了笑: "看,夠不夠烈。"
roman了一口,夾著煙也笑: "還行,不算很烈。"
男人撣了撣煙灰: "年紀大了,便不得太烈的。咳得厲害。"包廂雖大,可一張桌子就有好幾人煙,宋婉月覺得自己仿佛住進了煙囪里。
忍了忍,好歹沒說話。所以
說,工作確實能讓一個人的脾氣變好。
于是尋了個由頭,借故說去洗手間,想著出去會氣。才出包廂,外頭是條長廊,直走就能到出口。直通院子。
晚上的時候,院子里那個假山旁的小噴泉,被和燈一打,有種云霧繚繞的仙境。
宋婉月正要往那邊走,恰逢最前方的包廂門開了。
方才聽roman提過一,這個包廂是給頂級貴客留的。哪怕是他們接待的那位大人,也遠不夠格。
宋婉月還好奇是哪位貴客,定睛一瞧,男人拿著煙盒出來,里叼著一未來得及點燃的煙。闊而有質的黑西裝,金眼鏡,在這幽暗燈下,白皙皮泛著冷。
Advertisement
很多時候在看不清一個人的臉時,材和氣質基本就能決定一個人的基礎印象了。宋婉月不急著過去,看男人低下頭點煙。
燈太暗,瞧不清臉。廓有些悉,
這里的私好,隔音也做的不錯。當下除了屋外的風聲,幾乎聽不到任何雜音。所以打火機的砂聲,在這夜中格外明顯。
宋婉月純粹是出于欣賞的角度,將前面這個男人的背影由上而下,又由下而上打量了一遍。
長蜂腰,平直寬肩。
式西裝后背下擺是單開叉的,若若現的腰弧度。這屁,手一定很好。
宋婉月目停留了會,隨即瘋狂搖頭。自己已經是有夫之婦了,怎麼能盯著其他男人的屁看,簡直下流,對不起的庭庭!
深吸一口氣,剛要出去。或許是聽見了后的靜,走在前面,步履從容的男人回頭看了一眼。
宋婉月理所當然的和他對上視線。
男人角銜煙,眼神著幾分與這冬夜相映襯的薄涼。大約是酒過三巡,眼底幾分不太明顯的醉態。
但這個程度的醉,于他來說,顯然只算得上微醺。整個人是清醒的。
也是因為這幾分醉,讓他揭了平日的克制偽裝,氣低,面生寒。瞧著,就是個極難接近的人。
宋婉月卻并未被他的眼神嚇到,反而睜大了眼,愣了幾秒后,高興撲進男人懷里。“你怎麼在這兒。'
待看清懷中人的模樣后,男人眼底的緒瞬間便回暖了。語調卻也不見高
:“來這邊吃個飯。”
今早出門的時候,他便提前說過,今晚上有個飯局,會很晚回去,讓別等,先睡。他看了眼前方閉攏的包廂門,明知故問:“你呢。”
宋婉月洋洋得意:"有個很重要的案子,我是參與者之一。今天是過來談這個的。"將話說的模棱兩可,好像是代理律師一般。其實就是個負責打雜的。
Advertisement
段柏庭聞見上的煙味了,不是來自他手上這支。眉頭稍微皺了皺,又往前方包廂看了眼。
隨即將煙掐滅,抬手在側揮了揮,企圖早點將這味道給散開。笑聲淡,夸; "這麼厲害。"
“當然。”牛氣得很,但得瑟完,又想起什麼。不高興的從他懷里抬起頭, "你不是答應我要戒煙嗎?"
他沒狡辯,只說: “里面待久了憋悶,出來煙,氣。”
宋婉月埋怨起來: “我也是出來氣的。一包廂的人都在煙,我像個油煙機一樣,坐在那里吸二手煙。"
因為不大高興,所以說起話來兩腮一鼓一鼓的。像只儲滿食的倉鼠。
這兒道窄,怕擋到別人的路,段柏庭便牽著去了外面。正值冬日時節,晚上沒有蚊蟲,連聲蛙都聽不見。偶有風吹過,竹葉晃,發出簌簌聲響。
好在出來時記得穿一件外套,也不冷,見段柏庭一直盯著看。好奇手,在他面前揮了揮: “一直盯著我做什麼,喝醉了?”
“嗯,酒勁上來了。”他也不否認,明明那點酒對他來說好比喝水一般,他順勢低頭,氣音低沉,"有點想親你。"
他在距離一寸的地方停住了。兩人溫熱的鼻息纏在一塊,四周的氣溫仿佛都升高了不。
他在的包廂應該是焚了熏香,他上也沾染上一些,類似木的味道。淡中帶著清冷。
倒和他這個人的子有幾分合。
宋婉月讀懂了他的意思,笑了笑,踮腳去吻他。
點到為止的那種吻。吻一下,又離開,再湊上去吻一下,再離開。還故意吻出點聲音來。
"啵。"
"啵。
br />"啵。"
吻著吻著,他就笑了: "蹭我一口水。"
Advertisement
宋婉月的臉瞬間燥紅,見他上是有些盈盈水潤,但哪來的口水。
哼了一聲,那句“你講”還沒說出口,肩被按著,然后推靠在了墻上。
他彎腰低頭。
那個吻和宋婉月的完全相反。寂靜無聲,但深。
深到似要將舌頭都一同進的嚨里。
這兒雖然偏僻,但偶爾也會有人經過。宋婉月每次聽到聲音,心跳都會加速,擔心被發現。
好在段柏庭的量夠高夠大,完完全全將包裹在了自己的影子里。遮了個嚴嚴實實。
放在他腰上的手,攥著他的外套。
熨燙平整的西裝在掌心起了褶皺。
一正裝的男人,氣質清冷斂,瞧著就是一塵不染的高山白雪。此時卻做著這種事。
待段柏庭終于從的里離開,宋婉月氣吁吁的說: “我待會要去告狀,你工作中途溜號出來親人。"
他點點頭,甚至還善解人意的問: “需要我帶你進去嗎,正好都在。”
宋婉月被他問的啞了口,也就口嗨一下,怎麼可能真的去。不想繼續在這兒待著了,萬一他的酒還沒醒,又要繼續親呢。
親的那麼用力,又吸又咬的。的到現在還是麻的。宋婉月說:“我先回去了。”
上了臺階,朝走廊走,走至一半的時候,到出來的roman。側是那個男人,后面則是他的書和助理。
想來是談完了。
瞧見宋婉月,roman問;"去洗手間去了這麼久?"
宋婉月支支吾吾,從外面過來,洗手間在反方向,這下撒謊也沒得撒了。男人在一旁笑著打圓場: "小年輕坐不住,出去走走也正常。"
roman點點頭,也在笑: “工作期間溜號,下不為例啊。今天回去后記得把材料整理好,明天給我。"
一句話,讓在段柏庭面前連丟兩次臉。
用來指責段柏庭的言論,此時被上司用在了
上。剛才放出豪言,說自己是這次案子的參與者之一。
又被roman的后半句給拆穿。不過就是一個參與協助的小助理。抿了抿,抱著僥幸心理,興許段柏庭已經進去了呢。
結果一回頭,男人好整以暇抱臂靠墻,眼底淡淡笑意。
正看著。
宋婉月: ".…
猜你喜歡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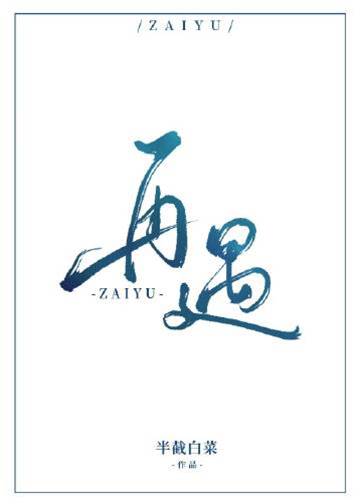
再遇
孟淺淺決定復讀,究竟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應浩。她也不知道。但是她成功考上了應浩所在的大學。一入學便得知,金融系應浩正跟金融系的系花談戀愛。-周喬曾說應浩不是良人,他花心,不會給她承諾以及未來。孟淺淺其實明白的,只是不愿意承認,如今親眼所見,所…
38.8萬字8 17739 -
完結1188 章

神秘狂妻燃翻天
全城人都知道蘇家三小姐腦子不好,身嬌體弱,反應愚鈍。最后竟成了京城人人敬畏的盛家小嬌妻!全城嘩然。蘇瑾一笑而過:黑科技大佬,奧賽全能,一級書法家……盛厲霆:我家丫頭還小,又單純,又可愛,你們不能欺負她。眾人跳腳,她小她弱她單純?她差點搗了我們的老窩,這筆賬怎麼算?
215.2萬字8 42608 -
完結86 章

櫻桃沙冰
作爲新人演員,顏漫入圈的第一個月就名聲大振—— 只因她在倒追的,是當紅頂流葉凜。 但所有粉絲都知道,葉凜一張神顏,淡漠高傲,是無慾無求的神,多年來從未下凡,拒絕一切緋聞。 因此當二人的詞條首度出現,羣情激昂。 CP黑粉:【滾吶!狗都不嗑!】 劇組殺青那天,顏漫決定放棄倒追,跟他解綁。 她連夜學習剪輯,剪出個驚天地泣鬼神的BE視頻,宣告二人徹底結束。 沒人想到,視頻火了。 第一天有人扒出,顏漫嫌熱脫大衣的時候,葉凜心跳135; 第二天有人發現,本該是女主強吻、男主躲避的鏡頭,花絮裏,葉凜居然迴應了…… 第三天,第四天…… 顏漫“初戀”結束的第一週,顏葉CP紅了。 CP粉:【這還不嗑?我嗑拉了呀!】 視頻的熱度過去,二人CP的熱度卻不降反增,無數照片爆出,“售後糖”管飽。 媒體懷疑一切都由顏漫策劃,對此,顏漫避嫌三連:不知道,不清楚,不認識。 當晚,葉凜微博迴應:【別亂猜,我發的,糖甜嗎。】 熱評第一:連澄清也要跟老婆工整對仗嗎!正主塞糖最爲致命! 再後來,顏漫憑實力,人氣一路飛漲,躋身一線小花。 大家發現拒坐飛機的葉凜,從中國到悉尼,近十小時飛機,只爲抓出和昔日男同學跳舞的顏漫,扔進了車裏。 兩小時後顏漫才被從車內放出,眼尾燒紅,大夏天還戴上了圍巾。 她氣憤地一腳踢上車門,男人卻從車窗內探出身,噙笑揉了揉她通紅的耳垂。
37.6萬字8.18 23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