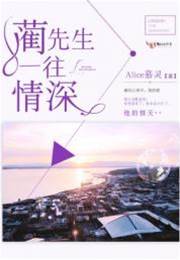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今日宜分手》 第11章 吃癟
上信,不得不說,真的是一個怨種朋友。
他也不知道自己上輩子是造了什麽孽,這輩子要跟汪斯年當發小哥們兒。
前一天晚上才從江城把人接回來,說給他安排腸胃鏡檢查,結果第二天在醫院等了半天都沒等到人。
打電話,電話不接,發信息,信息不回。
問管家,管家也不知道汪大爺到底去哪裏了!
管他的,來不來。
上信在醫院oncall36小時之後,終於躺到了家裏的床上。
結果,三更半夜,夜半好夢的時候,接到酒吧服務生的電話。
“你好,先生,我們這裏有位汪先生喝醉了,您能來接一下他嗎?我們酒吧馬上就要打烊了。”
上信一聽到姓“汪”的都有點條件反。立馬清醒過來。
“發個地址給我,我馬上過來。”
上信一邊穿服,一邊思考,這次江婉給的刺激太大了?已經這麽久了,還有效果?
從前那些人還嘲笑江婉是腦,上信覺得再這麽下去,可能要上山挖野菜的是汪斯年了。
汪斯年自從前年公司步正軌之後,在江婉的嚴格管控之下,除非必要的應酬,其實已經很喝酒了。
汪家人還以為是張媽的功勞,年底還給那個老媽子多發了獎金,來年還漲了薪。
結果江婉這一走了之,汪斯年的在他自己的作踐下,就沒有好過。
吃飯都吃到吐了,居然還敢去喝酒!
簡直是不要命了!
上信開車找到酒吧,下車之後走進去,就看見吧臺上趴著的汪斯年,果然是爛醉如泥!
“嘖,真是有生之年係列啊!”
他上前去推了推汪斯年,汪斯年迷迷糊糊睜開眼:“?”
看見麵前的是上信,又把眼睛閉上了。
這態度都要把上信氣笑了!於是他拿出手機,哢哢拍了好幾張照片,各個角度都拍了一張,然後才心滿意足的收起來。
Advertisement
上信上前去扶汪斯年,結果一個沒扶住,汪斯年躺地上了。
“這到底是喝了多啊?”
旁邊的服務生上前和他一起拉汪斯年,說道:“喝得多的,都是烈酒,我們都勸這位先生喝一點,畢竟這再好的酒也經不住他這樣喝。他喝醉了之後就開始哭,然後他一直讓我們幫忙打電話,但是電話那頭本就沒人接。”
服務生也十分無奈。
汪斯年因為江婉不接電話,抱著酒瓶,一邊哭一邊使勁喝酒。
後來汪斯年拿出自己的手機解鎖,然後又讓服務生幫忙打電話。服務生又打了幾次江婉的電話,也沒有人接,於是果斷選了一個最近聯係人的電話打了過去,這個怨種聯係人就是上信。
上信看著躺在地上的嗚嗚哭地汪斯年,真的是一個頭兩個大。
遇見你真是我的福氣。
上信幫忙結了帳,還開了發票,免得到時候汪斯年不認賬。
喊了兩個服務生幫忙,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發酒瘋的汪斯年搬上車。
今天的汪斯年,是真的醉了,還沒上車就“哇”的一聲吐了出來,上信看得一臉嫌棄。
服務生已經走了,上信隻好讓汪斯年坐在地上,靠著車,等著他吐完,他可不想讓自己的車遭嘔吐的襲擊。
上信點了一煙,看著汪斯年在一邊“哇哇”吐,他一點都不同他。
說實話,上信還是第一次看到這個樣子的汪斯年,以前在一起玩的時候,也不是沒有喝醉過,但是喝醉了之後哭這個鬼樣子,還是第一次見。
從前,汪斯年喝多了,有江婉來接,回家了還有江婉給喂醒酒茶,還有江婉給他子,第二天早上還有養胃的小米粥可以喝。
現在,連個人的電話都打不通。
Advertisement
風水流轉啊!
汪斯年吐完之後,有些清醒了。
扶著車站起來,掏出手機,遞給上信:“給打電話!”
上信彈彈煙灰:“不會接的。”
“我不管,你給打!”一個醉鬼,氣勢還大。
上信忍住了想打人的衝:“你不會還在指回頭吧?”
汪斯年眼眶發紅,瞪著上信:“給、、打、電、話!”
上信癟癟,掏出自己的手機:“算了,你的電話不會接的,我拿我的手機打。”
上信打過去也是沒有人接的,他自言自語地說道:“會不會是換電話了?”
汪斯年撲到上信邊,裏還不依不饒地說著:“打電話!”
“我在打。你邊上去點!”
上信知道江婉在江城開了工作室,所以找了點江城的朋友幫忙,弄到了江婉的新電話號碼。
淩晨四點半,有人打電話來,江婉還是有點意外。
接通電話之後,那邊報上名字之後,就更是意外了。
“你好,我是上信。”
“哦,有什麽事嗎?”
“不好意思,江小姐,這麽晚打擾你。”
“不晚了,天快亮了。”
電話那頭頓了頓:“不好意思,這麽早打擾你。”
“……”
江婉剛畫完圖準備睡一會兒,就接到了上信的電話。
對上信的印象還可以,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跟唐浙源和謝遊那樣的人對比,上信算得上是個好人了。從來也不喊的外號,也沒有拿開玩笑,對算是尊重。
“有什麽事?”
江婉不知道他從哪裏搞到的新電話號碼的,上信打電話來,也隻能是因為汪斯年了,於是再次問道。
上信拿著手機,打開免提,放在他和汪斯年之間。
上信說道:“汪斯年他喝多了,想給你打個電話。”
Advertisement
江婉了有些幹的眼睛,冷漠地說道:“嗯,還有事嗎?沒事的話,我就掛了。”
“江小姐,你先別掛……”
“我們已經分手了。”
上信看了一邊要死不活的汪斯年,繼續說道:“江小姐,我知道你們已經分手了,我知道的。但是你知道的,他很固執,又哭又鬧,要死要活,就要給你打電話,我也沒有辦法。”
上信的聲音低了下去:“你知道的,我們家得罪不起他們家。”
電話那頭,傳來一聲歎息。
汪斯年剛想要說什麽,卻被上信捂住了,隻能眼地看著上信。
“你把電話給他,我跟他說。”
汪斯年立刻掙了上信的控製,從他手裏把手機搶過來。
“!”
汪斯年有些雀躍,但是嚨卻有些發酸。
這一次,他又聽到江婉的聲音,不是在夢裏。
看來苦計還是有用的。
“汪斯年。”
江婉隻是簡單地了一聲他的名字,汪斯年的眼淚立刻掉了下來,此刻的他異常的脆弱。
上信在旁邊看得有些不忍。
“,我好想你……”
“汪斯年,你喝醉了。”
“我沒有喝醉,。我隻是好想你。”
“回家吧。”
“,我真的好想你。我想我們一起吃飯,一起睡覺,一起出去玩的時候,以後不能了嗎?”
“……”
“,以後都不可以了嗎?”
上信走開了兩三步的距離,又點燃了一隻煙。他看著汪斯年的眼淚就跟不要錢一樣流,哪裏有霸道總裁的模樣。
就像是一隻純小狗被主人拋棄了一樣。
江婉淡淡地說:“汪斯年,該說的,我都說過了。”
“我錯了,我不想分手。”汪斯年了眼淚,聲音有些哽咽。
汪斯年很害怕江婉掛電話,他這幾天不知道打了多電話,發了多信息給,都沒有回應。後知後覺才發現江婉可能換電話了,拋棄了用過很多年的電話號碼,社賬號那些,一點都沒有留。
Advertisement
就像不要他了一樣,不帶一點留。
電話那頭的江婉沒有說話。
“,你可不可以再給我一次機會?我哪裏做得不好,你跟我說,我保證我都改,你不喜歡我哪裏,我都改,你回來好不好?我們結婚,我們去環球旅行,我們換個帶花園的大房子,種很多你喜歡的花花草草,你回來好不好?”
汪斯年抓著手機,哽咽著哭訴著:“,我們為什麽會走到現在這個地步……我們明明好好的,你回來好不好?”
“我好想你啊!”
電話那頭的江婉還是一言不發。
電話顯示還在通話中,江婉沒有掛斷電話,還在聽他講。
一直都是那麽溫的人,連推銷電話都會禮貌回複。
“,求求你,不要不理我,好嗎?”
江婉幽幽問道:“汪斯年,分手了,會這麽難過的嗎?”
汪斯年不知道怎麽回答這個問題。
他心痛得要死。
江婉拿著電話,看著自己電腦裏麵的圖紙,淚水模糊了眼眶。
在決定分手之前,難過不知道多次。
難過不比汪斯年現在。
最後哭到麻木了,放棄了,也就不難過了。
一個人的心死了,又怎麽會再次難過呢?再想起從前,也是覺得自己傻而已。
如果汪斯年早知道會這麽難過,他還會在當初冷落嗎?還會任由他的朋友欺負嗎?還會任由張媽欺負,不聞不問嗎?
江婉說——
“今天什麽時候回家?”
“能不能早點回來?”
“斯年,你是在忙嗎?”
“能不能回我一下消息?”
“斯年,你記不記得今天是什麽日子……”
“怎麽出差都不跟我說一聲啊?什麽時候回來啊?”
汪斯年愣住了,江婉卻繼續說道——
“在忙。”
“沒事不要給我打電話。”
“該睡覺就睡覺,等我幹什麽?”
“沒回呢消息,就是在忙。”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近多忙?”
“有什麽事明天再說可以嗎?”
“我很累了!”
汪斯年聽到現在才明白,江婉在說些什麽。
這些都是當初兩個人的對話。
汪斯年閉了閉眼,心髒好像被一隻手住了一樣,痛得無法呼吸。
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麽,他能說什麽?
他一點都不敢去想,那個時候的江婉是怎麽度過的。他才這麽幾天,都已經難過這個樣子了。
那個時候被他冷落的江婉,一定更難過吧!
那個時候江婉很黏他,每天都要發好多消息,那個時候他的回複都很敷衍。
後來越來越不耐煩。
他的回答都是“哦”,“嗯”,“好”,“行”,“啊”。比AI都還要敷衍。
越是敷衍,江婉就越是黏得。
後來有些不需要他出差的公司項目,汪斯年也要一定要親自去,就像是為了得到自由一樣。外麵的空氣仿佛都要清新一些。
汪斯年拿出自己的手機,翻到他和江婉的聊天記錄,越翻越是心驚,手抖到都拿不穩手機,他怎麽敢的啊……
“對不起,,都是我的錯,你原諒我好不好?”
汪斯年隻能不停地道歉,說著自己的不是。
好像除了道歉,他說什麽都沒用,但好像說了也沒有用。
“不好。”
江婉掛掉了電話。
看了看手機裏的時間,已經六點了,天已經蒙蒙亮了。
江婉關掉電腦,躺在床上,閉上眼睛,沒有什麽緒起伏,沉沉睡去。
那些有緒起伏的日日夜夜,都熬過來了。
今後,也不會有什麽更難過的事了!
亦舒在《癡司》寫道過:隻不過是失,並非世界末日,原來那樣流淚的也會過去。
汪斯年呆呆愣愣地坐在後座上,上信開著車送他回家。
看著臉慘白的汪斯年,又被江婉了一遍,上信想著就覺得有些好笑。
這位天之驕子哦,終於吃到了的苦了哦~
上信打開了電臺,放起了歌來:“唉喲唉喲唉喲唉喲唉喲,你說你說我們要不要在一起,的日子裏,生活的不費力氣,傻傻看你,隻要和你在一起,唉喲唉喲唉喲唉喲唉喲,你說你說我們要不要在一起……”
歌詞還應景的。
汪斯年越聽越煩:“你能不能換一首歌?”
“汪爺說換,我們就換。”上信手點了一下切換。
“下的泡沫,是彩的,就像被騙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麽對錯,你的謊言,其餘你還我……”
這歌才放了一個開頭,汪斯年就更煩躁了。
“不放歌了,行不行?”
“行!”
上信十分遷就這位失的爺,畢竟今晚發生的事,他算是開了眼界。
讓上信想起來小時候看過的一部電視劇的一句話:“我知道他你的好痛苦好痛苦,我也知道你他的好痛苦好痛苦。”
他不知道能有多痛苦,但是看到汪斯年這個樣子,他覺得不也很好。
“下車吧!爺。”
上信下車,還十分心地打開車門,卻看到汪斯年一不。
上信湊到他的耳邊說道:“江婉在家裏等你呢!”
“我不信。”
喲,還醒著?!
“江小姐,你好啊……”
汪斯年想都沒想,連滾帶爬下了車,沒有看到任何的人影,他又失地坐回車裏。就好像上信的車裏很有安全一樣。
上信見狀:“喂!汪斯年,你不是想賴在我車上吧?我跟你講,你賴在我車上也沒有用,江婉已經把我拉黑了,你別想著拿我的手機打電話了。”
一點同心都沒有。
“把電話給我。”汪斯年說了一句。
“我發你手機上了,快下車吧,大哥,我晚上還要去醫院值班。你讓我回家睡會兒,行嗎?”
汪斯年蔫兒蔫兒的下了車,上信已經喊了管家李叔來接人了。
等王斯年睡醒了,已經是晚上七點的事了。
他癱在床上,頭也痛,肚子也痛。
昨晚喝了那麽多,也沒有醉得斷片,所有的事都記得十分清楚,他寧願不要記得這麽清楚。
“啊……”
“嗬嗬……”
江婉今日的冷漠,就是他往日的冷落造的惡果。
以彼之道,還施彼。
不過,他汪斯年是這麽容易放棄的人嗎?
猜你喜歡
-
連載1164 章
穿到跟殘疾大佬離婚前
遲清洛穿進一本狗血小說,成了商界殘疾大佬作天作地的小嬌妻。小嬌妻驕縱任性,飛揚跋扈,還紅杏出牆。遲清洛穿來當天,原主正因為爬了娛樂圈太子爺的床上了熱搜。大佬丈夫終於同意跟她離婚。遲清洛:“老公我愛你,之前跟你提離婚是我一時糊塗。”輪椅上的大佬眸色深沉:“你糊塗了很多次。”不不,從今開始,她要改邪歸正,渣女回頭金不換。可是漸漸的大佬好像變得不一樣了,對她說抱就抱,說親就親。嗯?大佬不是淡薄情愛,隻把她當擺設的麼?遲清洛眨眨眼:“好像有哪裡不對。”大佬將小嬌妻圈入懷中,指腹摩擦著她的唇珠,聲音嘶啞:“哪裡不對?”
104.7萬字8 56344 -
完結845 章

寵婚入骨
許家多年前送去鄉下養病的女兒許呦呦回來了,回來履行與林家的婚約婚禮前夕新郎逃婚去國外找他的白月光,眾人:哇哦……【吃瓜表情】許呦呦:哦豁。下一秒,白皙細軟的小手攥住男人的衣袖,甜糯糯的語調:“墨先生,您可以娶我嗎?”……墨深白商業巨擘清心寡欲,神秘低調,在波雲詭譎的商場叱吒十年,無一家報刊雜誌敢刊登他的一張照片,也沒有一個異性能讓他多看一眼。所有人都說墨深白娶許呦呦一定是協議婚姻,一年後絕對離婚。許呦呦津津有味的吃著自己的瓜,只是吃著吃著就發現好像不對勁啊。逛街購物不需要買單,吃飯不用點餐,不管走到哪里大家熱情跟她打招呼:墨太太好。後來墨深白的白月光回來了,前未婚夫深情表白:“呦呦,只有我是真的愛你,回我身邊,我不嫌棄你。”許呦呦還沒來得及回答被男人霸道的攬入懷中,低音性感撩人:“寶貝,你沒告訴他,這裡有了我們愛的結晶。”溫熱的大掌貼在她平坦的小腹上。許呦呦紅了臉,渣男紅了眼……【無腦瑪麗蘇先婚後愛文|專注虐男二】
142.9萬字8.18 230629 -
完結11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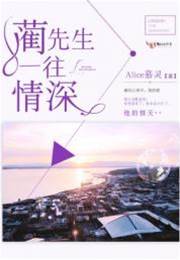
藺先生一往情深
曾有記者舉著話筒追問C市首富藺先生:“您在商界成就無數,時至今日,若論最感欣慰的,是什麼?” 被眾人簇擁,清俊尊貴的男子頓步,平日冷冽的眸難得微染溫色,回答:“失而複得。” - 人人都說她死了,藺先生心裡有一個名字,彆人不能提。 他走她走過的路,吃她喜歡吃的食物,人前風光無限,內心晦暗成疾。 情天眉眼寂淡:有些愛死了,就永遠不在了。 他眼眸卻儘是溫然笑意:沒關係,沒關係。 她的心再冷,他捂暖。 世人隻知商場中藺先生殺伐決斷手法冷酷,卻從不知,他能將一個人寵到那樣的地步。 - 但後來 人來人往的步行街頭,商賈首富藺先生仿若失魂之人,攔著過往行人一遍遍問—— “你們有冇有看到我的情天……” 他的情天,他的晴天。 · ·寵文·
138.8萬字8 78908 -
完結855 章

報告總裁,你老婆又跑了
黑暗中,他鉗住她的下巴,“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她自輕自賤“知道名字又如何?你只要一分不少的把錢打到我卡上就行了。” 本以為拿到錢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當一切沒有發生。 誰知那古怪男人從此卻陰魂不散的纏住了她。
167.7萬字8 38206 -
連載176 章

軍婚撩人:首長大人請深吻
她代替姐姐嫁給了那個據說身有隱疾的年輕軍長。他的寵,他的溫柔霸道,讓她毫無抵抗的臣服。卻原來爾婚我詐,不過是一段遠的要命的愛情。幾年後,她攜子歸來,撩撥的他欲火焚身。他反身把她壓在辦公桌上,“老婆,按照一夜七次的頻率來算,你已經欠我很多了,要不咱們還是先還債吧!”
30.5萬字8 263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