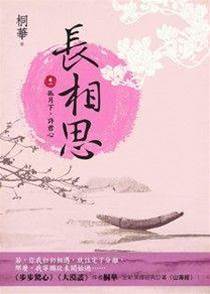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賜卿良辰》 第57章 你是我的了
沈連翹呆住了。
是!私闖東家臥房,是的不對。穿東家的服,也是自己的錯。可是,怎麽能解釋清楚自己不是有什麽特殊的癖好呢?
最重要的,怎麽讓孔佑明白,這服上鼓鼓的東西,是為了他好呢?
“東,東家……奴家……我,這個……”
結結,幹脆下中,拉出裏麵的銀盒,給孔佑看。
“這個是金瘡藥,我給你的,厲害吧?”
孔佑仍舊站在屋門口,這屋子裏點著的燈太多了,讓他不太想走進來。
可沈連翹為他展示銀盒的神,又那麽人,讓他忍不住想靠近。
“不這裏有,”沈連翹解釋著,“你看看這件,這件,都了呢!”
拿起架上摞起來的服。
經過一晚上的折騰,那上麵的服有很多。
此時沈連翹慌地用蠻力拉扯,架忽然歪倒,有一件服的袖,正好搭在燭火上。
“噗”地一聲,服著了。
“小心!”孔佑腳步不停地衝過來,然而他還未能近前,便見沈連翹整個人跳在火上,雙腳不停踩滅了火焰。
一麵踩,一麵對孔佑出手,做出向外推的手勢。
“東家別過來!你怕火!”
下意識地,喊道。
那是要保護他,要讓他遠離火焰。
火滅了。
屋充斥著織燃燒後的味道。有些嗆人,但他們誰也沒有出去。
沈連翹把那件燒爛的服拿開,確認其他幾件服完好無損,才重重呼出一口氣。
“還好還好。”抹了一把臉,原本白皙的臉頰上頓時留下幾道黑印。
孔佑仍舊沒有說話,他看著沈連翹的一舉一,眼底流濃濃的深。
“怎麽了?”沈連翹抬起頭,有些驚訝地問道。
怎麽覺今日的東家,有些奇怪呢。
Advertisement
“翹翹,”孔佑問道,“你是怎麽知道,我怕火的?”
“一直就知道啊!”沈連翹道,“東家你曾經滅我的燭火,還總是隻點一支蠟燭。我心想著,東家是因為小時候宜驛站火災的事。”
孔佑心神震。
知道自己怕火,還一次次地要保護自己。
可是他,卻要為了複仇,為了功業,遠離而去了。
剎那間,、懊悔、憐惜、自責的心緒填滿孔佑的口,他的心像是被水拍打著,潤地蘊藏了許多力量,難自。
孔佑出一隻手,攬起沈連翹的腰肢。
他與麵對麵,這樣親的作,讓沈連翹霎時一不能。
“東……”檀口微張,麵紅潤的小心翼翼地開口,僵,不知道手腳該往哪裏放。
孔佑已經低下頭,溫潤的瓣覆蓋了細的櫻。
。
他覺自己親吻的不是誰的,而是一縷潔淨的靈魂。那靈魂著,與他心的悸纏繞在一起。
甜。
不似糖般甜膩,像是他被花瓣包裹,品嚐到了最甜的。裏有芳香,有烈酒般的甘醇。多嚐一口,就要醉了。
沈連翹下意識抬手阻擋,孔佑的另一隻手卻握住了的手。
修長的手指撥開的荑,一一,與十指握。
這作似乎比親吻更有侵略,讓沈連翹渾。覺孔佑的親吻充滿著耐心,一麵試探,一麵掠取,一麵又恰當地給予。
原來對的親吻,竟然是這麽回事。
正想細品滋味,孔佑卻已經徐徐離開。
他火熱的眼睛看著沈連翹微驚的明眸,對道:“抱歉。”
抱歉?
為什麽要抱歉?
難道親了我,就準備不認賬了?
沈連翹有些惱,他明明還牽著自己的手,竟然就要耍賴了!
Advertisement
索!沈連翹踮起腳尖,主又快速地,親了下孔佑的角。
然後迅速退後,對他道:“不準道歉!你以後,是我的人了!”
霸道的語氣,不容置疑的神,若不是臉頰紅了柿子,倒非常像一個街頭霸王。
孔佑不由得笑了。
“好,”他的另一隻手也握住的手,把拉向自己邊,抱住,重複道,“好。”
孔佑的聲音很溫和,似乎怕略一用力,就嚇跑懷裏的姑娘。
但沈連翹還是逃了。
從他懷裏逃走,邁過地上糟糟的服,頭也不回地沒深夜。
像一隻驚的白兔。
霸氣和嗔切換得如此之快,讓抱著一團空氣的孔佑,有些後悔自己抱得鬆了。
他們這樣,算是相互告白私訂終了嗎?
孔佑覺得算是。
雖然前路不可知,但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姑娘。
既然主親吻自己,那是不是說,自己並非一廂願。
屋並沒有風,孔佑卻覺他的裏被灌鼓鼓囊囊的風,那些風讓他想要衝出門外,去飲酒、高歌、呼朋喚友。
然而最終,孔佑隻是低下頭,撿起地上那些服。
的針腳很細,那是做慣了針線活的原因。
雖然的位置不太合適,但是……孔佑的手著銀盒,覺心中有暖流湧。
被人關心的覺,真好。
自從母親不在,這是第一個,為他的姑娘。
史中丞魏嗣剛進門,就聽管家說,夫子把小公子趕回來了。
因為太過氣憤,甚至退回了束脩。
這件事太不尋常了。
魏嗣為了讓自己的兒子離京中貴族子弟遠一些,給兒子找的學堂很破爛,那裏的夫子也窮,每日就靠這些束脩過活。
春日鬧災荒的時候小公子恰逢生病沒有去讀書,聽說夫子差點被死。
Advertisement
如此窘迫,竟然也不要束脩了,可見兒子把人家氣什麽樣。
“又闖什麽禍了?”魏嗣準備掉頭離開家。
出門喝口小酒,聽幾段閑書,再拐到金樓給妻子買件首飾,才能回來。
回家的時機很重要,不然是要罪的。
“這回不是炮仗,”管家低頭道,“聽說小公子在學堂設賭,賭晉王的部隊能不能打過匈奴。”
完了。
魏嗣扶額歎息,這回連酒都喝不下去了。
小小年紀開起了賭場,也不知道夫人會不會氣出個好歹。萬一被史知道,必然要彈劾他教子無方了。
等等,魏嗣忽然想起來,他自己就是史嘛。
這麽想著,心裏有些底氣,還是決定進屋安一下夫人。
“阿?”
聽說夫人在等著他用飯,魏嗣走進去,提心吊膽地喚道。
夫人果然在哭。
雖然並無飲泣之聲,但獨自坐在屋,用帕子拭淚。
周圍也沒有丫頭服侍,這是在等著同他說話了。
“別氣了,”魏嗣走過去,安道,“等再長幾年,丟北邊打仗去,磨兩年回來,就不敢這麽無法無天了。”
“你還敢說打仗?”魏夫人抬起頭,一雙眼睛紅腫著,“虧你在朝堂做事,每日都能同皇帝說上話。怎麽就讓世子爺去打仗了?先太子隻有這一個骨,你們這麽做,不是要把他推進刀山火海裏嗎?”
魏嗣這才明白過來。
夫人這麽難過,竟然不是因為兒子,是因為世子要上戰場了。
他靜靜地坐在妻子邊,握住了的手。
“為國報效、視死如歸,這正是先太子的骨,會做的事啊。”
“可是……萬一……”魏夫人攥手帕,充滿擔憂。
“留在京都就沒有萬一了嗎?”魏嗣反駁道,“京城於他,是一個困住翅膀的牢籠。出去了,才有機會。”
Advertisement
至於什麽機會,魏嗣沒有說。
他們夫妻對坐良久,最後魏夫人輕輕歎息道:“能把我娘家陪嫁的弓箭,送給世子爺嗎?”
“不能,”魏嗣道,“魏某豈是趨炎附勢之輩?況且朝中都覺得,為夫同世子劉瑯,勢同水火。”
魏夫人白了魏嗣一眼。
怎麽演著演著,自己還信了呢?
“對了,”突然又想起一事,囑咐道,“那個小孽障在後院頂盆呢,你過去,看看水若灑出來了,添一瓢。”
“好。”魏嗣起。隻要不是他頂盆就行。
“添開水。”魏夫人又加了一句。
開水啊……魏嗣忽然有些擔憂逆子的安危了。
這可比上陣殺敵還玩命呢。
朝廷的餞行很隆重,卻也盡量儉省時間。
孔佑騎馬離開城門後,回頭看了看,沒有看到沈連翹的影。
不知道去哪裏了。
是不好意思嗎?
昨夜那個吻,到底是嚇到了啊?
“走吧,等什麽?”耳邊傳來晉王劉禮的聲音,“本王想迅速與大軍匯合,聽兄長賜教。”
孔佑含笑點頭,並沒有多說什麽話。
與對自己過殺機的人同行,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他在道旁送行的人裏,看到了蕭閑。
“一路保重!”蕭閑對他們拱手。
孔佑忽然策馬離開隊列,在蕭閑前止步。
金黃的白楊樹葉下,孔佑對蕭閑出手。
猜你喜歡
-
完結585 章

侯府真千金她重生了
重回十年前的江善(周溪亭),站在前往京城的船只上,目光冷淡而平靜。她是被人惡意調換的文陽侯府的真千金,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里的容妃娘娘是她姨母,溫潤如玉的二皇子表哥是太子之位的熱門人選,出生既頂端的她本該萬千寵愛、榮華富貴且波瀾不驚地過完一生。但十六年前的一場人為意外,打破了她既定的人生......等她得知身世,回到文陽侯府,取代她身份地位的江瓊,已經成為父母的掌心寶。前世她豬油蒙了心,一心爭奪那不屬于自己的東西,不論是父母的寵愛,還是江瓊身份高貴的未婚夫,這一世,她只想快快活活地活一...
107.9萬字8 330561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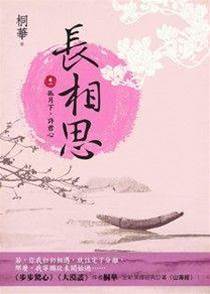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