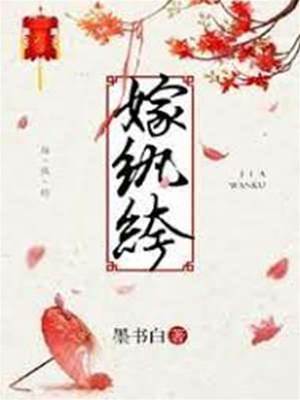《賜卿良辰》 第107章 與君終相見
孔佑看著劉禮,看他驚駭的雙眼,看他因為疼痛,扭曲的表。
如果能穿過時的界限,回到當年國子監的學堂,孔佑絕對不會忍心,對窗臺後笑得明的劉禮刀斧相向。
劉禮頑劣卻也可,時而自卑,時而又自吹自擂。他穿著華麗的服,是皇族子嗣中最為明豔的孩子。
是……他的弟弟。
可是他們終究做不兄弟。
回到京都後,孔佑曾試探過他,調查過他,以為劉禮當年不過是一個孩子,是被楚王裹挾著向前走的無辜者。
但孔佑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當年驛站中第一火箭,是劉禮進去的。
孔佑更不敢相信,大漠硝煙中,原本該同仇敵愾的兄弟,會一刀刺進他的。
孔佑不是一個人回來的。
他帶著宜驛站的數百亡魂,帶著十七年來被怨靈啃噬的魂魄,帶著大漠中一腔熱化作的激憤,把這柄刀,刺劉禮的。
罷了,曾經的兄弟是如今的仇敵。他早該殺伐果決,不能給背叛者留有活路。
隻是,這突如其來的尖,和突然出現的人,讓孔佑呆怔在原地。
他手中握著的刀,再不能刺深一點。
沈連翹穿著玄青的勁服,頭發紮在腦後,挽了一個實的發髻。紅的束腰讓看起來拔瘦削,又像是撞進絢爛中的一隻蝴蝶,璀璨灼目。
隻是,的手為何握著那柄刀,而那柄刀,又為何割破了的手?
一滴滴匯聚團,沿著沈連翹的手指,混合刀刃上累積的,滴落在地。
握住刺劉禮的寬刀,用一往無前的勇氣護著後的人,抬頭看向孔佑。
震驚和憤怒讓原本豔麗的臉平添幾分厲,像是中存留的皇族骨剎那間蘇醒,不容和質疑。
Advertisement
不過這些都不足以讓孔佑無措,讓他心底震的,是沈連翹陌生的眼神。
陌生的,仿佛本就不認識他。
不因他活著而意外,不因他歸來而歡喜。
“族長大人!”衛尉軍副統領蔡無疾呼喚著沈連翹,想要鬆開的手,卻因為男有別不敢。
蔡無疾猶豫著,把手中的刀指向孔佑。
“世子爺!”蔡無疾道,“收刀!”
沈連翹看著孔佑。
不明白前來支援的將軍,為何要把鋼刀刺晉王肚腹。
沈連翹衝上來,要阻止對方。但這將軍的作太快,快到隻來得及手握住刀。
刀割破了的手心。
起初並不覺得疼,反而是一種刺骨的冰冷。那冰冷順著胳膊向上蔓延,讓打了個激靈。然後才是疼,疼得如利刃割心。
沈連翹的目停在孔佑臉上,無法挪一分。
那迷霧般的夢境中,時時出現的影,是不是就是眼前的這個人?
這人披甲胄浴而來,單眼皮的眼睛凝聚芒,像是碎裂的琉璃落水中。這個人鼻梁高臉頰微瘦,略深,棱角分明的下頜線抵著,角微,喚道:“翹翹……”
那是驚駭又心碎的呼喚。
翹翹……
好似九天之上的神祇揮袖,仿佛一盞燭火照亮黑暗,像是憑空而來的鼓音,震碎眼前的迷霧,滌蒙塵的過往。
那些被丟失的記憶山呼海嘯般湧來,擊打在的心頭,的四肢,潔的額頭上。
沈連翹怔在原地,看到一滴淚珠從孔佑眼中落。
翹翹……
記憶中那玄青的影,與眼前的人合為一。
想起那隻掀開廚房門簾的手,想起他掐滅燭時的決然,想起他說:“不要管別人的死活,那樣,不值得。”
不,事實上,他無數次管過自己的死活。
Advertisement
被人追殺的路上,他著的子,穿過箭網逃命;學騎馬時摔下來,他背著,走過青草地和城門;京兆府的大堂上,他不惜提前暴份,也要把救下來;他甚至……甚至幫盛殮良氏全族的骸。
是良辰,,更是沈連翹!
沈連翹如遭雷擊怔在原地。
除了蕭閑給的良氏族人名譜,其他的,都記起來了。
伴隨記憶浮現的,是沈連翹心中銳利的疼痛。
孔佑,他不是戰死了嗎?
不,他沒有死!他回來了!他就在自己麵前,雖然周彌漫神擋殺神的戾氣,但他活著。
“翹翹,”孔佑喚著的名字,聲音難過,含著一乞求,“鬆手,你鬆手。”
“不要殺他。”沈連翹下意識道。
來不及想起關於劉禮的任何事,但知道劉禮是皇帝的兒子,是守城的將軍,殺了他,如何同天下人代?
“我不殺他。”孔佑承諾道。
沈連翹鬆開手,孔佑刀,苦苦支撐的劉禮再也無法站立,昏倒在地。
沈連翹呼喊蔡無疾:“快去太醫署!”
衛尉軍副統領蔡無疾抱起劉禮,懇求沈連翹同去。
“族長,您的手傷了。”
在一片混中,沈連翹跟著蔡無疾向前走了幾步,又忽然回頭,看向孔佑。
他魂不附般站著,臉上織著悲傷和困的神。
沈連翹想衝過去,看看他有沒有傷,問問他這一路旅途的辛苦,在兵荒馬的戰場抱住他,一頭紮進他懷裏。
但是沈連翹四肢僵無法彈。今日的事太突然,湧腦海的記憶也太淩,讓整個人失魂落魄。
見停步,孔佑忽然跑過來,從袖中取出一個銀質的圓盒,打開盒蓋。
他幾乎是搶過沈連翹的雙手,把那銀盒裏殘存的金瘡藥,一腦倒在的手心。然後不知從哪裏撕扯出一條窄布,仔仔細細包裹住的傷口。
Advertisement
“快去治傷,快去。”
這裏仍然有不匈奴殘兵,孔佑深深地看了沈連翹一眼,便回頭繼續殺敵。
蔡無疾催促著沈連翹,他們向太醫署奔去。
走下臺階,沈連翹覺自己的腳步越來越沉,越來越穩,仿佛漂浮的水草突然有了。
孔佑活了。
撞開太醫署的門,淚流滿麵雙手握。
手心很疼,沒有做夢。孔佑活了!
如喪考妣的皇帝帶領皇子皇後,藏在皇宮最深。
由一百多衛尉軍死守殿門,殿更是用沉重的家堆起來,封死出口。
皇帝在等,等衛尉軍擊退匈奴,或者等荊州刺史王正海前來勤王。
他甚至顧不得太多嬪妃,也顧不得那些未能趕來的公主。反正隻要他能活著,孩子還能再生,天下,還是他的。
枯苗雨般,終於等來了好消息。
“陛下,有援軍到!”
衛尉軍在外稟報道。
巍巍的侍大總管唯恐有詐,扶著門口的家問:“哪裏來的援軍?”
衛尉軍支支吾吾,最終回答道:“卑職也不清楚是哪裏的,隻看到穿著我大周的戰袍,把攻皇宮的匈奴殺完,正往這邊過來了。”
“快開門,開門!”
皇帝從座後起,整理冠冕,係袍,揮手道。
他要看看是誰解了京城之危,是誰衝破城外封鎖,救了一城百姓。
不管是誰,必然要加進爵。不,要封異姓王!
誰讓我皇位穩固,我必讓他世代簪纓。
沉重的家挪開,顧不得擺放整齊,殿門便緩緩打開。
皇帝向外看去,見衛尉軍守護在殿門兩側,遠走來許多將士。他們佩長刀邁步進殿,滿麵塵土是他們艱辛的佐證,浴的戰昭顯著殺戮的可怖。
皇帝有些不滿他們把兵帶進殿的無禮,但非常之時,他隻能忍下來,問道:“你們的將軍是誰?”
Advertisement
將士向兩邊散開,出後從容而立的人。
孔佑。
皇帝瞳孔張大抖,他下意識看向皇後,又看向侍,確認自己不是在夢中,方走近一步道:“阿瑯!你回來了!上天護佑,你沒有死!”
他的眼了,但是不出一滴淚。
“微臣救駕來遲,”孔佑肅然道,“請陛下降罪。”
他虛跪一下,被皇帝扶起。
“這都是怎麽回事?”皇帝看看簇擁著孔佑的將士,難以置信道,“這些兵馬,這些人……”
“他們一部分是因為反抗逆賊楊嘯,被驅趕的北部守軍,一部分是微臣事急從權,調配隴西的兵馬,更多是這一路上收編的府軍和民壯。他們都願意出生死,為大周而戰。”
出生死,為大周,而不是皇族帝王而戰。
皇帝品出這話裏的玄機。
他不明白孔佑為何就活了,還帶著足以同匈奴抗衡的兵馬回來。
但他很清楚,不能讓孔佑活。
羽翼未時尚且難以把他除去,如今他帶著兵良將回來,如果弒君謀位,自己怎麽辦?
皇帝的作漸漸僵,他看一眼門外的衛尉軍,見不朝臣已經趕過來。
有朝臣在,有衛尉軍,那麽……
一念至此,皇帝正要發令,忽然便聽到孔佑道:“陛下,微臣有禮奉上。”
禮?
人群中走出一位麵生的將軍,他的手裏握著一簇黑乎乎的發,發下麵,赫然是一個剛剛被砍掉的頭顱。
頭顱從頸部被利刃砍掉,旋轉著,正麵朝向了皇帝。死者眼皮外翻,口鼻冒,張著的似乎隨時要痛罵什麽。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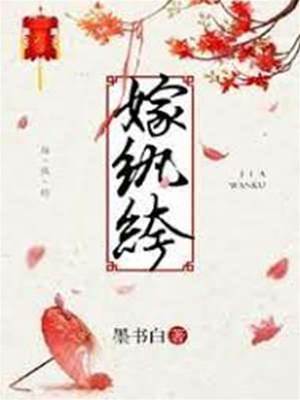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287 -
完結737 章

妃常妖嬈:王爺盡折腰
現代具有特異功能的西醫一朝穿越到失寵和親公主身上。白蓮花一瓣一瓣撕下來。王爺高冷傲嬌也無妨,某女揮起小鞭子,收拾得服服貼貼。
127.4萬字8 102792 -
完結216 章

不夜墜玉
師蘿衣與錦鯉小師妹爭斗。 不甘心比了一輩子,敗了一輩子。青梅終究比不過天降,最后連她的竹馬未婚夫也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小師妹。 破廟瀕死,無人殮骨。 就很氣啊! 她驟然想起,很久之前,自己也曾贏過一次:她不可描述了小師妹看得和眼珠子一樣的凡人兄長
33.5萬字8.33 84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