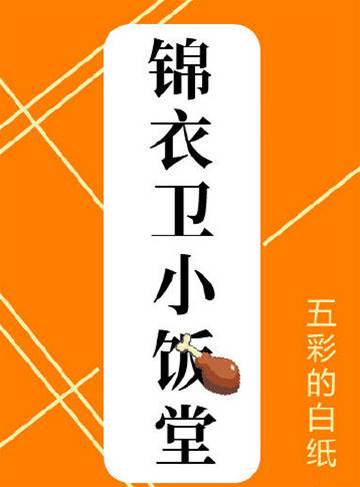《和親后,瘋批暴君索取無度》 第一百一十章 一梳梳到尾
謝蘅蕪輕輕應了一聲,兩人沒再說話,只靜靜地,聽著對方的呼吸聲與心跳聲。
蕭言舟懷中溫暖,抱得又舒服,謝蘅蕪半瞇起眼,覺得又有些困了。
……不,這可不。
蕭言舟適時問起“你與們都說什麼了?”
謝蘅蕪便將和那些夫人們說的事兒仔仔細細講了,這些事,問一問霍珩便也知道了,但蕭言舟就是想聽親口說罷了。
聽說這些有的沒的,平白有種安心。
謝蘅蕪兀自絮絮著,說到了國公夫人。
嘆一聲,憂愁道“陛下你說……妾的事,到底該如何與他們開口呢?”
蕭言舟沒回答,倒是抬手去卸頭上的釵環了。
謝蘅蕪似乎也不是想要個回答,繼續說著“若是妾主開口,也顯得太有目的了。可不開口,哪有機會讓他們自己發現呢?”
埋怨“若是妾的胎記是長在顯眼的地方就好了。”
蕭言舟冷不丁道“若是顯眼,恐怕阿蘅會先被別人發現。”
謝蘅蕪一頓,想也是。
要是顯眼……崔太后說不定是最先知道的人。
哪還得著知道自己生父母的時候。
Advertisement
嘆聲“那該怎麼辦……”
蕭言舟撥弄著發上步搖的流蘇,玩笑道“不如孤在先蠶禮上安排個滴驗親,讓你們相認如何?”
謝蘅蕪氣得杵了一下他口,步搖上的流蘇隨作晃,啪地在蕭言舟手背上。
怎麼他半點不為此事苦惱似的。
分明這是個該慎之又慎的事才對。
蕭言舟旋即收手,安般地了發頂。
“好了……孤會給你想法子的。”
他上這樣說著,實際心中也沒底。
這種事,
哪有什麼所謂周全法子呢。
謝蘅蕪哼了一聲,知道他也是在安自己,沒再追問。
索就岫書苑的事又聊了一會兒。
這期間功夫,蕭言舟功將頭上那些發飾盡數除下,原先整齊的發髻也因他這般了起來。
謝蘅蕪說完事,充滿怨念地了他一眼。
蕭言舟自知理虧,低聲猶疑“孤給你……重新挽發?”
謝蘅蕪抬眉,想這倒是難得。
“好啊。”爽快應下。
蕭言舟心中一呵,想還真是不客氣。
有蕭言舟在的時候,謝蘅蕪還真能腳不沾地。
Advertisement
比如現在,便是他抱著自己坐到了妝鏡前。
蕭言舟拿過妝臺上的玉梳,捧起一邊頭發,正要梳下去,卻見鏡中的謝蘅蕪言又止地向他。
蕭言舟作一停,問“怎麼了?”
謝蘅蕪猶豫著,小聲說道“陛下,梨落為妾梳頭的時候,都會用些發油的。”
蕭言舟嘖一聲,看妝臺上諸多瓶瓶罐罐,一時頭疼。
真是麻煩。
但他又不愿在謝蘅蕪面前暴自己不認識的事,于是著頭皮,隨意揀了一個蓋子上繪了花兒的。
謝蘅蕪瞳孔微,抬手制止他。
“陛下……這是香,搽臉的。”
蕭言舟面無表地哦一聲,轉而去取旁邊的小罐子。
“……這是口脂。”
“……這是珍珠
。”
“……這是裝螺子黛的盒子。”
……
謝蘅蕪忍笑,將發油遞到了蕭言舟手中。
蕭言舟仍是面無表的模樣,看著冷靜,但耳已然紅了。
謝蘅蕪十分乖覺低眸,給他留了一點面。
但蕭言舟又犯了難。
這東西……怎麼用啊?
謝蘅蕪等了一時,悄悄抬眼,就見到蕭言舟在對著手里的東西發怔。
Advertisement
忍不住出聲“陛下用梳子沾一點,梳在發尾就好。”
蕭言舟咳嗽一聲,冷聲“孤知道,用你多。”
謝蘅蕪抿一笑,垂眼下去。
尋常發油都帶著些香,但謝蘅蕪用的是特質的,自然沒有香氣。
蕭言舟依著的說法,先從上至下將發梳順了,才沾上發油,輕輕梳著發尾。
他雖是冷著臉,作卻很輕。
頭上發傳來輕微的拉扯,也不疼,只是有些的。謝蘅蕪舒適地嘆一聲,復又向了鏡中。
菱花鏡里,人長發披散,黑如墨云,后俊逸郎君神專注,細致小心地梳過每一寸發。
謝蘅蕪眼睫一,腦海里浮現出幾句話。
“一梳梳到尾,二梳白發齊眉……”
鏡中,蕭言舟抬起眼看向,兩點漆眸像是凝在上。
謝蘅蕪后知后覺,自己竟是將所想給說出來了。
抿了,試圖含混過去。
蕭言舟抬眉“怎麼不接著說了?”
謝蘅蕪眨一眨眼,想當然是因為本來就不該說出來的。
以及……
這下一句,是三梳兒孫滿地啊。
Advertisement
這說出來,顯得自己多麼急不可耐似的。
慌忙轉開話頭“陛下,妾覺得差不多了,可以不用梳了!”
蕭言舟意味深長地哦一聲,卻不放過“無妨,孤可以繼續聽阿蘅說。”
謝蘅蕪見此,蹙眉扶額角,哎呦道“陛下,妾忽然覺得頭好疼啊……”
蕭言舟漠然“阿蘅,這有些太假了。”
謝蘅蕪的子微妙一頓,旋即繼續哎呦道“不是呀陛下……那些首飾在頭上沉得慌,現在解開了,妾還是有些頭疼。”
“梨落都會給妾按按的……”
小聲嘟噥“莫非陛下是不愿意,才不信妾之言嗎……”
蕭言舟哼笑一聲,知道在激將,偏偏自己還真忍不了。
說他比不上一個宮人?怎麼可能!
他溫聲“阿蘅都這樣說了,那孤……就給阿蘅按一下吧。”
蕭言舟的聲音聽著溫和,謝蘅蕪卻覺得惻惻的,仿佛有一涼氣直竄到脖子后頭。
一炷香后,謝蘅蕪為自己方才的激將而后悔。
蕭言舟不止給按了頭皮,還將手順下去,順帶按過了肩頸。
如果說在頭上還覺不出來什麼,那麼在肩頸,可就太明顯了。
蕭言舟多有些公報私仇的意思,力道大得讓酸痛無比。
謝蘅蕪疑心自己要被他按得散架了。
然自己開的口,說什麼也不能了停。
謝蘅蕪抿著,偶爾實在忍不住,才輕嘶了幾聲。
但蕭言舟的力道,似乎更大了。
再也不讓他按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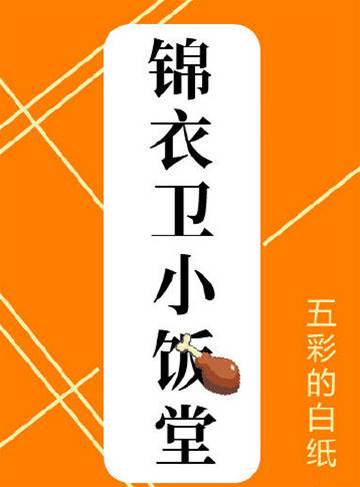
錦衣衛小飯堂(美食)
自從董舒甜到錦衣衛小飯堂后,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指揮使最近吃了什麼#錦衣衛1:“我看到夜嶼大人吃烤鴨了,皮脆肉嫩,油滋滋的,嚼起來嘎吱響!”錦衣衛2:“我看到夜嶼大人吃麻婆豆腐了,一勺澆在米飯上,嘖嘖,鮮嫩香滑,滋溜一下就吞了!”錦衣衛3:…
77.3萬字8.09 39239 -
完結656 章
和離后我把殘疾攝政王衣服撕壞了
她,百年宗門玄仁堂掌門,莫名穿越成大燕國花癡無顏女寧宛。 新婚當夜便讓渣男斷子絕孫,自請下堂。 一時間,萬人哄笑,惹來多個皇子頻頻側 人人都發現曾經的大燕國花癡傻子寧宛,沒了胎記,竟然回眸一笑百媚生! 覬覦? 羞辱? 陷害? 也要看寧宛那活死人肉白骨的醫術,答不答應! 從此,寧宛名揚四海,傾城容顏名聞天下,醫術通天驚泣鬼神。 一時間,國公府的門檻踏破,昔日萬人嘲笑的傻子,如今眾皇子挨個跪著求娶。 渣男更是泣不成聲:「宛宛,和我回家,以後什麼都給你」 寧宛巧笑倩兮。 “我把你們當侄子,你們居然還恬不知恥肖想嬸子?” 赫連墨川吻著女人的紅唇,咬牙切齒:“你究竟還認識本王幾個好侄子。
87.7萬字8 33948 -
完結131 章

寵妃的演技大賞
上輩子,世人都說蘇菱命好,姝色無雙,又出身高門,父親是鎮國大將軍,兄長是大理寺少卿。 十七歲嫁給晉王為妃,兩年後又順理成章做了大周皇后。 論其尊貴,真是無人能及。 然,延熙元年,鎮國公臨陣脫逃,蘇家被指認通敵叛國。 蘇菱誕下一子後,死於后宮。 待她再睜開眼時,卻成了五品太史令之女—秦婈。 一朝夢醒,她雖不會再惦記那個薄情的男人,卻不得不為了她曾生下的孩子,再入宮一次。 選秀當日,帝王靠在龍椅上垂眸不語,十分不耐地揉了下眉心。 便是留牌子都未曾抬眼。 直到秦婈走進去,頂著與蘇後一模一樣的臉,喚了一句:陛下萬福金安。 大殿之上,帝王驀然抬頭,幽遂的雙眸在對視間失神,茶盞碎了一地。 失魂落魄呢喃喊了一聲:阿菱。 【小劇場】 秦婈:再入宮,我發現當年坑過我的人都長了皺紋,包括那個狗皇帝。 蕭聿(yu):演我?利用我?然後不愛我? 【母愛小劇場】 她以為,人死如燈滅,過去的事,便永遠過去了。 可沒想到。 小皇子會偷偷跑到她的寢殿,拉著她的小手指問:“你是我母后嗎?” #她是他的白月光,也是他的心頭好。# #回宮的誘惑# ps: 非典型重生,時間線是持續前進的。 女主嫁了男主兩次,男主的白月光是她
34.4萬字8 11908 -
完結1648 章
殘王梟寵:涅槃醫妃殺瘋了!
“若有來生,定不負你一腔深情,讓那些害我性命、辱我親朋之人血債血償!“前世,沈玉眼瞎心盲,放著與暝陽王戰云梟的婚約不要,癡戀三皇子,為他奔走為他忙,害戰云梟殘了腿,瞎了眼,最后為她而死。可三皇子登基,第一件事情便是娶她表姐,滅她全族,一劍砍了她的頭!重生十五歲,沈玉醫毒雙絕,一針在手天下我有。斗渣男,虐賤女,挽回前世的深情冷王,帶領家族扶搖而上,秀麗山河更要有她一席之地!皇子妃有什麼好?她要一枝獨秀做皇后!前世那一腔深情的冷王“好說,掀了元氏皇族就是了!”1v1
293.5萬字8 48664 -
完結243 章

小小姐每天都在恐婚
大理寺卿之女的奚蕊,作爲京都貴女圈的泥石流,琴棋書畫樣樣不通。 奈何她生得嬌豔動人,家族又頗有權勢,縱然廢物了些,娶回去做個花瓶也是好的。 在她及笄那年,媒婆踏破了奚家門檻,奚父再三抉擇,終於選定吏部尚書嫡子。 奚 . 恐婚 . 蕊:天下男人一般狗,一個人多自在? 於是男方提親當日,她一襲素白長裙,淚眼婆娑,手持裙襬撲通一聲跪在堂前。 “父親有所不知,女兒早心悅祁家將軍,非卿不嫁,今聽聞其對戰匈奴生死不明,故自請守節三年。” 奚父氣得吹鬍子瞪眼,一場訂婚宴雞飛狗跳。 經此一事,奚家淪爲京都笑柄,衆人皆嘲她膽大妄爲又不自量力。 上趕着當未亡人的,這奚家小小姐倒是第一個。 說來也是,那大權在握的祁公爺若能活着回來,又怎會看得上這種除了美貌一無是處的女子? * 忽有一日祁朔詐死逃生,鎮北軍凱旋還朝,舉國歡慶。 隱匿在人羣之中的奚蕊遙望那身着厚重鎧甲,威風凜然的挺拔男子,隱隱感到雙腿發軟。 “......父親,女兒多年未見外祖母甚是想念,不如允女兒去丹陽縣住段時日?” * 後來,大婚之夜紅燭攢動。 男人高大的身形將她完全籠住,戲謔又低啞的哼笑在她耳邊響起。 “聽聞夫人深情至極?“ 奚蕊有氣無力,只覺那日所想的瑟瑟發抖果真不是幻覺。
36.9萬字8.18 156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