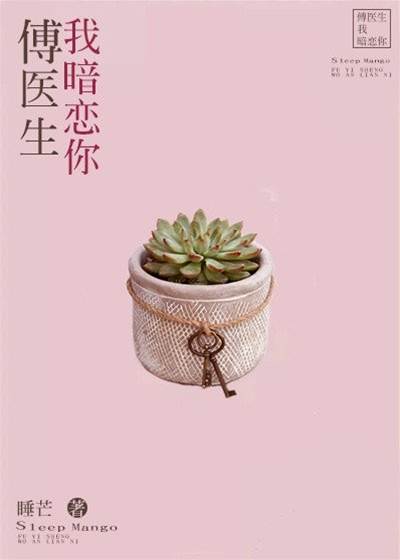《閣樓裏囚著病嬌大佬的金絲雀》 第42章 桑桑的任性
桑桑已經被他介紹出去了,夜太太的位置很高調,夜寒沉害怕江家或者自己的父親對桑桑不利。
他要把桑桑保護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才放心。
要不是江家一直婚,這個男人也不想把桑桑這麽快帶出來!
但桑桑好不容易才逃出來幾天,怎麽願意又被關進囚籠!
掙紮的很厲害,想要將自己從手銬裏掙出來。
很快,細的手腕就被掙紮出了一道紅紅的勒痕,眼看就要出。
夜寒沉心疼的瞬間眼底猩紅,訓斥:“別鬧了!”
夜寒沉突然很兇!
桑桑瞬間被他嚇得不敢了。
但心裏很憤怒很委屈,瞪著兇的男人,覺事似乎沒有了轉圜的餘地,難的一下子就哭了。
“嗚嗚,惡魔,惡魔……”
Advertisement
桑桑小一撇,難的哭的上氣不接下氣的。
夜寒沉心疼不已,但眼神晦暗戾,很多事,他不能容忍桑桑任!
看著桑桑一直哭,他出大手,想要拍拍的背安。
但被桑桑很兇的瞪著他,吼他:“滾啊,別我!”
夜寒沉隻能無聲的放下,不知過了多久,桑桑像是終於哭累了。
像是想再看外麵的世界最後一眼,看向了窗外不斷後退的樹木,整個人可憐的蜷了一團。
啜泣著,長長卷翹的睫上還掛著淚珠,隨著小子一一的往下滴落。
一個小時後,桑桑被夜寒沉強行帶回了夜宅閣樓!
左手腕上的手銬男人始終沒有給打開。
“桑桑,這幾天你在外麵累了,我們洗個澡。”
Advertisement
夜寒沉低沉詢問著桑桑,但桑桑現在連瞪他都不瞪了,氣鼓鼓的本不理他。
他苦笑一聲,一點點抱起桑桑,推著椅去了浴室。
這裏是傭人提前放好的熱水,桑桑這幾天在出租房都沒有洗澡。
夜寒沉將桑桑剛了服,放進浴缸,桑桑突然很氣的衝他吼:“我要出去!”
隨之而來的,就是一通小拳頭,衝著他的使勁捶打!
要是平常,夜寒沉隻會覺得是小貓打鬧,綿綿的無關痛,但他現在傷勢重,稍微一,就會撕裂。
尤其是桑桑,還真的一拳打到了他車禍的那個貫穿傷口上!
他霎那疼的出了一冷汗!
但也沒再舍得兇桑桑,而是哄:“桑桑乖,不要打了,我去給你拿沐浴,我們今天用油草莓味的好不好?”
Advertisement
“不好!不好!”
桑桑心裏有氣,小手一把奪過夜寒沉手上的沐浴,就使勁朝著他的砸過去!
夜寒沉沒有抵擋,就任憑桑桑出氣,任憑打。
沉甸甸的沐浴瓶子,一下一下砸在他的上,他傷口裂開,疼的臉都白了,薄微微抖。
一直等到桑桑沒有力氣了,他才抬著幾乎疼的揚不起來的胳膊,溫捋了捋耳邊碎發:“寶貝,累了吧,現在可以洗了嗎?”
桑桑心裏更窩火了,一掌就要打過去!
“寧桑桑!”
男人終於被的胡鬧失去了耐心,哢嚓一聲,將左手腕上的手銬,反過來鎖在浴缸後麵的水管上。
“嗚嗚嗚——”
桑桑突然害怕,還想掙紮,但被男人強行摁倒在浴缸壁上,掐起下。
眼睛猩紅可怕:“寶貝,一個人這麽不想洗,是想要我一起嗎?”
猜你喜歡
-
完結178 章

重生之香妻怡人
紫菱在失去意識的那一刻,聽到小三問渣男老公:“親愛的,她死了,姚家所有財產是不是都成我們的了?”原來,渣男老公不願意離婚,只是爲了外公留給自己的龐大財產!悲憤欲絕,滔天的恨意下,她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識。再次醒來,鼻翼間充斥著消毒藥水的味道。一張放大了熟悉的俊臉面色焦急看著她問:“紫菱,你感覺還好嗎?”好個屁!她被
43.2萬字8 35618 -
完結448 章
豪門隱婚,傲嬌總裁霸道寵
慕錦愛厲沭司的時候,他傲嬌不屑還嫌棄。她不愛他的時候,他也從不阻攔,但轉眼她就被人設計,被送到了他的床上。慕錦:我不是故意的。她對天發誓絕對冇有禍害彆人的心思,甚至還把設計她的人給找了出來,男人卻對她步步緊逼,最終把她逼到了婚姻的墓地。慕錦一萬個不願意,我不嫁!不嫁?男人涼涼的睨著她,你難道想未婚先孕?
91.2萬字8 38277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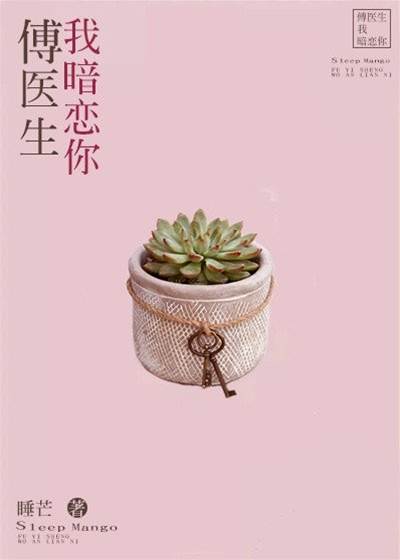
傅醫生我暗戀你
暗戀傅醫生的第十年,林天得知男神是彎的! 彎的!!!! 暗戀成真小甜餅,攻受都是男神,甜度max!!!! 高冷會撩醫生攻x軟萌富三代受 總結來說就是暗戀被發現後攻瘋狂撩受,而受很挫地撩攻還自以為很成功的故事……
44.4萬字8 7391 -
完結83 章

小情竇
身為北川大投資方長子,祁岸俊朗多金,一身浪蕩痞氣堪稱行走的荷爾蒙,被譽為本校歷屆校草中的顏值山脈。與他齊名的宋枝蒽氣質清冷,成績優異,剛入校就被評為史上最仙校花。各領風騷的兩人唯一同框的場合就是學校論壇。直到一場party,宋枝蒽給男友何愷…
33.9萬字8 68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