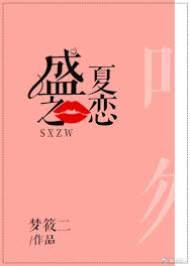《一念之私》 施皓X鄭解元——夙敵(19)
宴會場華燈璀璨,香鬢影,好不熱鬧。與之相比,建筑外頭就要安靜得多。
夜中,鄭解元立在一株據說已有百年歷史的紫藤樹下,一手著兜,另一只手夾著長煙。旁的垃圾桶頂了有五六個煙,都是他這半小時來的果。
鄭解元其實不大煙,他始終認為,人生在世,熱衷一樣癮就夠了,煙酒只能沾一樣。不過今天例外。今天,他確實遇到了不得不大口汲取尼古丁的難題。
施皓什麼意思?
前腳剛說喜歡他,后腳就跟他玩冷戰,把他當什麼了?膩了,不想玩了好歹說一聲啊,他難道還會纏著他嗎?
鄭解元咬住煙,無意識地磨牙。
不遠的玻璃側門忽然被人推開,對方沿著小道走來,停在了離鄭解元三米遠的地方。線昏暗,又有枝葉遮擋,鄭解元看不清對方的臉,只模糊地辨認出是名高大的男人。
“啪”,寂靜放大了一切細微的聲音,一點小小的橘紅在黑暗中亮起,不一會兒,煙味順著秋夜的涼風送到了鄭解元的所在。
對方也是來煙的。確認了這一點,鄭解元收回目,沒再管人家。
兩人相安無事各各的煙,鄭解元告訴自己這是最后一支了,完他就進去找施皓,然后讓他把話說清楚。
“哥哥,哥哥!”
一聲稚的尖打破了夜的寧靜。鄭解元抬頭向聲源,發現是池塘方向傳來的,丟下煙就急急跑了過去。
“哥哥嗚嗚嗚,你別嚇我……”一名十歲左右,穿著公主的小孩跪坐在池塘邊,驚慌地不斷朝池塘中央呼喊。
池塘種滿了荷花,這個季節雖然花早沒了,葉子卻依舊茂盛,像一蓬蓬綠的傘,在池水里。
Advertisement
離岸邊大約兩米左右,飄著艘單薄的小舟,是酒店工作人員日常清理池塘垃圾用的,照理不用時應該好好拴在岸邊,不知怎麼就到了水中央。
不同于鄭解元剛剛所站的地方,池塘周圍有許多景觀燈,照著水面,照著岸上,線明朗得多,這也使他很快發現了小舟下方,著船的小手。
男孩艱難地將自己的口鼻出水面,想要靠自己再次爬回船上,卻一個手沒抓住,整個人沉進了水里。
沒有猶豫,鄭解元一外套,立馬沖進了水里。
池塘水最深也不到兩米,他幾次蹬都能踩到池底的泥,但對不到一米五的小孩子來說,這已經是可以致死的水深。
男孩了驚嚇,鄭解元一靠近,他就跟終于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樣,整個人死死纏住他,攀在他的上。人在垂死之際發出的求生是很強的,鄭解元從沒遇到過這種力量,手腳都像是綁了大石頭似的,本游不開。
嗆了好幾口水,危急之際,他突然到一輕,上的石頭不見了。再定眼一瞧,竟然是施皓從背后將小男孩托出了水面。
對于突然降臨的男人,鄭解元錯愕不已,但這會兒實在不是問話的好時機,也只能先把疑問咽回肚里。他跟在對方后頭,三人沒多會兒便游到了岸邊。
“哥哥,你沒事吧?”小孩撲過來,哭著抓住男孩的手,“我都說不要去摘葉子了,你嚇死我了!”
兩人應該是一對雙生子,除了別,長得是一模一樣。
“對不起嘛……”說著,男孩白著臉打了個噴嚏。
鄭解元把自己丟在岸邊的西裝外套拾起來,拿出里頭的手機與煙盒,披在了男孩上。酒店工作人員這時也聽到靜跑了過來,見三個人都是一,驚訝地問過緣由后,一個勁兒地向施皓和鄭解元賠禮道歉,說是他們考慮不周,沒有在這邊安排保安巡視。
Advertisement
“你們應該是吳會長的孩子吧?”鄭解元將襯衫出來,盡可能地擰去下擺的水分。
作為今晚設宴的主人家,他對來的賓客多有點印象。
孩點頭:“我們爸爸是姓吳來著。”
肩膀突然一重,被披上了一件又又冷的西裝外套,鄭解元疑地看向旁的施皓,不明白他干嘛要把服披自己上。
“帶他們去找家長吧。”施皓對工作人員道。
兩名工作人員領命離去,剩下一名負責帶他們去洗澡換服。
對方走在前面帶路,鄭解元和施皓淋淋跟在后頭。兩人誰也不說話,氣氛逐漸尷尬。
鄭解元越走越心煩,忽地一把扯下上的外套,要還給施皓。
施皓看一眼外套,沒接:“你后面出來了。”
鄭解元一開始還沒明白什麼出來了,琢磨了下猛地反應過來,是背后的紋出來了。白襯衫遇到水,在上,可不就是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嗎?
!鄭解元暗罵一聲,屈辱地重新穿上了施皓的西服外套。
工作人員帶他們到了一間空房門前,替他們刷開房門后,告知里面的東西可以隨意使用便離開了。
鄭解元一進屋就掉了上的外套:“你先我先?”
施皓慢條斯理解著扣子:“你先吧。”
鄭解元也不客氣,直接沖進了浴室。
怕池塘里的水不干凈,他洗得格外仔細,洗完神清氣爽地踏著霧氣走出浴室,見地上服全都被收走了,施皓換了件浴袍,開著落地門,正在臺上煙。
鄭解元到這時才忽然意識到,方才與他一同在紫藤樹下煙的,是施皓。
“該你了。”鄭解元出聲道。
施皓回頭看向他,按滅煙,一言不發地走向浴室。
Advertisement
鄭解元在床上躺下,沒事做,拿手機出來玩,過了會兒又起來,換到一旁沙發上——無他,穿著浴袍躺床上這個行為太曖昧了,好像他在等施皓臨幸一樣,他覺得別扭。
他給他爸發了條信息,說自己有事先走了,讓他不用找他。
鄭四海能夠渡過這次危機,可以說全靠兒子出力,從前還會仗著老子的份說他兩句,現在是說都不敢說了,要啥給啥,簡直百依百順。
鄭解元甚至懷疑,他就算現在出柜,他爸都不會發火,只會強忍淚水讓他怎麼高興怎麼來。
一墻之隔的浴室里,水汽朦朧中,施皓雙手撐住墻面,任溫熱的水流不斷沖刷脊背。
十指慢慢握拳,胳膊到肩膀的線條繃起來,肩胛骨也因此更為突顯。
既然已經忍了這麼多年,再多幾天又怎樣呢?
他得讓他知道,誰才是那個正確的選項。
鄭解元盤坐在沙發上,正津津有味地玩手機游戲,頭頂上方忽然被一道影籠罩。
施皓向他出手:“借我手機用下。”
鄭解元剛想問你的呢,就記起剛才施皓是沒外套直接下水的,估計手機在口袋里,早就開不了機了。
他退出游戲,將手機遞給對方。施皓拿著他的手機走去了臺。
鄭解元發誓他沒有故意聽,但房間太安靜,沙發又離臺很近,聽到幾句也是難免的。
“是我。我有些事要理,晚點會自己回去,你讓老李送你……路上小心,我手機壞了,這部手機不是我的,你不要打……嗯,再見。”
無論多晚,他從施皓家離開,對方從來沒有對他說過“路上小心”這種話。
鄭解元著酸的心臟,一時分不清是在氣施皓厚此薄彼、區別對待,還是氣自己竟然要在意這種小事。
Advertisement
施皓打完了電話,回到房間,就見鄭解元耷拉著腦袋坐在沙發上,盯著自己什麼也沒穿的兩間,長長嘆了口氣。
“……”
施皓將電話還了回去。
鄭解元抬起頭,看了他片刻才手去接。
“你能不能幫我把背后的紋改了?”他上問著,手里去手機,接過竟然不。
他出疑地表,又加了點力,這才出來。
“改什麼樣的?”施皓垂眼問他。
“隨便,能見人就行。”
鄭解元本意是想表達自己這個紋的糟糕程度已經沒有別的能比的了,起碼給他改個能下水游泳的紋吧,結果施皓理所當然會錯意,以為他是要和人赤相見,才急著要改。
“不行。”于是,他想也不想拒絕了。
鄭解元蹭地一下就跳了起來,火大地攥住施皓浴袍襟,道:“你別以為我不敢揍你啊!”
施皓毫不懼,甚至還勾起角挑釁他。
“揍啊。”
鄭解元抿住,眼里怒氣蒸騰,雙地抿一條向下的弧線。
雙手用力一推,施皓失去平衡,向后倒到了床上。他下意識想起來,鄭解元又推著他口把他按了回去,坐在了他的上。
“一人一次,算是我還你的,以后不管你跟男的好還是的好,都跟我沒關系。”鄭解元手去解施皓的浴袍,由于剛才的拉扯,浴袍本就松垮,很輕易便解開了。
施皓還在愣怔中,就被對方了個:“喂……”先等等。
“別婆婆媽媽的。”鄭解元打斷他,一扯帶子,把自己的浴袍也了下來。
一人一次,這是非常公平的方法。還回去了,恩怨就兩清了,就像之前的施皓和桑念。
然而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低頭看了眼施皓還未復蘇的部位,鄭解元豪爽流暢的作一頓,回想起上次的劇痛,他實在沒有勇氣自己來,猶豫了一下,選擇翻趴到了一邊。
“來吧,這次我自愿的,你不用有什麼顧慮,上我吧!”
施皓衫凌地撐起,看著眼前呈“大”字型趴在床上的鄭解元,心復雜。
這個人大概是天生來克他的。
他要什麼,就偏不給什麼,等他選擇忍蟄伏,從長計議了,又突然將他一直想要的塞到他里,他咽下去,也不管他……是不是會因貪多而噎死。
猜你喜歡
-
完結485 章
萌妻小寶神秘爹地求抱抱
魚的記憶隻有七秒,而我,卻愛了你七年。 ——喬初淺。 喬初淺從冇有想到,在回國的第一天,她會遇到她的前夫----沈北川! 外界傳言:娛樂圈大亨沈北川矜貴冷酷,不近人情,不碰女色。 卻無人知道,他結過婚,還離過婚,甚至還有個兒子! “誰的?”他冰冷開口。 “我……我自己生的!” “哦?不如請喬秘書給我示範一下,如何,自—交?”他一字一頓,步步趨近,將她逼的無路可退。 喬景言小朋友不依了,一口咬住他的大腿,“放開我媽咪!我是媽咪和陸祁叔叔生的,和你無關!” 男人的眼神驟然陰鷙,陸祁叔叔? “……” 喬初淺知道,她,完,蛋,了!
86.5萬字8 13911 -
完結471 章

萌寶尋爹:媽咪太傲嬌
母親去世,父親另娶,昔日閨蜜成繼母。 閨蜜設局,狠心父親將懷孕的我送出國。 五年后,帶娃回國,誓將狠心父親、心機閨蜜踩在腳下。 卻沒想到轉身遇上神秘男人,邪魅一笑,“老婆,你這輩子都逃不掉了……”
83.4萬字8 75541 -
完結84 章

敗給喜歡
多年后,雨夜,書念再次見到謝如鶴。男人坐在輪椅上,半張臉背光,生了對桃花眼,褶皺很深的雙眼皮。明明是多情的容顏,神情卻薄涼如冰。書念捏著傘,不太確定地喊了他一聲,隨后道:“你沒帶傘嗎?要不我——”謝如鶴的眼瞼垂了下來,沒聽完,也不再停留,直接進了雨幕之中。 很久以后,書念抱著牛皮紙袋從面包店里出來。轉眼的功夫,外頭就下起了傾盆大的雨,嘩啦嘩啦砸在水泥地上。謝如鶴不知從哪出現,撐著傘,站在她的旁邊。見她看過來了,他才問:“你有傘嗎?”書念點頭,從包里拿出了一把傘。下一刻,謝如鶴伸手將傘關掉,面無表情地說:“我的壞了。” “……” *久別重逢/雙向治愈 *坐輪椅的陰郁男x有被害妄想癥的小軟妹
24.9萬字5 8280 -
完結501 章

金牌律師Alpha和她的江醫生
ABO題材/雙御姐,CP:高冷禁.欲腹黑醫生omegaVS口嫌體正直悶.騷傲嬌律師alpha!以為得了絕癥的岑清伊“破罐破摔“式”放縱,三天后被告知是誤診!換家醫院檢查卻發現坐診醫生竟是那晚和她春風一度的漂亮女人。岑清伊假裝陌生人全程高冷,1個月后,江知意堵住她家門,面無表情地說了三句話。第一句:我懷孕了。第二句:是你的。第三句:你必須負責。——未來的某一天,江知意堵住她家門......
172.4萬字8 11794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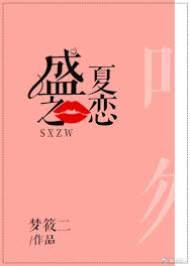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5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