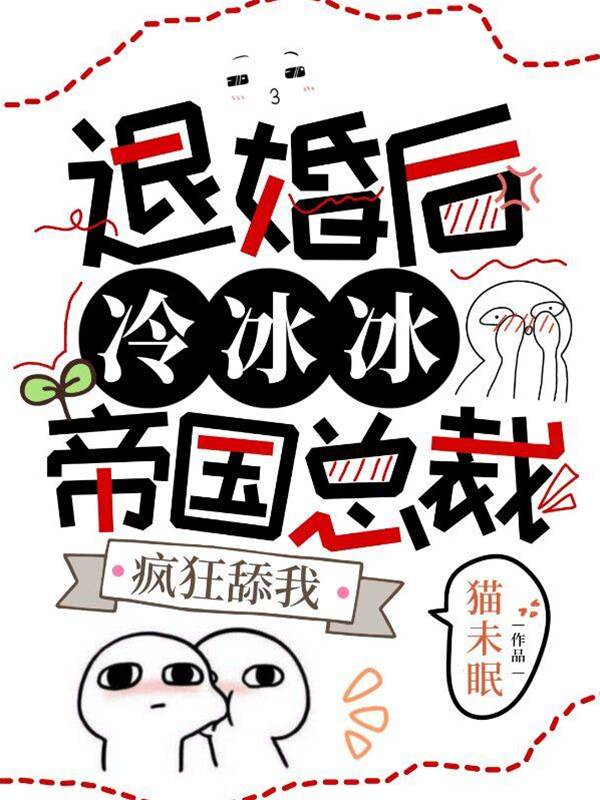《含梔》 第 62 章 含梔
后來一整場音樂會,路梔都看得心猿意馬。
他那段話時不時就隨著樂聲進腦海,一遍遍地加深印象,的細節也在回想中慢慢補充完整。
怪不得。
怪不得在俱樂部捉到傅的時候,沒過幾分鐘,傅言商就恰到好地出現、救場、面地把請進自己的VIP包,并讓侍應生端來熱茶。
那時覺得他和傅是一家人、一個隊伍,因此并沒多想,談話也沒往心里去,出了俱樂部就忘了。
再見就是他作為兄長,“好心”替傅善后,請們一家人去湯池泡溫泉,以一種極為穩善妥帖的方式,提出當下最好的解決方法,這個婚由他代結,既能不毀傅家的名聲,也能保住路家的面子。
他并未步步,給了時間讓考慮清楚,家里人當然同意,那唯一的決策權自然就到了手上。
被這事兒磨得心力瘁,晚上泡溫泉時,不知怎麼就“恰好”遇到他,晚上總是易沖,緩緩游到他的湯池里,然后問:“那結婚前我可以看你的檢報告嗎?”
在傅的事上栽了跟頭,開始覺得上流圈的男人一個都信不過,不管外部風評怎樣,誰知道本人是不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還是要自己了解才靠譜——傅不就是麼,所有人都說好,誰知道玩那麼花。
但那時他答得很快。
“可以。”他目很坦率,在霧氣中有出其不意的直白,“不過你不用擔心,我是男。”
……
現在想來,從那時候就能看出他這張口無遮攔的了。
當時怎麼看都覺得這人極有責任心,庇護堂弟、全傅家,四平八穩八風不地,一點兒也看不出有別的企圖。
老男人,果然很會裝。
Advertisement
休息的中途,有服務生前來送水,見到時明顯驚了一驚,但很快掩住,禮貌微笑著遞來一杯煮好的荔枝茶,這才離開。
路梔小聲問:“他為什麼好像被我嚇到的樣子?”
他在喧嘩聲中不聲地靠近,輕輕一的手。
“大概是因為,這個專屬的位置空缺了兩年,第一次有人出現。”
眨眨眼。
“你走的太快,找不到辦法聯系你,以為你喜歡聽這個樂隊,就在他們每次演出的時候給你送票。”
路梔緩了會兒:“那你送到哪兒呢?你又不認識我。”
“對面咖啡廳,”他講得隨意,“最后看到你是在那兒消失的。”
如果等會兒過去,大概能收到不過期票。
“可是……咖啡……”恍惚,“萬一我只是路過呢?”
他笑:“你應該確實只是路過,因為這里從來沒有人上座,偶爾我自己來聽,邊也沒人出現過。”
“那你還送?”
“是啊。”
在這瞬間反應過來什麼,這是一種別無他法的刻舟求
劍,他也知道不行,但,萬一呢。
路梔不可置信:“你這麼明的人,居然會做回報率這麼低的事。”
他抬了抬眉:“很意外?”
點頭:“很意外,在我的預設里,你應該是那種‘錯過就算了’的人。”
“算不了,”他說,“怎麼能算了?”
“如果再等不到你,按照我的計劃,今年就不會送票了。”
“嗯?”
“我會去找你,”他肯定地說,“直到找到你為止。”
命運預設出截然不同的兩條路,但不管走向哪一條,相遇的結果,都是必然。
路梔后來在咖啡廳拿到了所有已經過期的門票,厚厚五十多張,一張也沒掉。
“你一個人看過多場啊?”
“記不清了。”
Advertisement
路梔撇一撇,“你別這樣,這樣搞得我還愧疚的。”
“什麼?”他偏頭靠過來,“寶寶說要補償我?”
“……”
我沒說!
*
次日下午回家的時候,聽宗叔說他已經回來了,家里還有客人。
客廳沒看到人,最終在調酒室里聽到聲音。
調酒室遮天蔽日,關上門后暗一片,只有微弱的橘燈點落,靠外的位置,延展出一塊巨大的理石吧臺,是聊天品酒的地方。
傅言商正半陷在沙發里,握著一只冰山紋的玻璃杯,威士忌被喝到只剩淺淺一層,紐扣解開兩顆,領折散,正笑著跟他們聊天,不知道是講到什麼。
大概是聊天到了尾聲,沒一會兒,井池和陸承期就先走了。
“你還要喝嗎?”路梔在想要不要給他留私人空間,“那我也出——”
忽然被人勾住腰肢,沒站穩,直接跌坐在他上,他輕而易舉地找了個舒服的姿勢,托著后頸問:“去哪兒?”
“就,”忽然屏息片刻,“外面,等你啊……”
“在這兒陪我。”
他講得不由分說,路梔開口正要問我待這兒干嘛,下一秒,腳踝被人住。
他輕輕著,有慢條斯理的緩:“外面不冷麼?”
“冷的,”料想他應該是在說自己子穿得短的事兒,“但是室暖和,外面套了厚的……”
他嗯一聲,過酒杯的指尖很冰,費盡心思勾住的拖鞋,在轉弄間從足尖褪下。
啪嗒。
路梔攀著他肩膀,手指一下,然后問:“你還喝酒麼?”
“不喝了。”
“但還有這麼多冰塊——”
起先只是想找個話題,來分走自己在他指尖上傾注的過分的注意力,但似乎是被提醒,他偏過來,雪松木的香氣混合微醺的酒意,危險馥郁:“不能浪費,是不是?”
Advertisement
不知道他在問什麼,但本能只好點點頭,路梔又起來了些,覺得沙發的角落太悶,不承認是他作所致:“好熱。”
靠的調酒室是低溫,外面卻有暖風,就抵著出風口,暖烘烘地像要被吹起。
他好像在笑:“我腳踝就熱這樣?”
“不是,是風——”
話沒來得及說完,小忽然一冰,嗚咽出聲音,幾枚冰塊正在他指尖靈活地游走,在皮上,蜿蜒行。
四四方方的冰塊剛剛化開,有層水做阻擋,他手指把控得剛剛好,降溫的冰,卻不難,奇異的升起,全然未知的領域,心臟砰砰跳著,手指收,微微仰起頭來。
中被喂進一口烈酒,嗆得厲害,也隨之升溫,外降溫的冰與之緩沖,像在冰面又被火環繞,腳踝輕輕晃著。
“寶寶,不了和我說。”“……嗯。”
指尖向上,抵達小時,冰只剩一半,服帖地落進他掌心,隨按嵌進皮,鈍角的顆粒,像被打的紙張,一點點滲。
足尖全繃到一,可憐地蜷著,實在涼,但也實在解暑。
路過膝蓋。
忽地上拱,腰間扣住的大掌收,他聲線沉了沉,挲著:“怎麼沒穿安全?”
說不是:“回家掉了啊……”
神經愈發敏,一點溫度變化都能帶起不絕的漣漪,害怕:“不行,不行……”
他安親一親角:“嗯?”
“冰塊,不行……”
第一反應以為他是要送冰塊進去,得厲害。
“沒有,”他笑,“早化完了,你看看,哪兒還有?”
才不看。
百褶短遮住,他停了會兒,像是忽然轉念,跟接了個輾轉的吻。
他說:“怎麼還知道這個?都是在哪兒看的?”
Advertisement
“……”
“小說,”嘟噥,“你不也知道……”
又吻下來。
手指換了位置,攥住他領一團,這個習慣還是沒能改掉,他指尖太冰了,被親出連續不斷的鼻音,說不清是在抗議還是回應,沒一會兒,他著,像是單純好奇:“寶寶怎麼這麼暖和,一會兒就含熱了?”
……
憤死,捂住他,手指下的五卻忽然隨著用力,下抵著發起抖來。
“好了,”他安著沒撤開,替延長覺,“酒嗆嗎?”
搖搖頭,綿綿地丟了力氣,腰間的手上來托住腦袋,稍一用力,腦袋跟著晃兩下。
他像是得了趣,看腦袋隨自己掌心擺,有氣無力地喃喃:“這麼好玩嗎……”
“好玩。”
頓了一下,意識到這話有歧義,他補充:“都好玩。”
“……”
合上眼皮,也沒做什麼,但就是累得厲害,暈暈地像是缺氧,沒一會兒靠著他睡著,似乎沒睡多久,聽到哪兒傳來的靜,還以為是門被推開了,一個激靈,睜開眼。
“醒了?”
視線所及仍是暗的黑,燈很淡,門沒被人推開。
路梔點點頭,正要從他上下來,一,被他止住:“別踩到。”
低眼一看,地上滴滴答答地匯一灘。
他視線也跟過來,要笑不笑地問:“怎麼這麼多?”
“……”
僵在那兒一不敢,顯然是沒預料到這個場面,像個稻草人直直地矗在那兒,半晌訕訕:“……聽不懂。”
“哪兒不懂?”他笑起來,慢條斯理地,緩緩用腳尖踩過那灘,發出輕微的聲響,“就是冰塊全化了啊,化了好多,是不是?”
“……”
他很有就地附過來:“寶貝想什麼了,讓我聽聽?”
路梔鼓,用手肘推一把他,“我沒想——”
“好了,”不逗了,他道,“過完年再忙一陣我可以休息,要不要去芬蘭看極?”
*
二月底,他們出發前去冰島。
路梔特意提前做了攻略,剛進房間時還很興,盈盈白雪中的獨棟玻璃屋,他大概提前吩咐布置過,三面都環了起來,以確保私,只有一面正對著森林和天空,抬頭就能看到——
順著抬起頭來,然后頓住。
……
鏡子。
等下,頭頂怎麼會是一整面,高清的,連表都分毫畢現的,鏡子?
轉過頭,看向傅言商:“酒店安排的?”
“當然不是。”
“……”
他抬了抬眉:“你之前不是讓我自己去做功課?”
路梔一時語塞:“那,我是讓你去了解一下,又不是說要實踐……”
“了解了,但不實踐,不是相當于白了解?”他有道理,“我不做無用功,寶貝。”
“……”
不行,沒法跟他繼續這個話題,的腦子的幻想能力太恐怖了,是抬頭和他在鏡子里對視都覺得要去了半條命。
路梔低頭跟個鵪鶉一樣清東西。
十點多,他洗完澡從浴室出來,見已經很期待地坐到了玻璃前,在等極。
他了頭發,道:“現在估計還沒有。”
路梔:“是嗎?”
聲音從頭頂傳來,坐著他站著,路梔很自然地抬起頭,然后在看到鏡子的下一秒,又緩緩撤回了一道視線。
盯手指,顧左右而言他:“那大概在什麼時候?”
“一個半小時,”說到這兒,他頓了一頓,似乎有新的靈,“正好可以做著等。”
路梔:??!
“不好麼?”他好整以暇征求意見,“干看極多無聊,會困。”
路梔:“……”
你好有道理啊。
你是不是有一套自己的邏輯系統?
說到這兒,后的聲音停了。
他很有耐心地完頭發,然后將一把從墊子上拉起:“準備好了沒有?”
路梔回頭,有點兒茫然:“準備什麼啊?”
他笑一聲,抵住的玻璃上彌漫開一片白霧氣。
“一會兒要抬頭的,寶貝。”!
猜你喜歡
-
完結66 章

他只對她溫柔
你已經是我心臟的一部分了,因爲借走的是糖,還回的是心。—— 宮崎駿 文案1: 請把你的心給我。—— 藍晚清 當我發現自己愛上你的時候,我已經無法自拔。 —— 溫斯琛 愛上藍晚清之前,溫斯琛清心寡欲三十年,不嗜賭,不.好.色。 愛上藍晚清之後,溫斯琛欲壑難填每一天,賭她情,好.她.色。 文案2: 在T大,提起生物系的溫教授,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姓溫,但人卻一點溫度都沒有,高冷,不近人情,拒人千里。 但因爲長得帥,還是不少美少女貪念他的美色而選修他的課,只是教訓慘烈,一到期末,哀嚎遍野。 後來,大家都明白了,溫教授?適合遠觀,不適合褻玩。 然後,學校貼吧一個帖子火了,「溫教授性子冷成這樣,做他女朋友得有多慘?」 底下附和聲一片—— 不久,學校貼吧另一個帖子也火了,「以前說心疼溫教授女朋友的人,臉疼嗎?」 底下一溜煙兒的——「疼!特碼的太疼了!」
19.7萬字8 16870 -
完結453 章

閃婚禁欲保鏢野又撩!好心動上頭
【驕矜明豔大小姐VS冷酷禁欲係保鏢】【閃婚 先婚後愛 追妻火葬場 雙潔】傅西洲缺席訂婚禮那天,司棠棠成為了全城笑柄。她宣布取消婚約,轉身上了顧硯深的床。顧硯深是她保鏢,冷酷禁欲、不近女色,一向厭惡女人占他便宜。清醒後,她準備給他一筆錢當作補償,男人卻強勢求婚:“大小姐,嫁給我,以後我護你周全!”本以為隻是一場協議婚姻,沒想到婚後他卻寵妻成狂,撩她、勾她又纏她。-失去司棠棠後,傅西洲後悔了,想要重新追回她。告白那晚,他看到她被男人摟進懷裏:“大小姐,親一下。”“顧硯深,收斂一點。”男人低聲誘哄:“乖,叫老公。”“老公~”傅西洲目眥欲裂,上前質問她為什麼嫁給一個保鏢?當天晚上,傅家就接連損失了好幾個大項目。-傳聞,A國總統府的太子爺低調又神秘。司棠棠拿到國際影後大獎那天,受邀到總統府參加宴會。她不小心看到了一幅油畫。女人膚白貌美,天生尤物。那不正是她嗎?油畫下寫著一行小字:暗戀不敢聲張,思念爬滿心牆。“大小姐,你看到了?”男人走過來,將她從身後擁住。她心慌意亂,不知所措。“顧硯深,我們說好的,隻是協議夫妻。”男人俯身下來,親得她眼尾泛紅,“大小姐,愛我好不好?”#蓄謀已久##男主暗戀成真#
86.3萬字8.18 97876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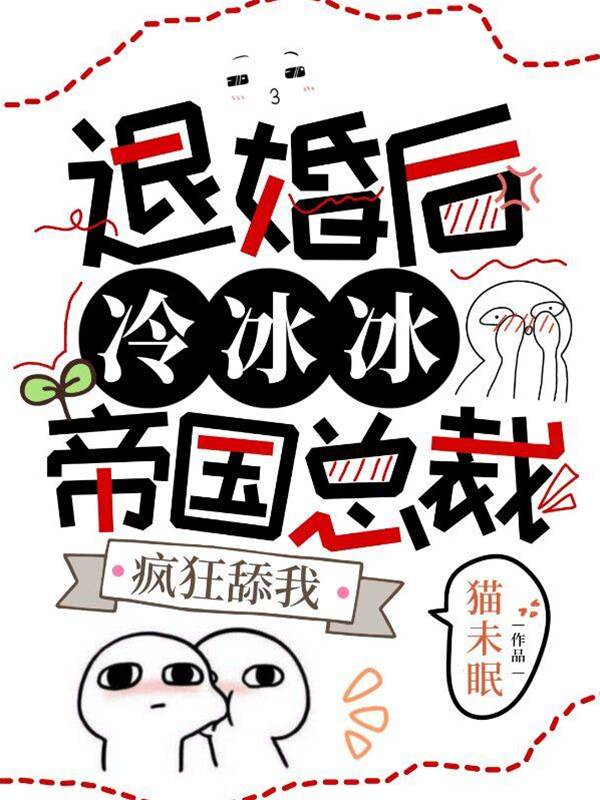
退婚後,冷冰冰帝國總裁瘋狂舔我
退婚前,霸總對我愛答不理!退婚後,某狗他就要對我死纏爛打!我叫霸總他雨露均沾,能滾多遠就滾多遠。可霸總他就是不聽!就是不聽!就非要寵我!非要把億萬家產都給我!***某狗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伸手扶額,終於凹好了造型,淡淡道,“這麼久了,她知錯了嗎?”特助尷尬,“沒有,夫人現在已經富可敵國,比您還有錢了!”“……”
29.4萬字8 16470 -
完結250 章

錯撩後,總裁失控
父母雙亡後,蕭桐羽被寄養在從小有婚約的林家。高中畢業那一天,她看到暗戀多年的林家少爺和校花翻雲覆雨,果斷轉身離開。大學畢業後,爲了小小的報復心,蕭桐羽進入季氏,成爲了帝都首富季允澤的貼身祕書。季允澤是帝都最高不可攀,令人聞風喪膽的黃金單身漢。撩人成功那晚,蕭桐羽後悔了,她哭着求饒,季允澤卻沒有放過她。“一百萬給你,買避孕藥還是打胎,自己選。”“謝謝季總。”後來,季允澤撕爛了蕭桐羽的辭職信。“你敢跨出這個門一步,我讓你在帝都生不如死。”再後來,季允澤被人拍到蹲在地上給蕭桐羽繫鞋帶,大雨淋溼了他的身子。“季總,這熱搜要不要撤下來?”“砸錢讓它掛着,掛到她同意嫁給我爲止。”
47.2萬字8.33 1082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