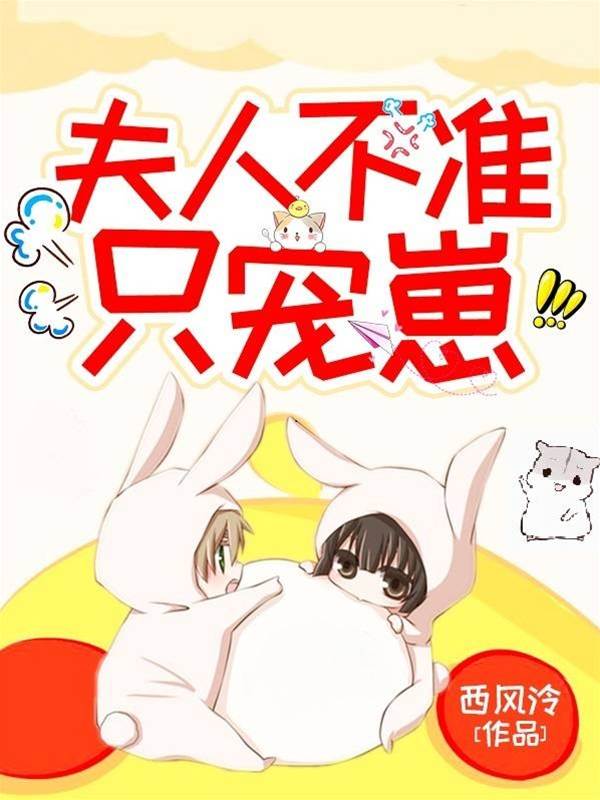《破產后,大佬千億哄她領證》 第599章 番外一:月亮在天上,你在我心里
金秋十月的帝都,最轟的消息莫過于秦夫人的去世。
纏綿病榻十余載,幾度傳出重病院生命垂危,可每一次都化險為夷。
有人說秦夫人運氣好,連死神也憐惜,一次又一次的放過。
還有人暗的說,不蒸饅頭爭口氣,就算只剩一口氣,也得熬走姚晚螢再死。
誰都知道后者不可能。
畢竟,姚晚螢年紀比秦夫人小,也比秦夫人好得多。
這麼多年了,帝都豪門里無數人等著看秦家的大戲。
看是姚晚螢先耗死秦夫人為上位。
還是秦夫人超長待機,熬到姚晚螢敗北。
先是四月里,姚晚螢悄無聲息的消失在了帝都。
再是十月收到秦家的吊唁通知。
哪怕只多活了半年,可在帝都眾人眼里,秦夫人儼然是贏了。
秦夫人頭七當日,秦氏集團東大會上,秦仲嵩正式卸任。
即日起,秦煜琛為秦氏集團掌權人。
一個月后,就在眾人都淡忘了秦家接二連三的八卦后,一架帶有秦氏集團lo的專機從帝都機場直飛紐約。
有人宣稱在紐約機場見到了秦仲松。
還有人想起在紐約豪門的宴會里見過珠寶氣的姚晚螢。
消息流通起來,眾人驚掉了一地的眼珠子。
爭了半輩子,可誰能說得清,秦夫人和姚晚螢到底誰贏了?
一筆糊涂賬罷了!
梨山公館的客廳里,秦楚著葉梨高高隆起的肚子,一臉的歉疚,“梨子,對不起,我可能要食言了。”
葉梨預產期是1月初。
Advertisement
按秦楚的個,10個小時的飛機,小菜一碟。
別說刮風下雪,就是天上下刀子也一定回來陪葉梨生孩子。
不怕奔波。
可葉梨不肯,滿目戲謔,“你等著瞧吧,你這次回到慕尼黑,你家陸總肯定沒有好果子給你吃的!你瞞了這麼大一個消息,還瞞了他整整一個月,我保守估計,未來一年,你都別想離開他的視線了。”
秦楚……
姐妹二人膩歪了一下午,吃完晚飯的深夜時分,傅厭辭開車載著葉梨,把秦楚送到了帝都機場。
帝都直飛慕尼黑,10個小時就到了。
即便如此,葉梨依舊拉著秦楚的手千叮嚀萬囑咐。
秦楚一臉求救的看向傅厭辭。
“那你一路多注意,飛機落地見了奚洲,給我們報個平安!”
傅厭辭攬過葉梨,夫妻二人沖秦楚揮手。
起飛時顛簸。
降落時顛簸。
秦楚雙手握著座椅扶手,張的心都在。
耳聽廣播里說飛機已經平安抵達慕尼黑,謝乘客們對漢莎航空的支持,秦楚回頭看到窗外漆黑的夜空,高懸著的心這才緩緩平落。
下一瞬,手機叮咚輕響。
接機口
5月傅爺和梨子婚禮,秦楚和陸奚洲都在帝都。
之后,兩人如從前商量過的,在帝都住了幾個月。
期間,陸奚洲還回泗城看了一趟他爸媽。
九月初慕尼黑的項目上線,陸奚洲依依不舍的告別車場事宜沒理完的秦楚,一步三回頭的先走了。
接下來的一整個月,陸奚洲都在暴躁催促和卑微祈求中無限切換。
Advertisement
每天一催陸夫人,你還要不要你男人了?
每日一祈求老婆,我想你了,你早點回來好不好?
然而每天,秦楚都有不能出行的花樣理由。
今天是已經約好了梨子陪去做產檢。
明天是車場某車手結婚作為老板要過去隨份子。
后天是老黃歷說今日不宜出行。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到十月行程要定了,秦夫人去世了。
陸奚洲……!!!
換做從前,秦楚是不會去的,也沒理由去。
畢竟秦夫人不是秦仲松。
秦仲松是生學意義上的爸爸,哪怕這麼多年都沒過他一聲爸,可他真要出什麼事,于于理都得出現。
可秦夫人不一樣。
但是秦楚沒想到,秦煜琛托了人,秦仲松也打了電話。
父子二人的態度出奇的一致一筆寫不出兩個秦字。
秦楚知道為什麼,不是因為姚晚螢不在帝都,秦家人沒威脅了。
也不是因為秦煜琛既往不咎放過了。
是因為是傅夫人最好的姐妹,傅爺認證過的大姨子。
歸結底,他們是為了傅厭辭。
無論是因為姚晚螢,還是葉梨,秦楚都不會去。
可傅厭辭不知說了什麼,秦楚去了。
不但秦楚去了,傅厭辭和葉梨也去了,自始至終,在哪兒,葉梨就在哪兒。
而傅厭辭的目,始終不離葉梨左右。
吊唁過后,帝都豪門里的一眾人看明白了。
秦楚這秦家二小姐的份,未必會認。
但是傅爺大姨子的份,是確定了沒跑的。
Advertisement
于是乎這一耽誤,就耽誤到了現在,生生比陸奚洲給定下的啟程日期晚了一個月。
輕裝便行,秦楚連行李箱都沒帶,只隨一個小包。
接機口的位置,陸奚洲只一眼,臉就變了,“怎麼著?您這是來我這兒度假來了,過幾個月就又打算回去是怎麼著?”
“對啊
!”
秦楚點頭,“梨子1月的預產期,我怎麼著12月得回去吧?反正就兩個月,行李帶不帶都無所謂。”
陸奚洲的臉徹底黑了。
誰能想到,當年萬花叢中過的他,有朝一日會變妻石呢?
果然,一報還一報,蒼天饒過誰!!!
一個多月的日思夜想,在這一刻,因為兩個月后的分別盡數化了郁結。
陸奚洲的郁悶憋屈寫滿了整張臉。
直到進了家門都沒好。
而最郁悶的,是秦楚好像沒有要哄他的意思。
“陸奚洲,這就是咱們以后的家了嗎?”
“陸奚洲你眼真不錯!這房子我喜歡,還有這沙發……”
這棟別墅是陸奚洲選了半個多月才選好的。
雖然不是新房子,可只一眼他就確定,是秦楚描述過的,夢里的、他們的家的模樣。
白的三層小樓坐落在巨大的綠草坪上。
周圍綠樹環繞。
一眼看去,仿若綠野仙蹤里的木屋。
別墅前的苗圃里,五六的花朵競相開放,蝴蝶蹁躚蜂嗡嗡。
別墅后的大片草地上,稀疏的白花朵仿若灑落一地的珍珠,若若現的好看。
看看廚房。
再看看落地窗后郁郁蔥蔥的綠。
Advertisement
噠噠噠的腳步聲仿若歡快的鼓點,秦楚順著蜿蜒的樓梯上了二樓。
陸奚洲準備了好幾天的話連開口的機會都沒有。
憋死他了!!!
解開西裝外套丟在沙發上,走出幾步覺得不對,又返回來抓手里。
陸奚洲一邊解著領帶一邊上樓,直到進了臥室,才將外套掛在架上。
再抬眼,就見秦楚輕車路的從柜里翻出家居服,跑去試間換了。
再坐回床上,秦楚偎進陸奚洲懷里,了他的口,“陸奚洲,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你想先聽哪個?”
陸奚洲眉梢輕挑,“壞消息不就是咱倆只能做兩個月的月夫妻,然后你就要離我而去了嗎?”
秦楚搖頭。
陸奚洲一怔。
就見秦楚板起臉道“我……不太舒服。醫生說,接下來的一年,要……要。還有,要保持心態平和,飲食也要調理。所以……”
幾乎是秦楚說不太舒服的那一秒,陸奚洲就有種心跳停止的覺。
“嗐,我當多大的事兒呢……”
秦楚低垂著頭,看不清臉上的表。
陸奚洲握了下拳,將摟進懷里哄道“別說一年,只要你好好兒的,一輩子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老婆,醫生……”
聲音帶著一輕,陸奚洲翻過看著秦楚的眼睛問道“醫生說,是什麼況?需要我做什麼?”
“錢我有。雖然只有幾千萬,但是你放心,無論多錢,咱該花就花!我這兒沒有,我還可以跟傅爺借!……再不濟,大不了回去繼承家業,我跟老頭子服個。他們就我一個兒子,不會狠不下心來不管我的。你放心,老婆,我不會不管你的!”
“時間我更是大把的。你放心,以后我哪兒都不去,就陪著你,好不好?”
“老婆,你別嚇我……”
說著說著,聲音都哽咽了,陸奚洲眼睛有些紅,“你……你到底怎麼了?”
秦楚很想笑話一下陸奚洲,問問曾經那個放不羈天塌下來還有個兒高的人頂著的陸哪兒去了。
可這會兒,笑不出來。
“陸奚洲你怎麼那麼傻啊?”
手抱他,秦楚拉著他的一只手覆在了肚子上,“親的,你要做爸爸了!”
???
!!!
眼淚都快要出來了,峰回路轉。
陸奚洲呼吸一滯,再看向秦楚,磨刀霍霍,“秦楚楚!!!所以你不想回來的真實原因就是這個吧?”
什麼葉梨產檢車手結婚老黃歷的,分明就是早孕期不易顛簸。
大腦有片刻的空白,陸奚洲猛地坐起了。
看看秦楚。
再依舊平坦的小腹。
陸奚洲怔怔的,“我,我要做……做爸爸了?”
秦楚笑著點頭。
反應半天,陸奚洲紅著眼圈抱住了秦楚,“老婆,謝謝你!”
前一刻還擔心秦楚得了什麼不治之癥,連萬一治不好,他就什麼都不要了帶著環游世界的路線圖都想好了。
這一刻得知什麼事都沒發生。
而他即將擁有一個崽。
短短幾分鐘,心從地下到天上,陸奚洲有種歷盡滄桑的劫后余生。
十月懷胎,一朝分娩。
翌年5月19號,秦楚在慕尼黑醫院生下了兒子陸一諾。
生孩子的過程過于揪心,雖然秦楚說沒那麼痛,可陸奚洲不傻。
他看了那麼多的書,書里講了陣痛的等級。
他還看了那麼多視頻,視頻里有生孩子的痛苦全程。
更別說,等在產房門外時,那一聲聲的“陸奚洲”。
這樣的痛苦,經歷
一次就夠了。
說什麼也不要第二次了。
可秦楚不干。
小時候,跟著姚晚螢顛沛流離,永遠都是自己一個人玩。
回到帝都,秦家的人排斥,帝都豪門圈子里的人也瞧不起。
邊只有一個梨子。
曾經以為孑然一,這輩子能活一天是一天,多活一天都是賺了。
遇到陸奚洲,是的福氣。
打從兩人在一起的那天,秦楚就想好了,要生至兩個孩子。
最好是兄妹。
猜你喜歡
-
連載942 章
陰婚不散:鬼夫大人狠狂野
繼承奶奶的祖業,我開了一家靈媒婚介所。一天,我接了一單生意,給一個死了帥哥配冥婚,本以為是筆好買賣,冇想到卻把自己搭了進去。男鬼帥氣逼人,卻也卑鄙無恥,鬼品惡劣,高矮胖瘦各種女鬼都看不上。最後他捏著我的下巴冷颼颼的說:“如果再找不到合適的對象,你就要自己上了。”我堅決拒絕,可惜後來的事情再也由不得我了……
168.7萬字8 10233 -
完結71 章

第二春
【1】林念初愛慘了梁辰,倆人相戀七年,結婚三年,梁辰卻出了軌,小三懷孕上門逼宮,林念初毫不留情直接離婚,從此之后看破紅塵、去他媽的愛情!程硯愛慘了心頭的朱砂痣、窗前的白月光,然而卻被白月光虐的死去活來,從此之后看破紅塵、去他媽的愛情!某天晚上,林念初和程硯在某個酒吧見了面,兩個去他媽愛情的單身青年互相打量對方,覺得可以來一場,于是一拍既合去了酒店。一個月后林念初發現自己懷孕了,和程硯商量了一下,倆人決定破罐破摔,湊合一下過日子,于是去民政局扯了證。【2】某...
31.1萬字8.38 55510 -
完結10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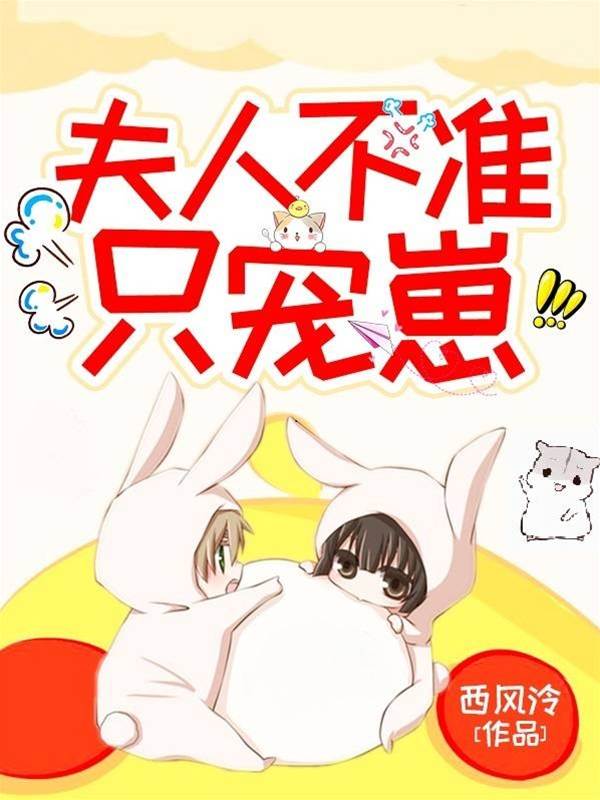
夫人不準只寵崽
南悠悠為了給母親治病為楚氏集團總裁楚寒高價產子,期間始終被蒙住眼睛,未見楚寒模樣,而楚寒卻記得她的臉,南悠悠順利產下一對龍鳳胎,還未見面就被楚家接走。
24.6萬字8 7964 -
完結150 章

許你一片深情海
【小甜餅+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蓄謀已久+男女主嘴毒且損+追妻火葬場+雙潔】*英姿颯爽女交警x世家混不吝小公子*所有人都以為京北周家四公子周衍喜歡的是陸家長女陸蕓白,結果他卻讓人大跌眼鏡地娶了妹妹陸苡白,明明這倆人從青春期就不對盤。兩人三年婚姻,過得談不上好,也談不上壞。一個不上心,一個看似不在意。陸苡白以為這輩子就糊糊塗塗地和周老四過下去了……結果陸苡白卻意外得知當年婚姻的“真相”,原來周衍比所有人以為的都要深情,不過深情的對象不是她而已。 他是為了心愛的人做嫁衣,“犧牲“夠大的!睦苡白一怒之下提出離婚。 * 清冷矜貴的周家四公子終於低下高昂的頭,狗裹狗氣地開始漫漫追妻路。 陵苡白煩不勝煩:“周衍,我以前怎沒發現你是一狗皮膏藥啊?“ 周行:“現在知道也不晚。我就是一狗皮膏藥,這輩子只想和你貼貼。“ 睦苡白:“.好狗。
27.2萬字8 84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