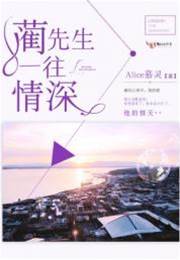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幸得婚後相遇時》 第430章 我不想做他妹妹了
晚上吃過飯,我給小泗打過去電話,但是沒接。
想想不放心,我又打給了江翱,我問他小泗有沒有過去找他,他說有,不但來找了,還把他拳打腳踢了一番。
我馬上問他:“你沒事吧?”
“沒事,不會真的打。”江翱說:“你跟說了?”
“我和賀雲開說話的時候被聽見了,最近正在跟賀雲開離婚。”
“跟我可不是這麽說的,說謝謝我的安排,我為安排的非常好,給找到了如意郎君,所以決定不辜負我的期,幸福滿的和賀雲開生活下去。”
“是在說氣話。”
“我知道。”江翱笑著說:“從來沒有見過小泗這麽生氣,不過生氣起來也好可。”
“也隻有你覺得可,現在人呢?”
“我不知道,跟我吼了一通之後就走了。”
“要不然你去家裏看看他吧,我有點不放心。”
“賀雲開回去了,剛才我在花園裏看到他的車剛開過去。”
“那你隨時關注,有什麽事給我打電話。”
我掛掉了電話,回過頭,鬱冬就站在我的後。
Advertisement
我把電話放起來,不鹹不淡地跟他說:“什麽時候對聽壁腳這麽興趣?”
“羨慕有朋友的人,每天管閑事就不亦樂乎。”他語氣涼涼的。
“對了,你好像沒有什麽朋友?”我仰起頭看著他。
“我不需要朋友。”他聳聳肩。
這時隔壁傳來了關門聲,鬱冬立刻就走出去了,我聽到他和鬱歡的對話從走廊裏傳進來。
“去哪裏?”
“跟朋友約好了出去玩呀。”
“大晚上的去玩什麽?留在家裏哪也不要去。”
“哥,你也太專製了!”鬱歡跺著腳道:“現在才7點多,你憑什麽不讓我出去?”
“總之晚上不可以出去!”
“哥,你一點自由都不給我,整天把我關在家裏,就像坐牢一樣!”
“反正就是不給出去。”
“砰。”的一聲巨響,鬱歡摔門回房間了。
鬱冬這個哥哥我不知道做的是否稱職,但是他的控製未免也太強烈了一點。
鬱冬也回到房間,我知道我不該管他們兄妹倆的事,但我聽到隔壁傳來了鬱歡歇斯底裏的哭聲。
“現在才七點,十點鍾回來就好了。”我對鬱冬說:“都那麽大了。”
Advertisement
他站在窗邊看著漆黑的窗外:“隻要天黑了,就有無盡的危險暗藏著,誰知道會發生什麽?”
“難道你永遠不讓晚上出門,你關不住一輩子的。”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他關了窗戶轉過:“不必管,哭一陣子就好了。”
鬱歡哭了好久,我於心不忍,去隔壁看。
正趴在床上哭的稀裏嘩啦,我擰了一條巾給,抬頭看我一眼,接過了巾胡了一把。
我在邊坐下來,拍拍的肩膀安道:“別哭了,你想去哪裏,我陪你去?”
“這種日子不知道還要過多久。”泣著道:“你總不能每次晚上我要出去的時候都陪我去。”
“可能以後他不會這樣了。”
“隻要我是鬱歡,他就會一直管我,不讓我晚上出門,我和誰往他也要管,不論男的還是的,還有我平時去上學,他還要配保鏢跟著!”鬱歡說著說著又哭起來,越哭越激:“我不想當他妹妹了,我寧願我還在外麵流浪,我寧願我吃不飽穿不暖,但是我有自由!”
鬱歡是氣糊塗了吧,我怎麽覺得的話裏有語病?
Advertisement
我剛想說話,門被推開了,鬱冬鐵青著臉站在門口:“鬱歡!”
抬起頭,臉一下子就煞白了,然後把被子拉到頭頂,繼續嚎啕大哭。
鬱冬走過來拉走了我:“不用理,你越勸越來勁。”
“你別太狠了...”
“你能保證晚上跑出去不會遇到危險嗎?”
“哪有那麽多危險...”
“十四歲的那年,晚上跟同學出去玩,被人綁架了。”
我猛的噤聲,呆若木地看著他:“然後呢?”
“費了很多的周折,才把救回來。”
我好像可以理解為什麽鬱冬對管教這麽嚴,原來是發生過那樣的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隔壁鬱歡的哭聲漸漸小了,對於鬱冬來說,這個來之不易的家人他格外珍惜。
臨睡前,小泗發來信息,告訴我幾個字:“賀雲開簽了離婚協議書。”
我不知道該不該恭喜,我也不知道賀雲開怎麽一下子就想通了。
第二天早上和賀雲開去離婚,我問二嬸他們知道嗎,小泗說:“先斬後奏吧,至於賀總那裏你先別風聲,我們辦完手續自己跟他們說。”
Advertisement
那是他們的事,我才不會多,我又不傻。
上午十點多的時候,小泗發給我一張圖片,絳紅封麵的離婚證。
我問:“賀雲開還好嗎?”
“看上去還好。”
“那江翱呢,你什麽時候去找他?”
“我昨天揍了他一頓。”
“傅泳泗,把握好你的,這次別錯過了。”
“切。”
掛掉了電話,這時賀總敲開了我的門,走進來莫名地跟我說:“不好意思,傅總,打擾一下啊,剛才雲開跟我說他和小泗離婚了,這是怎麽回事?”
我隻能裝傻白甜,表比他還要傻:“為什麽?”
不知道是不是我演的太像了,賀總居然相信了我什麽都不知道,唉聲歎氣地走出了我的辦公室。
猜你喜歡
-
連載1164 章
穿到跟殘疾大佬離婚前
遲清洛穿進一本狗血小說,成了商界殘疾大佬作天作地的小嬌妻。小嬌妻驕縱任性,飛揚跋扈,還紅杏出牆。遲清洛穿來當天,原主正因為爬了娛樂圈太子爺的床上了熱搜。大佬丈夫終於同意跟她離婚。遲清洛:“老公我愛你,之前跟你提離婚是我一時糊塗。”輪椅上的大佬眸色深沉:“你糊塗了很多次。”不不,從今開始,她要改邪歸正,渣女回頭金不換。可是漸漸的大佬好像變得不一樣了,對她說抱就抱,說親就親。嗯?大佬不是淡薄情愛,隻把她當擺設的麼?遲清洛眨眨眼:“好像有哪裡不對。”大佬將小嬌妻圈入懷中,指腹摩擦著她的唇珠,聲音嘶啞:“哪裡不對?”
104.7萬字8 56328 -
完結845 章

寵婚入骨
許家多年前送去鄉下養病的女兒許呦呦回來了,回來履行與林家的婚約婚禮前夕新郎逃婚去國外找他的白月光,眾人:哇哦……【吃瓜表情】許呦呦:哦豁。下一秒,白皙細軟的小手攥住男人的衣袖,甜糯糯的語調:“墨先生,您可以娶我嗎?”……墨深白商業巨擘清心寡欲,神秘低調,在波雲詭譎的商場叱吒十年,無一家報刊雜誌敢刊登他的一張照片,也沒有一個異性能讓他多看一眼。所有人都說墨深白娶許呦呦一定是協議婚姻,一年後絕對離婚。許呦呦津津有味的吃著自己的瓜,只是吃著吃著就發現好像不對勁啊。逛街購物不需要買單,吃飯不用點餐,不管走到哪里大家熱情跟她打招呼:墨太太好。後來墨深白的白月光回來了,前未婚夫深情表白:“呦呦,只有我是真的愛你,回我身邊,我不嫌棄你。”許呦呦還沒來得及回答被男人霸道的攬入懷中,低音性感撩人:“寶貝,你沒告訴他,這裡有了我們愛的結晶。”溫熱的大掌貼在她平坦的小腹上。許呦呦紅了臉,渣男紅了眼……【無腦瑪麗蘇先婚後愛文|專注虐男二】
142.9萬字8.18 230570 -
完結11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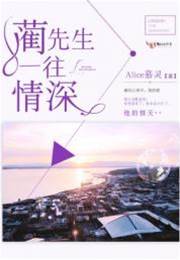
藺先生一往情深
曾有記者舉著話筒追問C市首富藺先生:“您在商界成就無數,時至今日,若論最感欣慰的,是什麼?” 被眾人簇擁,清俊尊貴的男子頓步,平日冷冽的眸難得微染溫色,回答:“失而複得。” - 人人都說她死了,藺先生心裡有一個名字,彆人不能提。 他走她走過的路,吃她喜歡吃的食物,人前風光無限,內心晦暗成疾。 情天眉眼寂淡:有些愛死了,就永遠不在了。 他眼眸卻儘是溫然笑意:沒關係,沒關係。 她的心再冷,他捂暖。 世人隻知商場中藺先生殺伐決斷手法冷酷,卻從不知,他能將一個人寵到那樣的地步。 - 但後來 人來人往的步行街頭,商賈首富藺先生仿若失魂之人,攔著過往行人一遍遍問—— “你們有冇有看到我的情天……” 他的情天,他的晴天。 · ·寵文·
138.8萬字8 78510 -
完結855 章

報告總裁,你老婆又跑了
黑暗中,他鉗住她的下巴,“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她自輕自賤“知道名字又如何?你只要一分不少的把錢打到我卡上就行了。” 本以為拿到錢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當一切沒有發生。 誰知那古怪男人從此卻陰魂不散的纏住了她。
167.7萬字8 38184 -
連載176 章

軍婚撩人:首長大人請深吻
她代替姐姐嫁給了那個據說身有隱疾的年輕軍長。他的寵,他的溫柔霸道,讓她毫無抵抗的臣服。卻原來爾婚我詐,不過是一段遠的要命的愛情。幾年後,她攜子歸來,撩撥的他欲火焚身。他反身把她壓在辦公桌上,“老婆,按照一夜七次的頻率來算,你已經欠我很多了,要不咱們還是先還債吧!”
30.5萬字8 262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