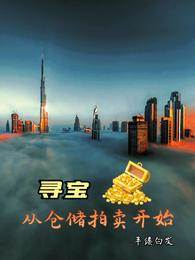《老街中的痞子》 第一千八百六十章 決戰(一百七十二)
張家始終擺出的姿態,像是一匹狼,貪婪,兇猛,狡詐,從來只有他們獲利,不允許別人占到便宜。
今天怎麼一反常態,改變了世準則?
雷牧東是條老狐貍,見慣了綿里藏針,既不激,也沒有寵若驚,而是緩緩說道:“哪里的?張家生意龐雜,涉及到地產,礦業,投資,教育多個領域,有賺錢的,有不賺錢的,那麼多親戚盯著,咱們合作第一筆項目,總不能像盧爺一樣,給塊沒的骨頭啃。”
盧懷遠冽了他一眼。
張纓豹和一笑,將蓋在上的毯掀開,巍巍起,走到雷牧東面前,說道:“我哥哥的,瑞虎集團。”
雷牧東大吃一驚。
盧懷遠又酸又恨。
瑞虎集團主要經營教育和礦業,主要靠關系拿項目,不敢說是張家最賺錢的企業,但也能排到第二第三,況且由張烈虎親手打理,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你掏百分之十的市值,給你百分之二十的份,雷先生,這樣一來,你可以給家里人代了吧?”張纓豹微笑說道。
Advertisement
“能代,能代,代的可好了。”一轉眼,雷牧東憨態可掬,從西洋紳士變了西北老漢,口中都帶著一黃沙味。
“咱們聯盟初興,是要做出點績,否則立不住陣腳,雷先生的苦衷,我深有會。”張纓豹誠懇說道。
“都是一家人,說啥兩家話,只要張公子做到前面,余下的事,包在我上。”雷牧東了眼。
“那雷先生回去差?”張纓豹含笑道。
雷牧東屁顛屁顛離去,腳都利索了幾分。
被晾到一旁的盧懷遠黑著臉,手中的康熙窯茶碗幾碎。
張纓豹關好門,步履蹣跚坐回椅中,一臉肅容說道:“懷遠哥,事態不妙嘍。”
“怎麼說?”盧懷遠挑眉道。
“最新消息,雷斯年拜了云老板的門下。”張纓豹沉聲說道。
“這云老板是哪路神仙,能讓你忌憚?”盧懷遠疑道。
對于張家的勢力,他可是心知肚明,在四九城能橫著走的角,怎麼會害怕一個商人?
“神仙?滿天神佛千上萬,這姓云的,可只有一家。”張纓豹指了指天花板,憔悴的面容充斥著無奈。
Advertisement
盡管盧懷遠對于政治比較遲鈍,順著張纓豹的提示猜想,也意識到了云老板的來歷,驚恐問道:“姓云的那位后代?”
“是。”
張纓豹點頭道:“雷斯年這個人,我還是低估了,盡管已經將他的招式封鎖在搖籃中,可他金蟬殼,又抱住了能撐天的大。不走商道,玩政治,他這一招,我真的沒有料到。有云老板做靠山,咱們做起事難免會畏首畏尾,所以我才不惜讓出份,博取雷牧東的好,增加他的聲,順便讓他快速掌控雷氏集團。只有雷牧東完全掌控雷家,咱們才能抵擋住雷斯年的反攻,否則的話,說不定會前功盡棄。”
“明白了。”
盧懷遠終于理解到了對方的良苦用心,輕聲道:“可百分之二十的瑞虎份,終究便宜了雷牧東。”
“禮尚往來嘛,再說這并不是一筆贈予,而是投資,用幾十億堵住雷斯年的回馬槍殺招,我覺得值。”張纓豹笑了笑,說道:“懷遠哥也學學我,拿出些誠意和甜頭幫助雷牧東,畢竟是聯盟,眼要放得長遠。”
Advertisement
盧懷遠嘆氣道:“不是我不給,是我沒權力給,盧家說了算的,是我父親和叔叔伯伯們,如果拿出盧家的心去填補未知的窟窿,相信他們不會同意。”
“這不是未知,這是即將發生的戰爭。”張纓豹糾正他的措辭,“雷斯年這一步,明顯是拿云老板當作跳板反攻,目前有不雷家的東,是站在他那一邊,包括主家一脈,如果不遏制住他的勢頭,多則三年,則一年,他會將雷牧東徹底擊敗,將咱們攆出西北,之前投資的真金白銀,也會化為烏有。”
“我覺得……你太看得起雷斯年了。”盧懷遠冷哼道。
“那時候的我,已經不在了,僅憑你和我哥,本不是他的對手。”張纓豹長嘆一口氣,說道:“別忘了,他的邊,還有一個能化腐朽為神奇子。”
“我試試吧。”
盧懷遠勉強答應,不屑說道:“那個小癟三,你說的是趙聲?我最看不上他,每次都是靠別人涉險過關,自己有什麼真本事。”
張纓豹苦笑道:“你跟我幾年前的想法一樣,隨便抬起腳就能踩死的角而已,有什麼可擔憂的?但今時不同往日,趙聲屢屢轉危為安,羽翼逐漸滿,已經能對我們構威脅。我特意找高人問過,說趙聲這種氣運加的家伙,是有高人在幫他納德授福,前人的德都被他納為己有。李玄塵那個老不死的,不玩武玩玄,玩的還那麼邪。”
Advertisement
“我前幾天給他做了一個套,幾乎是必死的局面,你猜怎麼著?我那濃于水的大哥,背叛了張家,只為去營救趙聲。現如今警方順藤瓜,把矛頭對準了我,獵人變獵,想想都可笑。”
盧懷遠擔憂道:“對于這種家伙,該怎麼辦?”
張纓豹瀟灑一笑,“我這人,最抵封建迷信。”
猜你喜歡
-
連載1196 章
北境少帥
我要讓這天,再也遮不住我的眼!我要讓這地,再也藏不住我的心!凡我出現的地方,必讓千軍膽顫,萬敵避退!天下戰神,唯遵少帥!
253.7萬字8 28046 -
完結1841 章

都市無雙醫神
未婚妻全家,都嫌棄杜飛又窮又懶。但是他們並不知道,杜飛醫術通神鑑寶無雙,救過富豪無數。
339.1萬字8 907474 -
完結5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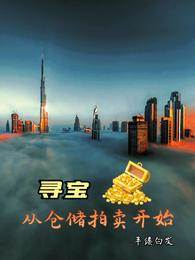
尋寶從倉儲拍賣開始
倒霉留學生李杰因為一次醫療事故,意外獲得了透視能力。美利堅倉儲尋寶黃金惡魔谷淘金深海打撈舊時代寶藏這是一個小人物的成長發家史……
103.5萬字8 27975 -
完結1549 章
最強仙醫奶爸
為了籌女兒的醫藥費,葉雲霄在去賣腎的途中捲入時空裂縫,落入仙界。 三千年修鍊,葉雲霄成為無上仙醫,他橫渡時空之海,九死一生回歸凡間,發現才過了僅僅三天。 他發誓要讓受盡委屈的妻子成為最耀眼的女王。 他發誓要讓被冷落的女兒成為最幸福的公主。 不要招惹我,不管你是什麼首富繼承人還是隱門傳人或是修行大佬,在我面前,你們通通都是螻蟻!
326.4萬字8 103778 -
連載1586 章
隱居三年,出獄即無敵
【熱血殺伐+無敵流+欠債流+裝逼爽文】 三年前,師門被毀,莫海因為一個約定,自廢修為,主動入獄! 三年後,期限已至,莫海以無敵之姿態,強勢回歸,震殺四方! “這一世我要讓天地為我顫抖,我的規矩,就是規矩!” “什麼?! 你說你富可敵國?! “ 莫海看著手中師父留下的一堆欠條,淡淡說了句:”抱歉,我也負可敵國! ”
272.1萬字8.18 86713 -
完結73 章

頂級客服,我受理眾神業務
百鬼夜行,萬妖齊出,人類大廈之將傾。一通神秘電話,鏈接了仙凡之路。文明重啟的希望近在咫尺。照妖鑒、鬆木劍、血誓石,稀世之珍齊出。傳說之建木更於天地中再起!神秘男子手持神器力挽狂瀾!諸天萬界顫抖!有猩紅重瞳探之,久久凝視後開口,“找到你了!”神秘男子一愣,“找我?別鬧!我就一小客服!”
13.3萬字8.18 9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