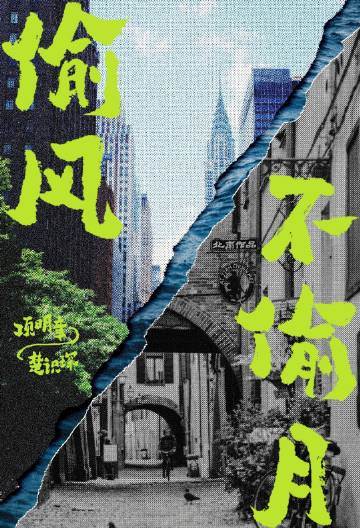《懸日》 第49章 P.孤獨告別
蘇洄醒來的時候,寧一宵已經消失不見了,桌子上留了面包,盤子下著紙條。
[我有點事,要臨時回一趟老家,行李先放著別管,等我回來收拾。你在家注意安全,不要隨便開火,去學校食堂吃飯,按時吃藥,我只去幾天,很快回家。——寧一宵]
他寫得不明不白,幾句話就概括了所有。
蘇洄看完,被一種莫大的恐慌逐漸包圍。他了解寧一宵,如果不是發生了非常重要的事,他不會就這樣離開,至會等自己醒過來。
不確信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確,但對蘇洄這樣的人而言,理智向來是會被所垮的,所以他下一秒立刻撥通了寧一宵的電話,但通話占線,聯系不上。
在網上查詢了去北濱的火車票,只有一個站可以去,于是蘇洄想也沒想,直接打車前往火車站。
十二月的第一天,天空是灰白,車站擁的人群編織出一張巨大的晃的網,令蘇洄不過氣。
今天本應該是他去醫院咨詢的日子,上午十點,他應該在醫院里等待回答醫生的提問。
但他現在反復撥打寧一宵的號碼,人中,被推搡著向前,無數行李箱的滾在地上發出嘈雜的滾聲,痕跡在蘇洄焦急的心上。
在他的神快要崩潰的時候,電話終于打通,寧一宵的聲音聽上去很平常,甚至有些過分冷靜。
“你醒了?有沒有吃東西。”
蘇洄聽到他電話那頭的列車信息播報聲,很明顯在候車廳。
“我在火車站,售票這里,你是哪一班車啊?我現在就買票進去找你。”
他著聲音里的慌張,“我已經進來排隊了,應該買哪里下車的?你發給我吧。”
電話里是停頓,停頓之后,約傳來像是嘆息的細微聲音。
Advertisement
在快要排到自己的時候,蘇洄的手機震了震,傳來了寧一宵發來的信息,他立刻報給窗口的工作人員,但時間門太遲,只買到一張站票,但蘇洄非常滿足。
他終于進了站,在大而擁的候車廳尋覓寧一宵的蹤影,按照他在電話里描述的,蘇洄在接飲用水的角落看到了他。
寧一宵抬頭見他的時候,并沒有笑,看上去沒那麼高興,但蘇洄還是向他跑去了。
他沒有問寧一宵為什麼不醒他,也沒有問發生了什麼,而是在人群里抓了一下他的手腕,很快松開了。
寧一宵抬手,撥了撥他被風吹的頭發,“你是不是穿得太了,臉都吹紅了。”
蘇洄著他,搖頭,說自己一點也不冷。
寧一宵似乎并不想主說自己的事,蘇洄一無所知,也不想他,看了一眼時間門,很快就要檢票。
“我醒來發現你不見了,有點慌。”蘇洄猶疑地開了口,小心詢問,“如果我要跟著你去,你會不高興嗎?”
寧一宵沒有立刻回答,他向蘇洄,勾了勾角,又垂下眼,“當然不會。”
蘇洄看出來,他并不是真的在笑,只是在掩飾什麼。
“不是什麼好事,蘇洄。”寧一宵很平淡地說,“其實不太想讓你看到,但是……”
他停頓了幾秒,并不是為了思考,而是好像沒辦法一口氣說完這些。
“如果你陪我,我可能會好過一點。”
蘇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很想抱住他,所以就這樣做了,在人來人往的候車大廳。
“我會陪著你的,無論發生什麼。”
他是個對未來毫無打算的人,就像此時此刻,為了第一時間門找到寧一宵,什麼都拋諸腦后,一點行李都沒拿,只闖過來。
Advertisement
陪著他上了車,找到座位,蘇洄站在過道里,被來來往往的人來去。寧一宵這時候才知道他買到的其實是站票,于是起把位子給他,但蘇洄拒絕了。
“我不累。”蘇洄故意捶了捶自己的腰,“昨晚沒睡好,坐著更難,正好站一站。”
無論寧一宵怎麼說,蘇洄都不愿意,非常倔強地站在他邊,手放在他的肩上。
車程比他想象中還要長,蘇洄人生中第一次坐綠皮火車,才發現原來火車走得這樣慢。
他的意識忽然拉遠,想到一些臥軌的人。他們躺在滾燙的鐵軌上,聽著不遠傳來叮叮的聲音與火車的轟鳴,這段時間門,他們在想什麼呢?
忽然地,他意識到這個念頭很危險,勒令自己忘記,將視線落到寧一宵上。
寧一宵始終在愣神,一言不發。
只是在抵達某一站時,他還是起,把位子讓給了蘇洄,“我也想站一站。”
三小時,蘇洄從沒站過這麼久,他渾都酸痛無比,但還是想找機會和寧一宵換,所以時不時抬頭向他,小聲和他說話。
就這樣換著,他們陪伴彼此,熬過了非常艱難的十個小時。
下車后,轉了大,暈眩中蘇洄靠上了寧一宵的肩,做了一個很可怕但又難以描述出節的夢。再醒來,天快黑了,他們也終于抵達目的地。
寧一宵在出站后買了一瓶水,擰開蓋子遞給蘇洄,“很累吧?”
蘇洄接過水,喝了一大口,笑著搖頭,說一點也不累。
他寸步不離地跟著寧一宵,就差與他牽手。這是一座小到蘇洄從未聽過的小鎮,房子都矮矮的,到都是電車,沒什麼城市規劃可言。才下午五點,街上人已經不多,蘇洄有些,但沒做聲。
Advertisement
“你以前來過這里嗎?”他挨著寧一宵的手臂,輕聲詢問。
寧一宵搖了頭,“我第一次來。”
第一次?
蘇洄不太明白,他只是很直觀地到寧一宵的壞心,卻毫無辦法。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兒啊?”他又問。
寧一宵站在風里,沉默了許久,站在一塊陳舊的公站牌下,他終于等到一輛公車,拉著蘇洄的手臂上去,然后說,“派出所。”
沒等蘇洄弄明白這一切,他們就已經抵達。
一整天下來,終于有蘇洄不是第一次來的地方了。他想起自己病最不穩定的青年時期,某個月連著三次被帶去派出所,一次是酗酒倒在馬路上,一次是失蹤,家人報了警,還有一次是自我傷害。
都不是太好的事,所以他沒有對寧一宵說。
接待的民警和寧一宵通了幾句,接著給了他紙質材料登記,最后帶著他進去。
“你別進去了。”寧一宵握住了蘇洄的小臂,用了比平時大的力氣,好像在展現某種決心。
“就在外面等我。”他沒抬眼。
蘇洄不是很明白,但還是尊重了寧一宵的決定。
“好,我就坐那兒。”他回頭指了指大廳的一排椅子,“我等你。”
寧一宵點了下頭,沒說話,轉便跟著警察走了。
等待的時間門很難熬,蘇洄的手機快要沒電,他關了機,過派出所大門看外面逐漸消逝的天。
他忽然想到去醫院探媽媽時,說其實也很不喜歡被家人安排和婚姻,所以每次都自己選,但好像自己選的也不一定對。
蘇洄問,和爸爸結婚之后有沒有后悔過,季亞楠沉默了片刻,坦誠得有些殘忍。
說最后悔的時候,就是他爸生病的那段時間門,那時候每天都在想,為什麼老天這麼殘忍,既然要分開他們,又為什麼要讓他們遇見。一想到蘇洄爸爸總有一天會離開,就幾乎無法生活下去。
Advertisement
蘇洄聽著,到可怕又真實,尤其媽媽最后說的那一句——他走的時候很輕松,但活著的人太痛苦了。
他最近的思緒經常發生跳轉,想到死亡的頻率極高。有時候會突然地想象自己死去的畫面,或是腦子里出現一兩句很適合寫在書上的話,明明在躁期,明明很快樂。
蘇洄只能不斷地說服自己,他可以很好地生活下去,這個病不算什麼,只要他夠寧一宵,一定可以克服一切,就這樣一直陪著他。
他不會讓寧一宵那樣的苦,不會的。
很多事想多了便可以真,在這一刻蘇洄變得很唯心主義,希一切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發展,他不在乎科學或正確,只想要寧一宵幸福。
寧一宵出來的時候,整個人冷得像雪里的一棵枯木。
蘇洄第一次見他眼眶發紅,好像在咬著牙,不然本走不出來。
他立刻上前,想抱住寧一宵,但被他拒絕了這個擁抱。
“孩子,再簽一下字。”年邁的警察遞過筆,看向寧一宵,眼神于心不忍,于是又補了一句,“節哀。”
這兩個字像晴天霹靂,打在蘇洄臉上。
他抓著寧一宵的一只手臂,無措地看著他的側臉。
寧一宵到最后也沒有掉一滴眼淚,草草簽了字,抬頭,很冷靜地問,“火化的流程什麼時候可以辦?”
“已經走過鑒定流程了,明天上午可以通知殯儀館來取,看你方不方便,也可以晚一點。”
“早點吧。”寧一宵說,“我請的假只有兩天。”
就這樣,他們離開了派出所。蘇洄與他并肩走在黑暗的街道,路燈把影子拉得好長。他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又很想安寧一宵,想了很久,只問出“可不可以牽手”。
寧一宵沒說話,蘇洄主握住他冰冷的手,他沒躲,也沒有甩開,蘇洄就當他默認了,握得很。
“你的手好冰啊。”蘇洄抬頭看他,“冷不冷?我們去吃點東西吧。”
寧一宵搖了頭,看似漫無目的地走,但將他帶去了鎮上的一間門賓館。
這里一切設施都很陳舊,走進去便是經久不散的難聞煙味。前臺的木柜子已經破得掉了大片油漆,木皮一揭就掉。
一個中年人坐在高高的柜臺后,正用手機刷著吵鬧的短視頻,聲音大得什麼都聽不見,也咯吱咯吱笑著,仿佛很開心。
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寧一宵還是開了口。
“開一間門雙床房。”
聽到雙床房,蘇洄看了寧一宵一眼,但什麼都沒說。
人抬了頭,打量了他的臉,笑臉相迎,很快就替他走了流程,遞過來一張陳舊的門卡,上頭還有油漬。
蘇洄看了一眼卡,自己手接了,沒讓寧一宵拿。
他們按照提示上了二樓,地板踩上去會響,門與門挨得很近,他們的房間門在最里面。刷開門,里頭涌出一下水管道的氣味,冰冷,房間門里只有一臺很久的電視,窗戶很小,被黃窗簾遮蔽。床也很小,兩個中間門隔著一個紅木柜子。
關了門,蘇洄抱住了寧一宵,很滿很滿的一個擁抱。
這次寧一宵沒有拒絕,但也幾乎沒反應,僵直著,沒有了往日的溫度。
蘇洄只能靠聽著他的心跳維持緒穩定,他很害怕寧一宵沉默,但又清楚此時此刻,除了沉默,寧一宵什麼也給不了。
盡管他只經歷了表層,只看到寧一宵所看到的冰山一角,起承轉合的任何一樣都不了解,但也覺得好痛。
很忽然地,媽媽說過的話又冒出來,像沒愈合好的傷口,滋滋地冒出膿。
[他走的時候很輕松,但活著的人太痛苦了。]
不會的。
蘇洄對自己說。
他不會消失,不會離開,不會留寧一宵一個人孤零零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蘇洄的躁與郁早被分割兩極,誰也無法理解誰,哪個時期的承諾都不能作數,躁期他決定生活的好,下一秒,被抑郁支配后,覺得只有死亡才是最永恒的好。
他的承諾很廉價,總是不作數,甚至不配說出口。
所以他只敢很空地說,“寧一宵,不要難過,好不好?”
寧一宵其實表現得一點也不難過,他拍了拍蘇洄的背,在擁抱分開后,獨自去洗了手。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