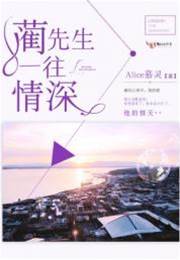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鮮婚蜜愛》 069 給我洗衣服
蘇喬瞧著他那副強的態度,想著不讓他上床估計是不可能了。
然而一肚子的火沒發出來心裏也堵的慌,又是又轉而提了別的要求,
“那好啊,不然你幫我洗服吧。”
“請注意,不是丟進洗機裏洗哦,是手洗!”
蘇喬著重強調了一下手洗這個詞,然後又笑瞇瞇地說著,
“你知道的,有些是不適合用洗機洗的。”
蘇喬打定了注意要刁難他到底,所以說完之後就那樣眼睛亮亮的盯著他。
顧庭深聽了的話之後挑眉反問了一句,
“你確定?”
蘇喬毫不猶豫地就點頭肯定著,
“當然!”
顧庭深也沒有任何猶豫地就答應了下來,
“OK,這個我接。”
蘇喬一時間有些吃驚,愕然看了他一會兒之後喃喃問著,
“你真的答應了?”
蘇喬之所以提出這些刁難的行為來,最終的目的是不讓顧庭深。
現在煩他煩的慌,才不想讓他呢。
而且也很了解他,出差在外麵十多天,今天早晨做了一次之後他本不可能解,晚上不了又要折騰,然而早晨那次已經雙都酸了,今天在公司腰也快要直不起來了。
蘇喬覺得顧庭深是肯定不會答應下來幫手洗的,顧大總裁長這麽大恐怕連自己的都沒親自洗過吧,所以想著這樣的話他就不用再折騰了。
然而哪裏能想到他會答應下來了,一時間都懵了。
也失算了。
顧庭深瞧著那副又驚又懊惱的模樣,心好得不得了,玩心機深沉這些東西,哪裏是他的對手?
“不然我還有別的選擇嗎?比起不準上床,我比較能接給你洗服這件事。”
是他又故意調侃了一番,然後拿起筷子來悠然用餐。
Advertisement
蘇喬氣的胃都疼了,然而剛剛話都說的那樣囂張了,姿態也端的那樣高,現在也不可能拉下臉來求饒,或者是改變主意。
後麵又想著,好啊,既然他要洗,那他就洗吧,倒是要看看,他顧大總裁是不是能真的放低姿態給洗服。
到時候可以拍張照片,等什麽時候找個合適的時候放出來給別人看,讓他麵盡失!
想著這些的時候蘇喬又咬牙強調了一遍,
“你要一直給我洗到你什麽時候弄好鑽戒和求婚這些事!”
顧庭深的眉眼間多了幾分深,淡淡應了下來,
“很願意為你效勞。”
蘇喬狠狠瞪了他一眼,低頭將注意力放在眼前的飯菜上,給對麵的某個惡劣的男人來了個不理不睬。
晚飯之後顧庭深就打電話去了,蘇喬收拾了碗筷去廚房。
等洗好碗出來的時候,發現顧庭深人已經不在客廳了,臥室裏也沒有他的人影。
蘇喬看著衛生間的方向,額頭不由得跳了跳。
因為早上被他纏著做了一次,所以洗過澡之後有換下來的,當時急著上班就那樣丟在髒簍了,此時蘇喬心裏在想著,顧大總裁不會真的在衛生間給洗服吧。
這樣想著有些慌張地推開了衛生間的門,
“顧庭深——”
蘇喬實在是無法想象顧庭深給洗那些是什麽樣的畫麵,而且一想,就覺得臉紅心跳。
衛生間裏。
顧庭深卷著居家服的袖子正站在洗手盆前專注洗服呢,他麵前的臉盆裏,有蘇喬的早上換下來的,還有屬於他的。
他的是黑的,蘇喬的是白蕾的。
男人人最的就那樣糾纏在一起,如同男人人的,也如同男人人的。
Advertisement
剪不斷理還。
那樣薄薄的一層布料被他的大手在掌心裏著,要多曖昧就有多曖昧。
蘇喬看一眼過去就覺得臉紅,總覺得像是他火熱的手指在著最私的那一。而偏偏,此時的顧庭深角還叼著煙卷,別著煙邊洗著,一張英俊的側臉在那些繚繞的煙霧中愈發顯得人。
蘇喬推門進去的時候,顧庭深就那樣咬著煙卷轉過頭來瞇著眼看了一眼。
蘇喬一瞬間覺得心跳加速,像是被什麽擊中了似的,渾麻。
輕咳了一聲走了過去,一下子端走了他麵前的臉盆,臉上有些紅的說著,
“我想過了,還是繞過你好了,我自己洗就好。”
顧庭深低低笑了起來,慢條斯理地洗了手抬手將邊的煙卷拿了下來按滅,丟到了一旁的垃圾桶裏,
“再親的事我們都為彼此做過了,有什麽好難為的?”
男人不經意間暗示著兩人在事上的歡愉和親,一雙湛黑的眸子更是盯著,那裏麵倒映出蘇喬越來越紅的臉。
直接低吼了一句,
“你閉!”
然後端著臉盆就打算往外走,蘇喬哪裏會想到,明明是想要刁難他的,到最後反倒被調戲了。
顧庭深攔住了,
“都洗了一半了,哪有半途而廢的道理。”
“我覺得這也沒什麽不好的,夫妻趣的一種不是嗎?”
說著大手徑自將手中的臉盆拿了過來,衝笑著吩咐了一聲,
“你先出去吧。”
見蘇喬窘著臉站在原地不彈,他又說著,
“或者你在這裏洗澡也可以。”
“我不介意一邊勞一邊欣賞。”
蘇喬,“......”
“不要臉!”
這樣低低罵了他一句之後匆匆跑出了洗手間,就那樣將自己丟進沙發裏捂著臉好一會兒心才平複下來。
Advertisement
睡的時候,蘇喬被勞完的男人抵在大床裏好一番懲罰。
男人在按著吻遍了的子之後,卻始終不肯給,蘇喬的早已不已,也做好了接納他的準備,然而他一直在外麵徘徊著,蘇喬被他的整個子都又又。
男人的手極富技巧的著的子,順便威脅地問著,
“還敢不敢再跟我作對了?”
蘇喬要哭出來了,挨不過去隻能摟著他的脖子好一番求饒,
“不敢了......”
男人又問著,
“真的不敢了?”
“真的不敢了......”
蘇喬氣惱著顧庭深每次都會在床事上拿著,然而卻又沒有辦法不被他拿。
因為太了解的,那人有的是辦法讓哭著求饒。
一番歡愉結束,蘇喬累的趴在枕頭裏抗議著,
“顧庭深,你再這樣下去,我早晚要死在你手裏。”
蘇喬是咬牙切齒說著這番話的,真的是承不住了。
從頭發到腳趾,都是酸的累的。
早晨一次,晚上一次。
他就不怕盡人亡嗎?
無比饜足的某人靠在床頭煙,順便懶洋洋回著,
“你可千萬要住,以後我還要指著你證明我在男科方麵沒有問題呢。”
蘇喬覺得他真的是太可惡了,累死累活的,他還有力氣說著風涼話。
當下就卷著被子轉過來,一雙麗的眸子眨呀眨地看著他笑著,
“其實我有一個很好的辦法,瞬間就能證明你英勇無比。”
顧庭深了一口煙,好整以暇看著問著,
“哦?什麽好辦法?說來聽聽?”
蘇喬笑的很是邪肆,
“你找個優,跟拍個作大片,你順便再超常發揮一下,做半個晚上,保證瞬間能挽回你的男雄風。”
顧庭深給了一個涼涼的眼神,
Advertisement
“就這麽希你男人出去染指別的人?”
“我覺得證明我沒問題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趕給我生個孩子。”
顧庭深這樣說完之後看向的眼神又變的濃沉了下來。
蘇喬抿不說話,就那樣看著顧庭深。
他的眼神也沒有毫要退讓的意思,兩人一時間就那樣僵在床上。
早上兩人分明已經因為生孩子的事弄的不歡而散,現在他又重新提了這個話題。
蘇喬不知道顧庭深為什麽非得執著在孩子這個話題上,但是也聰明的知道,如果再次像早上那樣強排斥的話,沒有好果子吃。
半響,拉過被子來蒙住了自己的臉,
“我困了,要睡了,晚安。”
試圖用這樣的方式逃避著這個話題。
下一秒被子被人很是魯地給扯了下來,是顧庭深將手中的煙卷按滅再次湊了過來,蘇喬嚇的連忙求饒,
“你別再來了好不好?我真的要累死了......”
顧庭深扯掉上的被子,冷著臉掰著的,
“心不爽,必須要做。”
蘇喬挪著躲著,
“求你了顧庭深,我真的很累......”
蘇喬知道他說的心不爽是為什麽,不就是為不肯回應生孩子的事嗎?
早上都回應了不是嗎?他又不聽的那個答案。
現在他又這樣不依不饒的,是非得著答應馬上就生嗎?
“累了沒關係,我不要,讓你爽就行,一會兒就好。”
顧庭深說著,已然將的折了起來,俊臉往下埋了去。
蘇喬尖著,
“我不要——”
然而男人堅持的事,是本無法改變的。
蘇喬一張臉要紅了,他這樣做,本不是在讓爽,而是在折磨。
男人的舌熱,蘇喬沒一會兒就渾癱了下來,大口大口的息著,極致的愉悅讓整個人都是的,沒有一力氣。
猜你喜歡
-
連載1164 章
穿到跟殘疾大佬離婚前
遲清洛穿進一本狗血小說,成了商界殘疾大佬作天作地的小嬌妻。小嬌妻驕縱任性,飛揚跋扈,還紅杏出牆。遲清洛穿來當天,原主正因為爬了娛樂圈太子爺的床上了熱搜。大佬丈夫終於同意跟她離婚。遲清洛:“老公我愛你,之前跟你提離婚是我一時糊塗。”輪椅上的大佬眸色深沉:“你糊塗了很多次。”不不,從今開始,她要改邪歸正,渣女回頭金不換。可是漸漸的大佬好像變得不一樣了,對她說抱就抱,說親就親。嗯?大佬不是淡薄情愛,隻把她當擺設的麼?遲清洛眨眨眼:“好像有哪裡不對。”大佬將小嬌妻圈入懷中,指腹摩擦著她的唇珠,聲音嘶啞:“哪裡不對?”
104.7萬字8 56331 -
完結845 章

寵婚入骨
許家多年前送去鄉下養病的女兒許呦呦回來了,回來履行與林家的婚約婚禮前夕新郎逃婚去國外找他的白月光,眾人:哇哦……【吃瓜表情】許呦呦:哦豁。下一秒,白皙細軟的小手攥住男人的衣袖,甜糯糯的語調:“墨先生,您可以娶我嗎?”……墨深白商業巨擘清心寡欲,神秘低調,在波雲詭譎的商場叱吒十年,無一家報刊雜誌敢刊登他的一張照片,也沒有一個異性能讓他多看一眼。所有人都說墨深白娶許呦呦一定是協議婚姻,一年後絕對離婚。許呦呦津津有味的吃著自己的瓜,只是吃著吃著就發現好像不對勁啊。逛街購物不需要買單,吃飯不用點餐,不管走到哪里大家熱情跟她打招呼:墨太太好。後來墨深白的白月光回來了,前未婚夫深情表白:“呦呦,只有我是真的愛你,回我身邊,我不嫌棄你。”許呦呦還沒來得及回答被男人霸道的攬入懷中,低音性感撩人:“寶貝,你沒告訴他,這裡有了我們愛的結晶。”溫熱的大掌貼在她平坦的小腹上。許呦呦紅了臉,渣男紅了眼……【無腦瑪麗蘇先婚後愛文|專注虐男二】
142.9萬字8.18 230570 -
完結11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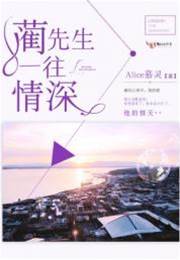
藺先生一往情深
曾有記者舉著話筒追問C市首富藺先生:“您在商界成就無數,時至今日,若論最感欣慰的,是什麼?” 被眾人簇擁,清俊尊貴的男子頓步,平日冷冽的眸難得微染溫色,回答:“失而複得。” - 人人都說她死了,藺先生心裡有一個名字,彆人不能提。 他走她走過的路,吃她喜歡吃的食物,人前風光無限,內心晦暗成疾。 情天眉眼寂淡:有些愛死了,就永遠不在了。 他眼眸卻儘是溫然笑意:沒關係,沒關係。 她的心再冷,他捂暖。 世人隻知商場中藺先生殺伐決斷手法冷酷,卻從不知,他能將一個人寵到那樣的地步。 - 但後來 人來人往的步行街頭,商賈首富藺先生仿若失魂之人,攔著過往行人一遍遍問—— “你們有冇有看到我的情天……” 他的情天,他的晴天。 · ·寵文·
138.8萬字8 78669 -
完結855 章

報告總裁,你老婆又跑了
黑暗中,他鉗住她的下巴,“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她自輕自賤“知道名字又如何?你只要一分不少的把錢打到我卡上就行了。” 本以為拿到錢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當一切沒有發生。 誰知那古怪男人從此卻陰魂不散的纏住了她。
167.7萬字8 38185 -
連載176 章

軍婚撩人:首長大人請深吻
她代替姐姐嫁給了那個據說身有隱疾的年輕軍長。他的寵,他的溫柔霸道,讓她毫無抵抗的臣服。卻原來爾婚我詐,不過是一段遠的要命的愛情。幾年後,她攜子歸來,撩撥的他欲火焚身。他反身把她壓在辦公桌上,“老婆,按照一夜七次的頻率來算,你已經欠我很多了,要不咱們還是先還債吧!”
30.5萬字8 262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