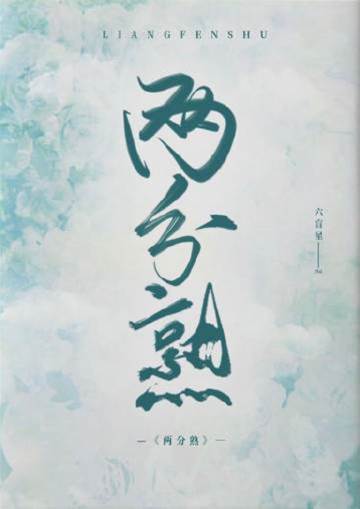《越山愛你百年》 第一百五十章他遠走,她常念
周平桉是跟著隊伍走的,他特意囑咐過讓許抒那天就別送了,機場有記者和軍區的領導,不能被拍到。
許抒便站在小區門前送,穿了件長到腳踝的漂亮白子,長發也沒用皮筋綁起來,特意化了妝,原本就明豔的長相,此刻更是的讓人錯不開眼,勉強地扯出一抹笑。
周平桉背著包,手裏拖著黑行李箱,整個人穿得是軍人常服,他回頭深深地向。
就站在原地,緒穩定得讓人心驚,纖細的小小影,一雙漂亮的眼睛盯著他拉著箱子一步步的走遠。
許抒拚命地克製自己,的指甲深深嵌進了掌心,麻木到已經不覺疼痛,眼睛又又酸,好半晌才舍得眨一下。
他沒走出去多遠,便丟下箱子往回跑,蠻橫地將人攬懷裏,用力地擁抱著自己的人,仿佛要將骨子裏。
許抒再也忍不住了,的眼淚嗒啪嗒啪地就落了下來,小聲地噎著,纖細地輕輕抖著,瘦削平直的肩膀也在抖著。
“平安符不要離。”
周平桉什麽也不說,他們的離別沒有親吻,沒有挽留和煽,隻有用力地擁抱,仿佛一鬆手人便不見了。
他手背青筋暴起,將臉埋在的脖頸,香溫涼。
Advertisement
“阿苑,我若平安回來便娶你,回不來…”他的話還沒說完,便被許抒用堵住,難舍難分的一個吻,雙方忍克製的一個吻。
不想聽他說喪氣話,那樣的事,想都不敢想。
…站在原地,直到霧蒙蒙的路上再也看不見周平桉。
兩天後的淩晨,終於等到了周平桉的短信——阿苑,平安降落了。
守著豆腐塊一樣的軍事報紙度日,不肯錯過任何一點兒軍事新聞,在國心急如焚,卻沒有任何法子出國找他。
自從上次維和隨醫的事,家裏人格外防備,甚至收走了所有的護照和境卡,即使什麽也不沒收,的出境也早被限製,大使館會卡的簽證,許家會不聲的用一切關係和力量阻攔。
放棄了抵抗,卻仍舊賭氣沒有和家裏聯係,幾乎每天都會給打一通電話,知道爺爺一定也焦急的守在旁邊聽著。
許抒怕他們跟著擔心,那天在房子裏發生的事隻字不提,隻是說在忙畢業答辯,等六月下旬,學校裏的事理好之後就會回去看他們。
周平桉降落在馬裏某國時,淩晨四點,外麵的旭初生,霧蒙蒙的東邊亮起了天,一種用語言不能描述的。
Advertisement
這樣的壯觀震撼,許抒曾在零八年便見過了。
那還是很久之前,他曾經在夜裏睡不著的時候翻來覆去地去翻許抒的人人網賬號,默默看著那六年來的點點滴滴。
零八年北京奧運會,那時的北京備全世界的關注,功申請做了奧運會誌願者,經常用著畫質模糊的CCD小相機拍北京熱鬧的街道和天安門廣場。
距離奧運會開幕式的倒計時三天,曾經在人人網發布了一張日出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微微曙,天破曉,遠的雲層層漸變,站在遠,拍下了曙下人頭攢從世界各地趕來看升旗儀式的壯觀場麵。
周平桉落地後,跟在隊伍的最後麵,在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引導下往路口走,街上也有許多的人一團,他們全都是自發遊行示威的當地居民,不管男老,所有的人都穿著破爛髒兮兮的服,滿是泥垢的手指舉著自製的木板。
他有些恍惚,在同樣麗的景下,同樣是人頭攢的街頭,卻翻天覆地、截然相反的境。
周平桉突然停住腳步,用手機的後置鏡頭記錄了當下的那一刻,遠天微亮,霧蒙蒙的天,破敗不堪的街頭,全是憤怒罷工停學的當地民眾。
Advertisement
2012年,人人網漸漸從昔日國最大的社平臺走下了神壇,他沒辦法繼續用以前那個賬號了,他在某國外大火的推特上創建了一個小號,偶爾發布自己維和的一些態,目的就是不想讓許抒為他擔心,也算是變相的分生活,讓這異國沒有那麽辛苦。
他不知道,許抒常常握著手機睡覺,將音量調到最大,就是怕兩地時差,萬一從有打來電話,沒接到。
可維和部隊總是駐紮在野外的營地裏,當地憂外患,在某些心懷不軌的歐國家的慫恿下,他幾乎每天都要去班執勤,還會經常與反派發生槍戰,他過傷,在這支隊伍裏,幾乎沒有人毫發無損。
許抒從不主給他打電話,怕幹擾他,隻敢在推特上不停地刷新著頁麵,盼著他會更新。
冬天悄無聲息地來了,仍然住在周平桉的那棟小房子裏,勤儉樸作風一生的爺爺心疼早出晚歸地鐵,搭出租車,給買了新的跑轎,牌子低調,但是配置極高。
博士畢業後在軍區部署醫院實習工作,長大後的許抒真的喜歡上了王菲。
時代承載著所有暗心悸的那首《曖昧》,聽得耳朵都快磨出繭子了,可每次聽,都會被時間猛地拉回許多年前,那時還在讀高中,被家長老師都懷疑是早。
Advertisement
人生中最早的一次悸,也是最刻骨銘心的喜歡。
灰藍的天,告別未晚,穿他的。
結束一天工作後,常常驅著車子駛在日落大道上,聽王菲的其他歌。
周平桉的賬號不常更新,那些過往的帖子被看了又看。
戰中的馬裏某國街頭角落,一大群不蔽的兒瑟瑟發抖,周平桉於心不忍,給他們分發補充力的甜巧克力。
那些孩子年齡尚小,最大的不過才十二三歲,街上不再能見到遊行示威的隊伍,就在半個月前,暴分子武裝遊行,他們買了某發達國家的軍火,走在街上的人民隨時都有被槍殺的可能。
猜你喜歡
-
完結91 章

偏要你獨屬我
分手兩年後,秦煙在南尋大學校友會上見到靳南野。 包間內的氛圍燈光撒下,將他棱角分明的臉映照得晦暗不明。 曾經那個將她備注成“小可愛”的青澀少年,如今早已蛻成了商場上殺伐果斷的男人。 明明頂著壹張俊逸卓絕的臉,手段卻淩厲如刀。 秦煙躲在角落處,偷聽他們講話。 老同學問靳南野:“既然回來了,妳就不打算去找秦煙嗎?” 男人有壹雙桃花眼,看人時總是暧昧含情,可聽到這個名字時他卻眸光微斂,渾身的氣息清冷淡漠。 他慵懶地靠在沙發上,語調漫不經心:“找她做什麽?我又不是非她不可。” 秦煙不願再聽,轉身就走。 在她走後沒多久,靳南野的眼尾慢慢紅了。在嘈雜的歌聲中,他分明聽到了自己的聲音。 “明明是她不要我了。” - 幾年過去,在他們複合後的某個夜晚,靳南野俯身抱住秦煙。 濃郁的酒香包裹住兩人,就連空氣也變得燥熱稀薄。 男人貼著她的耳畔,嗓音低啞缱绻,“秦秦,我喝醉了。” 他輕啄了壹下她的唇。 “可以跟妳撒個嬌嗎?” *破鏡重圓,甜文,雙c雙初戀 *悶騷深情忠犬×又純又欲野貓 *年齡差:男比女大三歲
27.3萬字8 19074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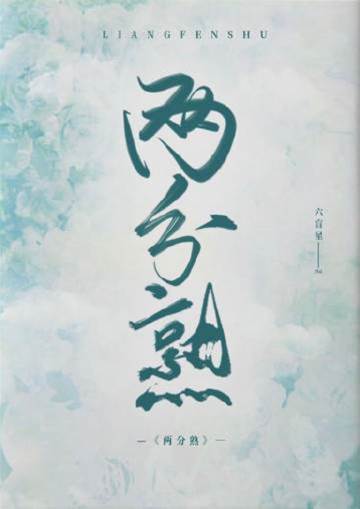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408 -
完結62 章

要和我交往嗎
徐其遇被稱爲晉大的高嶺之花,眉目疏朗,多少女生沉迷他的臉。 餘初檸不一樣,她看中的是他的身體。 爲了能讓徐其遇做一次自己的人體模特,餘初檸特地去找了這位傳說中的高嶺之花。 可在見到徐其遇第一眼時,餘初檸立即換了想法。 做什麼人體模特啊,男朋友不是更好! 三個月後,餘初檸碰壁無數,選擇放棄:) * 畫室中,餘初檸正在畫畫,徐其遇突然闖了進來。 餘初檸:“幹、幹什麼!” 徐其遇微眯着眸子,二話不說開始解襯衫鈕釦:“聽說你在找人體模特,我來應聘。” 餘初檸看着他的動作,臉色漲紅地說:“應聘就應聘,脫什麼衣服!” 徐其遇手上動作未停,輕笑了一聲:“不脫衣服怎麼驗身,如果你不滿意怎麼辦?” 餘初檸連連點頭:“滿意滿意!” 可這時,徐其遇停了下來,微微勾脣道:“不過我價格很貴,不知道你付不付得起。” 餘初檸:“什麼價位?” 徐其遇:“我要你。”
16.8萬字8 4565 -
完結435 章
一手遮腰
【清醒心機旗袍設計師vs偏執禁慾資本大佬】南婠為了籌謀算計,攀附上了清絕皮囊下殺伐果斷的賀淮宴,借的是他放在心尖兒上那位的光。後來她挽著別的男人高調粉墨登場。賀淮宴冷笑:「白眼狼」南婠:「賀先生,這場遊戲你該自負盈虧」平生驚鴻一遇,神明終迷了凡心,賀淮宴眼裡的南婠似誘似癮,他只想沾染入骨。
66.3萬字8 59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