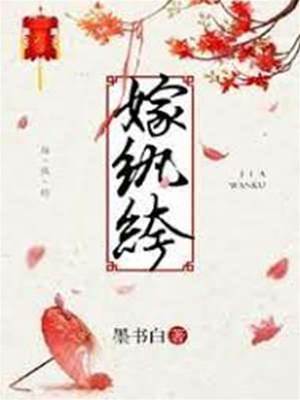《重生后,她逼婚了漠北戰神!》 第1915章
第1915章
云夢牽心里咯噔一下,怎麼還有個轉折?
難道是因為的份?
玄蒼的眼神也瞬間變了。
卻聽南非熙繼續道:
“只是這婚事嘛,自古以來都是父母之命,妁之言。你的婚事與不,還得你母親說了算,為父......說了不算......”
聞言,司空一口老差點沒噴出來!
趕過了二十多年,這位太子爺還是如此自覺地懼啊!
天快亮了,東方泛起了魚肚白,有金黃的霞漸漸從云層里綻放。
一陣馬蹄聲噠噠噠的響起,由遠及近,朝太極宮奔馳。
不多時,一道火紅的影映著朝霞而來。
馬背上跳躍的大紅,宛如一團跳的火焰。
火紅的影在南非熙面前停下。
“吁......”
拉停韁繩,居高臨下地看著南非熙,從頭到腳,從腳到頭。
Advertisement
水伶的眼中漸漸蓄滿淚水,一馬鞭到了龍輦上,“啪”的一聲,發出偌大的回響。
“南非熙,二十多年,你跑哪去了?沒死為什麼不來找我?你知道我裝瘋裝得有多辛苦嗎?你怎麼賠我?”
說著,水伶抬手又是一馬鞭到了龍輦上,淚水潸然。
打龍輦,與打皇上無異。
也只有,敢如此對他。
龍輦上的南非熙,眼中含淚,卻是忍不住笑了出來。
他艱難地抬起手,這是他第一次有了作,不再像一古木一不。
天知道,他想要抬起手,牽扯到傷口,需要花費多大的力氣與痛苦。
“伶兒......”
他張了張,卻只喚了的名字,聲音已是哽咽。
水伶急了,連忙跳下馬背,沖到他的面前,里卻沒一句好話:
“傷得這麼重,逞什麼能?還不把手放下?”
Advertisement
然而,最心的人到了眼前,南非熙還怎麼舍得放手?
干柴一般的手指輕輕上了水伶的臉,著溫熱的,他的淚落了下來。
“伶兒,我好想你......”
一句話,終是把水伶惹得不行,放聲痛哭。
不敢他,怕他疼。
只能伏在他的上,如此著他的存在。
二十多年了,他們終于再見。
他們還是彼此的摯,此生不渝。
南非齊著這一幕,終是丟掉了所有的偽裝,淚水痛苦地落。
原來,從沒有瘋過。
的瘋,只是為了拒絕他。
二十多年,他小心翼翼地呵護著、用盡全力地著,卻始終捂不熱的心。
到最后,江山還是南非熙的,人也還是南非熙的。
他努力了這麼多年,仍舊一敗涂地。
為什麼,究竟是為什麼?
太極宮前,南非熙一家團聚。
南非齊孤家寡人。
兩個極端,兩個世界。
朝躍出天際,金燦燦的霞給南非熙一家鍍上一層耀眼的暈。
而另一邊的南非齊,卻始終頹然在暗之,一如他的未來。
天亮了,整個皇宮沐浴在之下。
南非熙吃力地握著水伶的手。
玄蒼攥著云夢牽的手。
他們看著彼此,眼里只有彼此。
仿佛窮盡一生的努力,只是為了這一刻。
過盡千帆,洗盡鉛華,眼前,仍是,只有。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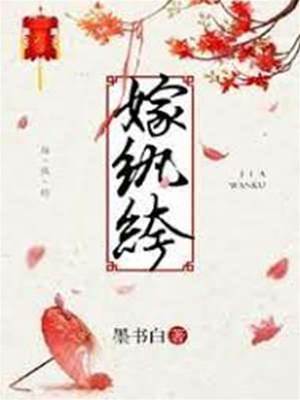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287 -
完結737 章

妃常妖嬈:王爺盡折腰
現代具有特異功能的西醫一朝穿越到失寵和親公主身上。白蓮花一瓣一瓣撕下來。王爺高冷傲嬌也無妨,某女揮起小鞭子,收拾得服服貼貼。
127.4萬字8 102792 -
完結216 章

不夜墜玉
師蘿衣與錦鯉小師妹爭斗。 不甘心比了一輩子,敗了一輩子。青梅終究比不過天降,最后連她的竹馬未婚夫也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小師妹。 破廟瀕死,無人殮骨。 就很氣啊! 她驟然想起,很久之前,自己也曾贏過一次:她不可描述了小師妹看得和眼珠子一樣的凡人兄長
33.5萬字8.33 84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