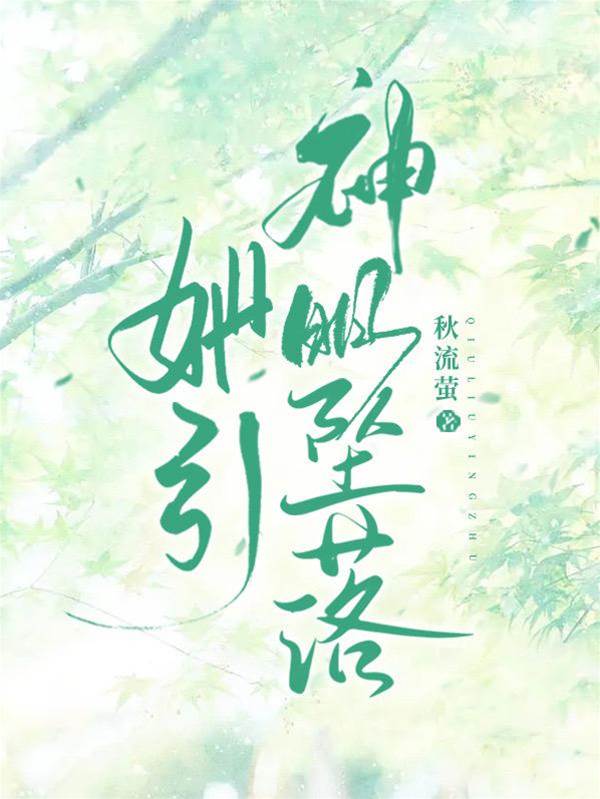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他難馴》 第129章 失控
見咬著不說話,陳燼子前傾,變本加厲地拽著胳膊上挪:“手撐在桌上。”
幽暗的房間,桌上隻有臺燈開著,溫熒的軀輕輕栗,被他拎起來手肘托在書桌,背對著他,心裏無聲唾罵著陳燼的變態行徑。
“……你別這樣。”
頸後傳來帶著裹挾著笑音的聲音,陳燼扯鬆掛脖細繩摘下,反剪過雙手抵在背後束手腕,“別哪樣?可是我看寶貝很.啊。”
——他竟然把了!
溫熒大腦快炸,嚨出一聲極輕的嚶嚀。
陳燼修長骨的手指按在沙發兩端,膝蓋骨懲罰地,溫熒哪裏經得住他這麽折磨,沒兩下就嗚咽出聲。
不了地轉過來,徑直被陳燼摁在了桌上。
他微躬,低下頭來,頎長的形拔如鬆,熱的呼吸噴灑在腰間,薄烙了下來,聲音低啞。
……
“到給我看。”
門外的人走後,溫熒才劫後餘生地息著,滿腦子都是陳燼驚人的肺活量。
-
五一小長假來臨。
微電影拍攝到一半,還差關鍵幾個重要的鏡頭和節,男主養父的角遲遲未敲定。
陳燼不知從哪打聽到一個演藝界的知名前輩住在廈市,且這幾天橘子海旁有個落日天音樂節,聲勢浩大,去玩幾天和拍攝兩不耽誤,一拍即定。
考慮到有人家庭條件一般,溫熒提議大家搭車去。
五一車票難定,眾人隻搶到了晚上六點多的,五六個小時車程,到了直接住附近酒店過夜。
進了高鐵車廂找到位置,陳燼替擺好行李箱,前麵車座的後背鉤子掛好垃圾袋,網兜裏放滿了零食 、水和防暈車的橘子皮。
Advertisement
足足弄了五六分鍾。
蔣璿和潘柏他們坐在斜後方,這節列車是三人一排,溫熒靠窗,陳燼居中,外側還有個三四十歲的中年大叔,帶著一個小男孩。
溫熒從包裏拿出他的pad,和陳燼共一副耳機,一起看了部《空》的日本文藝片。
節狗而悲,是男主患癌癥瞞病和主分手,並托朋友幫忙安心孩的故事。
集未婚先孕、絕癥、誤會於一,結局男主病逝be。
窗外夜幕黑沉,溫熒將腦袋靠在他肩膀上,低聲問:“如果有一天你得了絕癥,會不會也瞞著我?”
想進一步了解陳燼的觀。
“當然不會。”
陳燼毫不思索地勾,愈發近耳廓,舌尖剮蹭,“老子肯定第一個告訴你,畢竟不能我痛苦。”
這、個、壞、種。
溫熒回子,不想理他了。
就在昏昏睡地頭一點一點地傾向陳燼膛時,旁邊的小男孩突然將陳燼包上的刺蝟掛件了下來,顯然是好奇盯了許久。
下一瞬,他就被陳燼牢牢桎梏住了手腕,骨節得泛白:“還來。”
“我不!這是我拿到的!不給!打你!打洗你!”
小男孩不知是被擰痛了,還是被他眼神震懾得恐慌,邊打邊哭,站在地上大吵大鬧。
陳燼瞇起眼,嗓音冷似冰:“別讓我重複第二次。”
誰知小男孩就跟陳燼強上了似的,站在走廊中央,用力掐著刺蝟對峙著。
“小夥子你什麽意思?怎麽欺負小孩呢?”
中年男人站起推了他一把,“一個絨掛件值多錢?十塊錢都不到的玩意兒,一個大男人怎麽氣量這麽小,一個地攤貨都要跟小孩斤斤計較?”
Advertisement
陳燼猝然失控,眼底蔓出紅,驟然將他按在椅背,腮幫咬得很:“你他媽再說一次。”
“我說錯了嗎?就是地——”
“這是我跟他的紀念品,他悉心保存了六年。”
溫熒一字一頓地盯著男人,麵凜然,“別道德綁架了大叔,我們憑什麽要因為您兒子小就讓著他,我們放過他,誰來放過我們?”
男人被伶牙俐齒的話懟得啞口無言,列車員也趕忙過來調解,正好到了一個站點,小男孩抓著刺蝟就往門口跑,徑直跑了出去!
中年男人急得趕連忙追了上去,誰知小男孩隻是嬉皮笑臉地將刺蝟丟了出去就回來了,還朝陳燼做了個鬼臉就跑了:“略略略,就不給你,你欺負我!”
陳燼臉鷙,猶如出籠的兇,顧不得管他,背影剎那消失在車廂門口。
“滴”、“滴”、“滴”,列車已經緩緩鳴起關門的笛聲。
“——陳燼!別撿了!!”
溫熒疾步追了出去,瞳孔陡然一——
濃稠暗得不見天日的夜晚軌道,陳燼彎腰匍匐著背,摁亮手機電筒,焦灼又迅速地一寸寸徒手翻找索著站臺外的空地。
那是從未見過的陳燼的樣子。
驕傲睥睨萬不可一世,卻又卑微執拗到了泥土裏。
潸然淚下,心口一寸寸刀割般揪著疼。
突然想起那天跟陳燼去城隍廟祈福,明明就在附近,陳燼卻怕丟了,讓一個阿姨看著。
因為三年前的一次不告而別,造了他近乎病態的缺乏安全和恐懼。
本想象不到,在杳無音信的三年,陳燼是怎麽撐下來的。
Advertisement
“聽話,先上去。”
“找不到就別找了,你想要多個我都可以送你!陳燼,我不會丟的,我會永遠陪著你。”
溫熒又急又心痛,終於在休息椅旁邊拾到了,陳燼抓著胳膊,趕在最後一次關門的倒計時最後三秒,上了車。
驚魂未定,又有些慶幸立馬下了車。
“知不知道你剛才有多危險?為什麽跟著我下車?夾到手怎麽辦?”
陳燼拎著提到了座位,臉龐染上了一沉青的薄怒,像是被氣笑了,又像是在哄小孩,帶著無奈,“你又不會把我弄丟。”
“就算錯過了,我也能搭下一班找你。”
你又不會把我弄丟。
溫熒心口一片鈍痛,哽咽到說不出話,死死地抱了他,頭搖得像撥浪鼓,眼睛很紅。
“你永遠不會錯過的,因為會自己來找你。”
溫熒聲音嘶啞,帶著噎哭腔,埋進他膛,“那就是一隻刺蝟掛件而已……你要是想要,我可以給你買,給你織很多很多隻,多到你再也弄不丟。”
“你說的,我錄音了。”
陳燼麵微怔,愉悅滿足地了,先前的躁戾煙消雲散,出了兜裏掌心的手機,角輕挑,“老子會每天提醒你。”
午夜列車發出轟隆隆輾過隧道的聲響,兩人纏的背影卻像是回到了高中那段青蔥歲月,共一副耳機聽著品味相似的電音。
孩腦袋一點一點地傾向他的肩,一隻骨節分明的手輕地摘下的耳機,墊著的頭慢慢托到了膝蓋上。
……
零點抵達廈門,一夥人就近在附近酒店過了一夜,翌日醒來,天氣晴朗,是個豔天。
Advertisement
休息好後,劇組員就去拜訪了那個已退知名男演員的家。
他們今天要拍一場重頭戲,主周菱去男主家找男主,結果意外撞見男主遭著養父的家暴,敢聲張遭到男人威脅後,主想早日幫男主解,失手殺了嗜酒如命的養父。
後來,男主魏燃騎托帶主潛逃私奔。
甚至請到了影視界實力派的餘哲前輩出演男主養父。
對陳燼的考驗很大,劇本不節描寫魏燃慘遭非人欺淩的節,溫熒擔憂他,餘老師也問他要不要到時候打輕些,或者不會真打。
誰知,陳燼淡然如斯:“就按照劇本的演,別把觀眾當傻子,隻有真傷和真才能打觀眾。”
導演喊開始。
溫熒敲響了他家的門,無人應答,下一秒,聽到裏麵傳來玻璃杯摔摜聲。
“讓你給老子倒杯酒,啞呢?”
一個喝得酩酊大醉雙眼猩紅的禿頂中年男人,拍了拍陳燼的臉,掐住了他的脖子,將他重重地推向茶幾。
陳燼雙目充,子重重地栽下去,撞上啤酒瓶,一片狼藉。
溫熒過門看到了他脊背青紫斑駁的淤痕。
那一瞬,兩人目相撞,陳燼眸一震,如有驚愕和難堪的浮一掠而過,抄起桌上的杯子就朝門口砸去:“滾。”
後來,溫熒帶了傷藥去找他,陳燼隻留給一個修長冷漠背影,口吻疏離:“你走吧。”
猜你喜歡
-
完結511 章

聽說校草被甩了
安靜內斂沉默的少女,嬌生慣養毒舌的少年,兩人之間坎坷的成長曆程與甜蜜情深的故事。*雲慎曾在學校時聽到這樣一段對話--「聽說言謹被甩了……」「誰這麼囂張敢甩了他?」「雲慎啊。」「那個偏遠地區的轉學生?」「可不,不然還能有誰?」全校同學集體沉默了一會兒,唯有一道聲音有點不怕欠揍的說道:「這年頭,言謹還會遇上這麼活該的事情?」雲慎「……」*他們的愛情,屬於那種一切盡在無言中,你圍著他轉,卻不知,他也圍著你轉。很甜很寵,包你喜歡,快來吧~
80.4萬字8 14751 -
連載2595 章

霸道帝少惹不得
安希醉酒後睡了一個男人,留下一百零二塊錢,然後逃之夭夭。什麼?這個男人,竟然是她未婚夫的大哥?一場豪賭,她被作為賭注,未婚夫將她拱手輸給大哥。慕遲曜是這座城市的主宰者,冷峻邪佞,隻手遮天,卻娶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人,從此夜夜笙歌。外界猜測,一手遮天,權傾商界的慕遲曜,中了美人計。她問:“你為什麼娶我?”“各方面都適合我。”言安希追問道:“哪方面?性格?長相?身材?”“除了身材。”“……”後來她聽說,她長得很像一個人,一個已經死去的女人。後來又傳言,她打掉了腹中的孩子,慕遲曜親手掐住她的脖子:“言安希,你竟然敢!”
424.7萬字8.18 52225 -
完結512 章

新婚夜,我治好了陸先生的隱疾
【一場陰謀撞上蓄謀已久的深情,經年仇恨,也抵不過陸靳宸想要溫晚緹一輩子的執念。】 *** 溫晚緹嫁給了陸靳宸。 她本以為,他們的婚姻只是有名無實。卻不想…… 她還以為,他和她都一樣,各懷目的,於是小心翼翼地守著自己的心。殊不知,他早把她鎖在了心裏。 *** 眾人都等著看她笑話,等著看她被趕出陸家大門的狼狽樣子。 哪知,等啊等,等啊等。 等來的是他替她遮風擋雨,替她找回親人…… *** 片段 他曾醉酒後,撫著她的臉呢喃,「阿緹,我放過你,誰放過我自己?」 他也曾清醒後,黑著臉沖她吼,「溫晚緹,我陸靳宸從和你領證的那一刻起,就認定了你。我們之間不會有生離,只有死別!」 *** ——後來, 人人都羨慕溫晚緹,她不僅是豪門真千金,還是陸靳宸寵在心尖尖上的女人。
98.4萬字8 46965 -
完結50 章

許以晴深
祁邵川是許晴心頭的一根刺……當那天,這根刺扎穿了許晴的心臟,讓她鮮血淋漓的時候,她就徹底失去了愛一個人的能力。但如果所有的一切重新來過,許晴興許還是會這麼做。…
5.2萬字8.18 14289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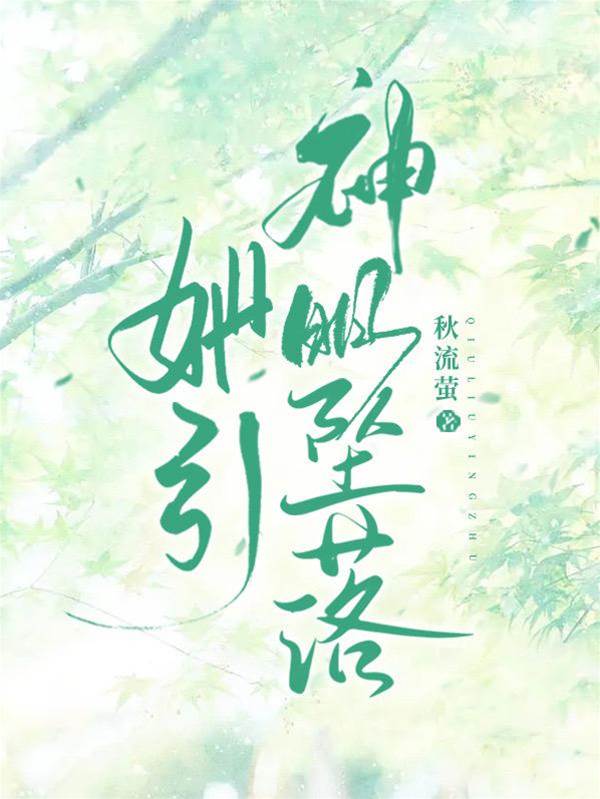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442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