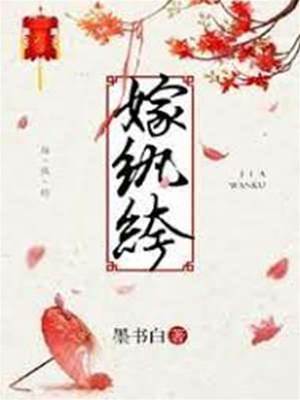《嬌軟美人和她的三個哥哥》 【67】
【第六十七章】
元宵過后,這個年節也算結束了。
步二月,冰雪尚未消融,柳樹才冒出點點綠,春闈便拉開序幕。會試與鄉試一樣,共考三場,三日一場,通共要考九日。
在謝叔南的強烈要求下,云黛答應送他們進場——
原本也是想送他們考試的,但考慮到謝伯縉也會去,才有所猶豫。然而兩人之間牽扯難斷,躲無可躲,還是得上。
好在嘉寧滿心歡喜要去送謝仲宣,云黛稍覺安,心里想著來回有嘉寧作伴,起碼不用與大哥哥單獨相了。
這日一清晨,天邊還灰蒙蒙的,冷冽的空氣里繚繞著霧氣,貢院門口已然熱鬧起來,人來人往,車馬不斷。
“二哥哥,三哥哥,包袱里放的膝套和護腕你們記得穿戴,夾里還有提神醒腦的薄荷膏,你們上場前記得在兩側額角抹上一些,尤其午后容易犯困,抹一些腦袋能清醒些。”
“知道了,妹妹你都念叨一路了。”謝叔南清俊的臉上掛著笑,抬手拍了拍膛,有竹對云黛道,“有云妹妹的關心加持,我和二哥一定會全力發揮,你就在家等著我們的好消息吧!你說是吧,二哥?”
“我可不敢將話說的這樣滿。”謝仲宣含笑睨了他一眼,轉而看向云黛,目和煦,“九日過得很快,出場那日,云妹妹會來接的麼?”
見他語含期待,云黛自是答應,“肯定會的,你們在里頭好好考,到時候我和嘉寧表姐還有……大哥哥,嗯,到時候一起來接你們。”
嘉寧忙不迭點頭,亮晶晶的一雙眼看向謝仲宣,“對對對,一定來的!”
一直緘默不言的謝伯縉嚴肅的面部線條稍,上前一步,拍著兩個弟弟的肩膀,諄諄鼓勵了兩句,見時辰不早,說道,“進場吧,莫要張,盡力發揮即可。”
Advertisement
謝仲宣和謝叔南與他們告別,轉往貢院里去。
來時是兩輛馬車,去時謝伯縉住嘉寧,“我與云黛有事要談。”
言下之意嘉寧怎會不懂,看了眼已經坐在馬車里的云黛,再看一眼面前氣勢攝人的大表兄,很是配合道,“行,那我去前頭那輛馬車。”
說罷趕帶著丫鬟往前去了。
寶藍車簾被掀開,看見俯進來的男人,云黛心口猛地跳了兩下。
四肢僵地著車壁坐著,低低喚了聲,“大哥哥……”
謝伯縉四平八穩地坐下,見直直的盯著垂下的車簾,語帶冷意,“嘉寧在另一輛馬車。”
云黛臉微變,低頭盯著水紅羅下黛藍繡鴛鴦蝴蝶的鞋,屏氣凝神。
這是正月初一后,他們頭一回單獨相。
在這狹窄的馬車里,人息都變得艱難起來。
他突然換馬車,是想做什麼?
忐忑不安地等待著,猶如砧板上的魚等著刀子落下,時間變得很慢,每一刻像是煎熬。
直到馬車再次行駛,見他還沒有開口的意思,云黛最先不住,看向側那氣定神閑輕撥香爐灰燼的男人,開口道,“大哥哥換馬車是有什麼事麼?”
“無事。”
謝伯縉放下香撥,平靜向,“只是想與你說會兒話。這些日子,你一直躲著我。”
云黛抿了抿,這是事實,無法辯駁。
謝伯縉見垂下濃黑羽睫,慢慢道,“這一趟來長安,妹妹玩得夠久了,是該回家了。等半月后放榜,我會派人送你回肅州。”
回去?云黛微怔,見他臉上并無半分玩笑的神,急急道,“我不回去……”
謝伯縉往車壁一靠,高大的形如玉山將傾,語氣還是平淡的,“出來這麼久,都不想家麼?”
Advertisement
“我自然牽掛府中,只是……”云黛頓了頓,不知該如何往下說。
謝伯縉替接上,“只是姑母雖已往隴西寄信稟明這樁婚事,可隴西的回信尚未寄回,與崔家的婚事沒定下,你心頭不安。”
云黛心口一跳,再看他這副神態自若的模樣,頓時了然,白的手指微微收攏,“是了,這事你一問,姑母也不會瞞你。”
“沒問。”謝伯縉輕飄飄道,“我把信截下來了。”
云黛瞳孔微,難以置信地看向他,“大哥哥,你為何如此?”
謝伯縉清冷的朝面上看去一眼,“妹妹這樣聰慧,你說為什麼。”
他這副不近人的涼薄樣子遽然將云黛拉回那日傍晚,頭微哽,緩了好半晌,才艱開口,“大哥哥,你到底想怎樣?那日我已與你說的很清楚,你又何必這般糾纏不休,這樣對你我都不好……”
“我想怎樣?”
謝伯縉輕輕呢喃一句,高大的軀忽得朝云黛那邊俯去,見要躲,手掌牢牢地勾住的后脖頸,讓避無可避。
“我想要怎樣,那日也與你說了。妹妹還不懂麼,那夜之后,你我再無法像從前那樣當兄妹了。”
云黛面慘白,細細哀求著,“別說了,你別說了……”
他抓著的手,按在了他的膛上,把握的拳頭一點點平,著他跳的心口,低頭在耳畔用極低的聲音道,“在那之前,倒還能克制住。可妹妹你招惹了我,是你將那些荒唐的惡念放了出來,你就不管了麼?”
云黛覺到掌心下那劇烈跳的節奏,他灼熱的溫侵襲著,將的心跳也變得很快很快。
慌張地收回手,反駁著,“我不是故意的,那日是中了藥,都是那藥惹的禍……”
Advertisement
“嗯,說到那藥。”
謝伯縉另一只手起的下,這作讓與他對視著,他湛黑的眸子帶著絕對的冷靜,又如鷹隼般銳利,定定地凝視著,語氣卻是溫和緩的,“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那一晚你真的半分意識都沒有麼?”
云黛眸閃了閃。
想扭過頭,他發現的意圖,得更近了些,聲音漸低,“那晚,換做是旁人尋到你,你也會……求他幫你麼。”
云黛瓣囁喏,心頭紛不堪,結結道,“沒有旁人,這假設不存在,那日就是大哥哥……我相信大哥哥,知道哥哥不會害我……”
“只是信任?那若是二郎和三郎呢?”
他看到越發慘白的臉,知道這或許殘忍,卻不可避免,的心思藏的太深,像只小烏,遇事只知道往殼里躲,手段不狠一些絕不出來。
握著的手轉而按在了的口,他抵著的額頭,著那的跳,薄似笑非笑,“妹妹的心,也跳得很快。”
云黛半邊子都僵,心底像一團麻,強烈的恥一波一波涌上來,流遍的四肢百骸。
謝伯縉見那雙明亮的黑眸里漸漸漫起水氣,心頭一,溫熱的手指挲著的臉頰,嘆道,“誠實些,你心里也是有我的。”
聞言,眼睫一,淚水就順著頰邊滾落了下來。
像是被當眾裳,又像是做賊被示眾,那份不想承認的心思被他看得徹,被他直接點明——
是,那夜的并不是全無意識,知道抱著的人是謝伯縉,是的大哥哥。
也不清楚那是怎樣的一種,信任他,依賴他,想要靠近他,甚至有一瞬慶幸,是他尋到了。
或許正如他說的,心里是有他的。
Advertisement
也不知是從何時開始,原本的兄妹就變得不那麼純粹,時不時想起他,惦念著他,見著他會格外歡喜,見他與冷淡,失落且傷懷——同樣是哥哥,這種緒只對他有過,旁人都沒有。
只是自欺欺人,試圖將一切罪責都推到那合歡藥上,試圖維持著道德完、品行高潔的妹妹形象。
哪戶好人家的姑娘會惦記著自家兄長呢?祖母和夫人對的教誨、圣賢書上的規矩道理,從來沒有這樣的。
“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云黛語氣幽戚,淚如雨下,沿著白皙的臉頰滾落在下尖,晶瑩剔。
“別哭了,這也沒什麼。”
謝伯縉見逐漸崩潰,手攬過的肩,將抱在了懷中,有一下沒一下拍著的背哄道,“你我皆非圣人,何必要將自己架得高高的。你不必自責,我與你是一樣的……”
“不一樣……我們不一樣的……”云黛在他懷中放聲大哭,手指揪著他的襟,恨他咄咄人,更恨自己的不知廉恥。
待哭到累了,揚起臉,淚眼婆娑看向他,帶著幾分歇斯底里的意味,“且不說這世道的標準,對男子總是更寬容,對子更苛刻。就說我與你的份,你有退路,你始終都有退路……可我呢,我不行,我沒有父母,沒有親兄弟,沒有家族,我如今的一切都是國公府給的,我仰仗著國公府,著國公府的恩惠,我依附著國公府才有如今的好日子……若是做出此等勾搭兄長忘恩負義之事,國公爺和夫人會如何看我?外人會如何看我?我又怎麼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時在喬家家塾讀書,讀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之耽兮不可說也”,就覺著心里難過。
現在想起這句話,愈發覺得傷懷——
“大哥哥……如果你真的喜歡我,真的為我好……就放過我吧。”
仰著臉,眉眼間是孤注一擲的神,“現在你也知道了,我是個很糟糕的人,心思不那麼單純,膽怯如鼠怕惹事,明明討厭一個人一件事卻要裝作寬容、裝作喜歡,我一點也不乖,也不想那樣懂事,我也很懶,一點都不喜歡日日早起請安,也不想學那些繁重的禮儀規矩。我羨慕玉珠,羨慕慶寧和嘉寧,甚至還羨慕過明珠。可我沒得選,為了讓國公爺和夫人喜歡我,我得變溫馴乖巧的樣子……凡事都要三思,做事說話都要有分寸,時刻謹記自己的份,我不能惹麻煩,不能出錯……”
以手掩面喃喃道,“我不敢,也不能,我得按部就班、循規蹈矩的過日子,我輸不起的……”
謝伯縉垂下黑眸,看著懷中抖的削瘦的肩背,將的摟得更了些。
手掌按著的頭,他高的鼻梁深深埋的脖頸,長長的喟嘆,“我很早就知道。”
“知道那個乖巧溫順的妹妹并不那麼乖。知道寄人籬下過的辛苦,知道心思敏,知道也想活得肆意自在……”
所以,他一直想多護著,對更好一些。
哪知最后把心都了出去。
黑沉沉的眼底劃過一抹輕嘲。
“第一次見你時,你說你不想去秦州,求我幫你,你說你相信我。這些年過去,甚至中了藥,你依舊信我……”
在驚懼無措的目中,他的薄落在抹了胭脂的角,喑啞道,“妹妹為何不再信我一回?我不會讓你輸的。”
云黛震住。
還沒等反應,他低下頭,吻了上來。
比那晚的吻更為繾綣,帶著些懲罰的味道,撬開的瓣與貝齒,不容拒絕的索取著,將上的胭脂吃得干凈,又打破的理智與意識,生的拽著,認清他的心,認清他們的本,拉著一道沉淪著。
他也是自私的。
自掉泥淖,便不許置事外,和樂滿。
過了一段極漫長的時間,這個吻才結束。
云黛息著睜開眼,看到謝伯縉的眼睛格外得黑亮,眼尾染著淡淡的紅,墨黑的瞳孔像是旋渦,要將給吞噬般,心驚跳。
他的態度也變得格外的溫,再沒先前的冷臉,低頭吻了吻的眼睛,又將抱得更了些,兩人都沒再說話。
隔著裳能到他腔的起伏,還有他夙愿得逞的歡喜。
他的懷抱很暖,將嚴嚴實實罩著,到溫暖,一顆心卻依舊在云端飄著,對這一切到恍惚與彷徨。
馬車又行了一路,靠在他的懷中,垂著眼睛喚他,“大哥哥……”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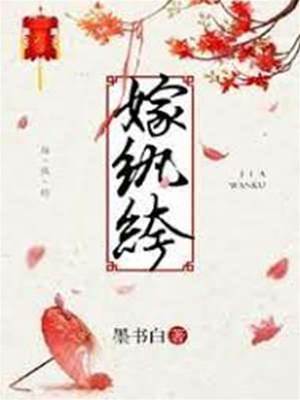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727 -
完結737 章

妃常妖嬈:王爺盡折腰
現代具有特異功能的西醫一朝穿越到失寵和親公主身上。白蓮花一瓣一瓣撕下來。王爺高冷傲嬌也無妨,某女揮起小鞭子,收拾得服服貼貼。
127.4萬字8 102826 -
完結216 章

不夜墜玉
師蘿衣與錦鯉小師妹爭斗。 不甘心比了一輩子,敗了一輩子。青梅終究比不過天降,最后連她的竹馬未婚夫也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小師妹。 破廟瀕死,無人殮骨。 就很氣啊! 她驟然想起,很久之前,自己也曾贏過一次:她不可描述了小師妹看得和眼珠子一樣的凡人兄長
33.5萬字8.33 87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