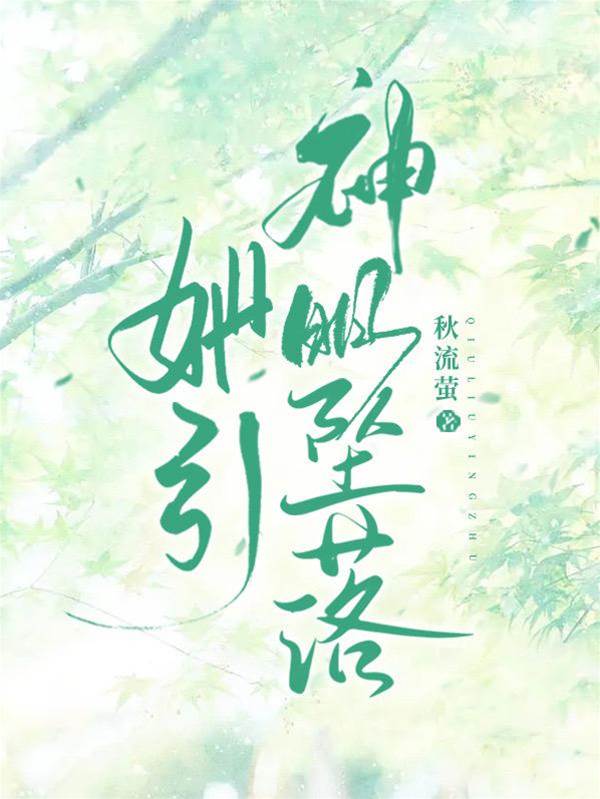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前夫想要生二胎》 第40章 老天爺派來折磨她的
白西月當晚回到家,已經是後半夜了。思兔
木木睡著了就很難再醒,王士把臥室的門開著,方便隨時觀察木木的況。則坐在客廳沙發上,等著白西月回來。
門口傳來靜,起去了玄關。
白西月看見,嘆口氣:「又等我?」
王士道:「都跟你說了,上了年紀,覺。」
白西月換了鞋進門,不知道怎麼才能把這個習慣改一改。
擔心自己,白西月知道。但這麼晚不睡覺,白西月也心疼。
「不?」王士跟在後:「還吃點東西嗎?」
白西月忙說:「您快去睡吧,我洗洗也睡了。」
王士看一眼:「你不是洗了澡走的?」
白西月一愣,接著裝傻:「我洗了嗎?」
王士點頭:「洗了。」
白西月道:「哦,那再洗把臉。困死了,我去睡了。」
Advertisement
進了臥室,直接把房門關了,然後靠在門後,藉助門板才能站穩。
季連城這個瘋子,喝醉了酒沒輕沒重的,折騰得腰酸背痛不說,一下地,都是的。
等洗完躺在床上,整個人都要散架了。
然後,想口。
沉穩得的白大醫生,遇見季連城,就變得衝急躁,腦筋短路。
這麼多年,季連城對的影響,依舊是不能控制的。
他吻過來的時候,半邊子都是的。
所以,這要是在古代,是君王,季連城絕對是那個皇帝不早朝的禍國妖妃!
不能怪定力不夠。
實在是季連城魅力太大。
但現在唾棄自己也是真的。
不管怎麼說,季連城有朋友。第一次因為喝醉了,算有可原吧。那這次呢?喝醉的人可是季連城,可一直是清醒的。
Advertisement
怎麼能做出這樣的事?
現在,只能祈禱季連城喝了就斷片,明天早上起來,一切都忘得乾乾淨淨!
而且,這樣的事,以後絕對不能再發生!
在摻雜了悔恨、酸楚甚至還有莫名其妙恨意的奇怪緒中,白西月終於睡著了。
鬧鐘響起的時候,白西月實在是不想爬起來。
太累了,全上下每一塊關節都在囂著「不想」,本來上一天班就很累了,又被季連城沒輕沒重地折騰了兩回——如果不是用盡全的力氣保持了最後一冷靜,然後趁著季連城不注意逃了出來,照他那個沒完沒了的勁頭,不被折騰死才怪!
不過,話又說回來,上次兩個人差錯睡在一起,是喝得人事不省,兩人親熱的過程忘得一乾二淨,只留一痕跡,是他一夜戰的戰利品。這次呢,他醉了,是清醒的。
Advertisement
因此,時隔多年,再一次清晰地到了他的熱、力度和強度。
所以說,沉迷其中無法自拔,本就不是的錯啊!
這男人……簡直就是老天爺派來折磨的吧?
雖然承認這一點讓白西月覺得很恥,但從兩人的親里得到了至高無上的快樂——這是毋庸置疑的。
是個正常的人,也有自己的需求。
特別是在知道這個男人能帶給自己多麼強烈的覺的前提下,讓拒絕他,是一件非常難的事。
白西月把自己跑偏了的思緒拉回來,一鼓作氣坐了起來,穿了鞋子就往洗手間跑。
然後就是每天按部就班的洗漱,哄木木起床,吃早餐。
飯桌上,王士道:「昨晚沒來得及問你,你前……那個,木木爸爸沒事吧?還有,你怎麼回來那麼晚?」
最近為了刺激白西月,時常把「前夫」掛在邊上,剛剛差點在木木面前也說出來。
白西月瞪一眼:「沒事。回來晚了是因為,我去了醫院一趟。」
話音剛落,手機就響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28 章

年代甜炸了:寡婦她男人回來啦
(全文架空)【空間+年代+甜爽】一覺醒來,白玖穿越到了爺爺奶奶小時候講的那個缺衣少食,物資稀缺的年代。好在白玖在穿越前得了一個空間,她雖不知空間為何而來,但得到空間的第一時間她就開始囤貨,手有余糧心不慌嘛,空間里她可沒少往里囤放東西。穿越后…
97.7萬字8 2851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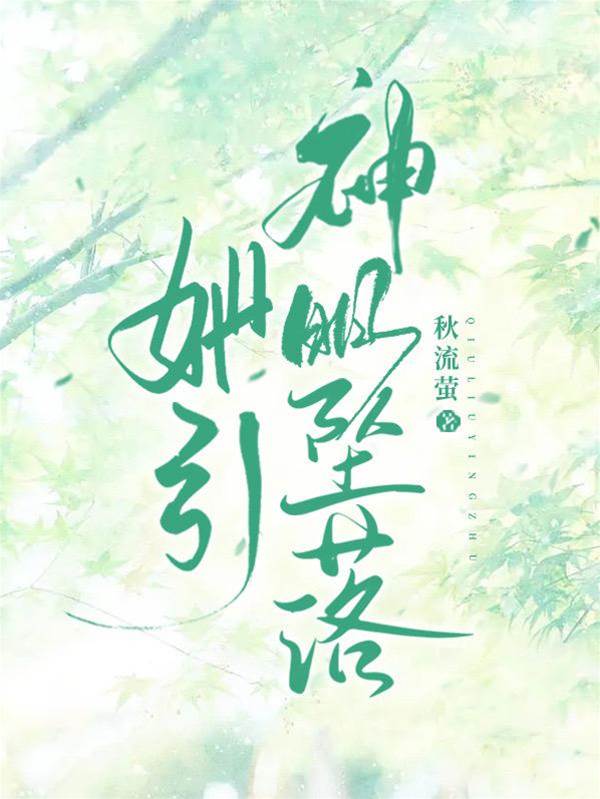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221 章

春意入我懷
【大學校園 男二上位 浪子回頭 男追女 單向救贖】【痞壞浪拽vs倔強清冷】虞惜從中學開始就是遠近聞名的冰美人,向來孤僻,沒什麼朋友,對前仆後繼的追求者更是不屑一顧。直到大學,她碰上個硬茬,一個花名在外的紈絝公子哥———靳灼霄。靳灼霄這人,家世好、長得帥,唯二的缺點就是性格極壞和浪得沒邊。兩人在一起如同冰火,勢必馴服一方。*“寶貝,按照現在的遊戲規則,進來的人可得先親我一口。”男人眉眼桀驁,聲音跟長相一樣,帶著濃重的荷爾蒙和侵略性,讓人無法忽視。初見,虞惜便知道靳灼霄是個什麼樣的男人,魅力十足又危險,像個玩弄人心的惡魔,躲不過隻能妥協。*兩廂情願的曖昧無關愛情,隻有各取所需,可關係如履薄冰,一觸就碎。放假後,虞惜單方麵斷絕所有聯係,消失的無影無蹤。再次碰麵,靳灼霄把她抵在牆邊,低沉的嗓音像在醞釀一場風暴:“看見我就跑?”*虞惜是凜冬的獨行客,她在等有人破寒而來,對她說:“虞惜,春天來了。”
39.6萬字8.18 627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