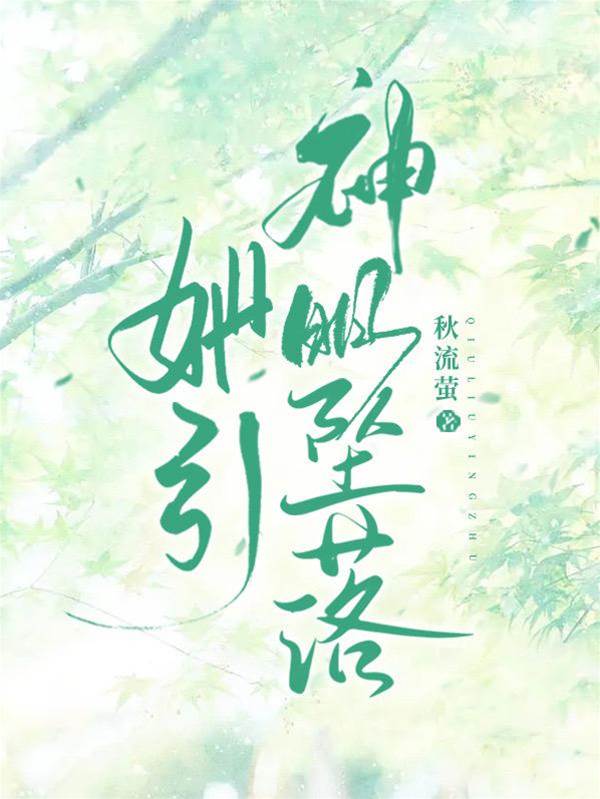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無人區玫瑰》 第109章 第109章
一個無關于你的夢
“沒有,才不浪漫。”
夏星眠別過頭,輕哼一聲,眼底鐫著一種理想化的狂妄。
“我和你不會死,我們長生不老,宇宙活多久,我和姐姐就在一起多久。這才是終極的、現實主義的、浪、漫。對不對?”
陶野便順著,嘆著氣點頭。
“好吧,好吧,那我們不會死,我們長生不老。”
夏星眠憋著笑,卻皺起眉,故意做出怪氣的樣子:“姐姐這語氣,本就不是真的信,本就是哄我。”
陶野嘆氣:“小滿啊,我再怎麼想順著你,也不能讓我這樣心智正常的年人一下子就相信人真的會長生不老吧?”
夏星眠笑了:“噗……好了好了,我不胡攪蠻纏了。”
陶野又抬頭,向棚外看了眼天空,說時間已經不早了,還是早點吃晚飯。
夏星眠答了聲好,從陶野懷里起來,坐到桌子一邊,拉著夏懷夢,一起吃起烤和魚湯。
再晚一些,吃過飯,三個人收拾了桌子。把該折疊的都折疊起來,安放妥當,就各自回帳篷休息了。
一看手機,已經過了十一點,差不多就是夏星眠和陶野平時習慣睡覺的時間。
但今天是營在山雨中,雨點落在帳篷頂,滴滴答答的。時不時大風吹過,帳篷的骨架還會發出吱呀聲。
人一躺下,滿眼只剩眼前搖晃的帳篷了。
夏星眠睡不著,翻過來翻過去,輾轉不停,就是無法睡。
最后,索翻過,趴在睡袋上,看向邊的陶野,聊起些日常瑣事。
“姐姐,我們回頭買一架鋼琴,放在店里好不好?”
陶野端正地躺在睡袋里,雙手叉放在小腹上,眼睛閉著。
聽到夏星眠的話,也沒睜開眼,只是輕聲回道:“我還以為你這麼多年不彈,已經對鋼琴沒有什麼興趣了。”
Advertisement
夏星眠哂笑一下:“是嗎……”
陶野:“你這次回來,好像一次琴都沒有彈過。”
夏星眠:“是……”
陶野慢慢地轉,面向夏星眠,悠悠睜開眼。
“如果你真的很想彈,那我就給你買兩架,一架放在家里,一架放在店里。這樣的話,你想在哪彈就可以在哪彈了。”
“好,謝謝姐姐。”
夏星眠向著陶野蹭過去,環住陶野的胳膊,輕輕笑。
“給店里買一架就好了,不用那麼破費。”
陶野沉默了一陣子。
半晌……
又開口:“也給家里買一架吧,你想在哪彈就在哪彈。”
陶野連著說了兩遍「你想在哪彈就在哪彈」。
夏星眠敏地覺察到了什麼,抱著陶野的胳膊僵了一剎。
在黑暗中悄悄抬眼,看向對面的陶野。
在這手不見五指的濃稠夜中,只能看到陶野大致的一個廓。
看不見對方此刻眼底的緒,也看不見任何可能會出心細枝末節的表。
是啊……
不論怎麼說,當年,都是因為鋼琴才離開陶野的。
連夏星眠自己也都覺得,如果最開始沒有因為鋼琴一鳴驚人,也沒有因為鋼琴出國巡演,那麼后來所有荒唐詭譎的事都不會發生。
只是,昨日之事不可追。
現在再慨這些,也已經沒有了意義。
可誰都會在潛意識里害怕重蹈覆轍吧?
或許陶野是不太愿意重新撿起彈琴這件事的,更不愿意再次從事鋼琴事業。
哪怕還是很想彈。陶野寧愿在多個地方擺上琴,讓解癮,讓饜足,讓留滯在兩架琴圈的小世界里。只要再也飛不走,飛不遠。
誰知道呢?
陶野真正的想法,也揣測不到百分之百。可能這些也只是的胡思想。
Advertisement
夏星眠發覺自己好像思慮得太遠了。
收回神緒。
“好,姐姐既然愿意買兩架,那就買兩架吧。”
“嗯。以后我空閑了,就聽你彈琴給我聽。”
陶野在黑暗中來了手,勾住了夏星眠的小拇指。語氣似在嗟嘆。
“以前在酒吧,或者在演奏臺上,你都是彈給大家聽的,我一直都是旁觀者。”
夏星眠順著陶野的話說:
“那我以后就只彈給姐姐一個人聽。”
陶野似乎得到了期待的承諾,很開心地笑了起來。
“好……”
們又聊了些其他的小事,諸如陶野的下一個假期們要去哪玩,又或者店里生意越來越好,是不是需要再雇兩個勤工儉學的學生來高峰期幫幫忙。
還聊到了夏懷夢和周溪泛的事。
夏星眠和陶野慢慢地詳細講述了從小到大,周溪泛都是如何掛念著那個早就離開的大姐姐。
講述了周溪泛為了夏懷夢放棄了多東西。還有到最后,周溪泛自己都弄不明白的這種長久又畸形的。
在別人的故事里,陶野像是終于忘記了自己的故事。
一邊聽夏星眠緩慢地講,一邊模模糊糊地閉合了雙眼,徐徐睡了。
夏星眠知道陶野為了這餐晚飯忙碌了一天,很累了,于是合時宜地閉上,幫陶野挽起垂落在側臉與鼻梁上的頭發,抱住陶野的胳膊,也醞釀起睡意。
雨聲淅淅瀝瀝,在耳朵里逐漸變得空遠去。
帳篷里,汽車上。
每個人都做起不同的夢。
這一夜,夏星眠也做了夢。
以往的夢,不論好壞,總是和陶野有關。可是這一次,很罕見的,的夢里沒有出現陶野。
夢見了許多年前,在瑞典的斯德哥爾的一次演出。
那不是反響最大的一次,也不是賺錢最多的一次,甚至在履歷表里都排不上號。但是卻最喜歡那一次的演奏。
Advertisement
那次的演出,和任何人都無關。
和陶野也無關。
只是自己,很喜歡那天的天氣。喜歡那個天的場地,彈奏的時候,一抬頭,就可以看見溫煦的和湛藍的天,還有綿白的云和清爽的風。
那天的觀眾不是什麼高雅的音樂好者。只是一群沒有穿禮服戴領結、抱著膝蓋坐在草地上的孤兒。是一次義演。
著那些異國孩的淺眼睛,縱然與他們語言不通,過去的數十年也不曾照過同一片,不曾飲過同一條河溪。
但還是能從他們的眼睛里看見關于音樂,那種無國界、無長、無別的共鳴。
鋼琴……
樂曲……
音樂……
夏星眠在這個夢里,找到了年時期第一次到鋼琴,彈下第一個鍵時的回憶。
心底深的一抹靈犀之火,被那「咚」的一聲琴音點燃。那一刻,就明白了這一生最為不可或缺的事與中,一定會有這些黑白琴鍵。
夏星眠醒來時,還是半夜。
雨仍舊滴滴答答地響在頭頂的帳篷,天仍是黑的,不過帳篷比之前稍微亮了一點點。夜從卷開的窗口進來。
陶野在側睡,頭微微偏向,手握拳放在臉前面,指間捉著的一縷頭發。
夏星眠抬起手,想要把自己的頭發從陶野的手里取出來。
可探到一半,猶豫了片刻,最后也沒取。
就這樣安靜地凝著陶野的臉。
夏星眠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做剛剛那個夢。
或許只有自己明白,鋼琴,也喜歡以鋼琴為介演奏心里的音樂給世界上所有愿意聆聽的人聽。
人總是想要找知音的。也總希擁有觀眾,用觀眾熱烈的反饋告訴自己,的理想并不只是孤芳自賞。
沒有哪個藝創作者會不希有更多的人來認可自己。
Advertisement
就像作家的書總想要出版。
就像畫家的畫總想要掛上展覽長廊。
可是……
可是如果陶野很在意……
夏星眠明白已經做出了選擇。
所以才會做這個夢。
的大腦,在用這種方式,和一生的理想做著告別。
這樣暗暗的割舍,是一種無意義的自我嗎?
夏星眠思索了一番,進行了否定。
因為此時此刻,并不痛苦。
知道有舍不得,可是所有的舍不得都被另一種心覆蓋了。
那心做:我終于給了姐姐足夠的安全。
看起來是在給陶野安全,是在付出。但事實又不僅是如此。對于真正相的人來說,對方能夠開心,給予自己的心反饋是另一種不可取代的緒價值。
這也是所收獲的切真價實的快樂。
陶野在岸的酒店里曾經和說過:不介意們之間公不公平,夏星眠是全世界唯一不想用利益得失心去對待的人。
夏星眠覺得不是。
覺得,陶野不是真的不在意公平。陶野是很清楚,無論自己付出多,夏星眠都會和一樣地回去。
不是懷著不計較公平的一腔癡傻的,才無底線地寬容對方。
是因為足夠相信對方的,所以才不計較在的天平上,誰的得失更多一些。
陶野是對的。沒有信錯人。
夏星眠陶野,的確,和陶野夏星眠一樣多。
夏星眠悄悄湊過去,在睡的陶野臉上很輕很輕地吻了一下。
從沒想到,當放棄理想的這一天,居然沒有任何冷徹心扉的痛苦。
反而因為能夠給對方安全,而從心底里覺得,就該為了這樣做。
“姐姐……”
夏星眠趴在陶野耳邊,輕不可聞地細聲呢喃。
“我以后,就真的只為你彈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31 章

萌寶歸來:爹地放開我媽咪
他冷血無情,隻懂強取豪奪!她被逼無奈,放下傲骨,與他糾葛,踏入豪門。五年後,她攜萌寶歸來,勢要雪恥前仇。萌寶狡詐呆萌,像極了他。“叔叔,你想做我爸比?可你好像不合格。”某男人俯視身邊的女人,“合不合格,隻有你媽咪說了算。”這個男人不但霸道,還寵妻入魔。
78.4萬字8 25363 -
完結955 章

先婚后愛:權少的迷糊小老婆
蘇煙怎麽也想不到交往了四年的男朋友會爲了前途而選擇另壹個世家女,既然這樣,那她選擇放手。 可是對方卻不依不饒,幾次出現在她面前秀恩愛!她忍讓,對方卻越發囂張。 蘇煙:“我已經有男朋友了。”誰知她在馬路上隨便找的男人竟然這麽優質,而且還全力配合她。 她感動的想以身相許,結果人家說,他需要壹個能洗衣做到拖地的人。 蘇煙傻兮兮的被帶回家,發現自己的老公是壹個經常出任務的軍人,而且她什麽都不用做,只要被寵愛就行了! 婆婆:“寶貝兒媳婦,這是婆婆炖了幾小時的湯,快喝。”公公:“妳那些客戶要敢欺負妳,妳就告訴我,我讓他們消失!”老公:“我老婆是我的,妳們誰也別想霸占!”………………婚前:蘇煙:“妳爲什麽幫我。”沈右:“我是軍人,爲人民服務是應該的。”婚後:蘇煙:“妳最喜歡吃什麽。”沈右:“吃妳。”【歡迎跳坑~】
242.7萬字8 42778 -
完結985 章
南方有喬木喬妤
父親年邁,哥哥姐姐相繼出事,24歲的喬家幺女喬妤臨危受命接管風雨飄搖的喬氏。為了保住喬氏,喬妤只好使盡渾身解數攀上南城只手遮天的大人物陸南城。 初見,她美目顧盼流兮, “陸總,您想睡我嗎?” 后來,她拿著手中的懷孕化驗單,囂張問著他, “陸總,娶不娶?” 男人英俊的面容逼近她,黑眸諱莫如深, “這麼迫切地想嫁給我,你確定我要的你能給的起?” 她笑靨如花,“我有什麼給不起?”
229.9萬字8 695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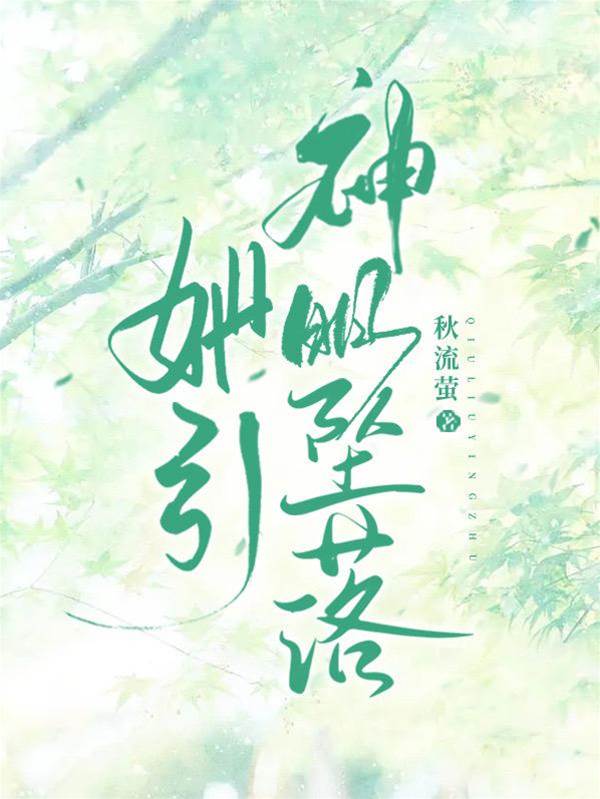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