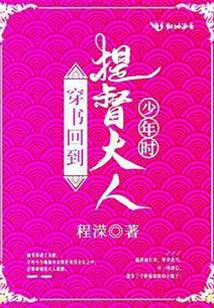《替姐出嫁後,錦鯉農女逆襲了》 第1836章 四宗師的下落
直到前頭街頭的人紛紛跪下了,石姑幾人站著太顯眼,不得不在人群裏蹲下。
果然是王後的車駕,但王後為何在此時出宮?
王後的車駕過去,街頭兩邊的百姓終於鬆馳下來,石姑幾人倒不急著去諳蠻族府邸了,而是在一茶樓停了下來。
石姑抬頭看向茶樓上,建築不似漢人區的茶樓,搭的架子卻是簡陋無比,而且喝茶的寮國人並不多,來的也是來北城做生意的漢人或者寮國商人。
石姑臉微變,二板疑的問道:“媳婦兒,怎麽了?”
石姑總覺他們幾人被人盯上了,卻說不出誰盯著他們,已經不聲的環顧了一周,並沒有發現異樣。
“就在這兒落腳。”
石姑做下決定。
跟來的馬幫夥計立即進樓裏打點,石姑夫妻二人一進,果然樓上的窗戶邊出一隻手來,是一隻男人的手,他很快將窗戶關上。
樓裏明明客人不多,掌櫃的卻不讓他們上樓去,皆因他們是漢人,並非寮國商人。
於是石姑幾人在廳裏坐下,尋了一個角落的位置,要了一壺茶收走了十兩銀子,這也忒貴,關鍵給了一壺茶,還沒有任何點心。
這十兩銀子的消費,要是放在南城漢人區,可以喝上好茶吃上致的點心了。
Advertisement
馬幫夥計給石姑夫妻二人倒茶,結果夥計先自己喝上一口的時候,沒忍住吐了出來,這哪是茶,這是沙土裏的水煮了幾片不知的葉子。
夥計的舉引起廳裏僅有的幾名客人注意,石姑使了個眼。
茶沒法喝,倒是可以先坐一坐。
沒坐多久,街道上又傳來整齊的腳步聲。
茶樓裏的客人都往外張,如石姑幾人一般對外頭好奇的不在數。
石姑看了一眼,小聲說道:“是阿拔族的勇士出,是打擂臺的。”
阿拔族這是有野心吶。
石姑和二板來了上京這麽幾日了,也不見阿拔族的人來報複,就是古怪,現在在街頭撞上,對方卻是醉心於勇士擂臺。
“或許等阿拔族裏出了宗師,咱們在上京才會有生命危險,第一個報複的就是咱們了。”
石姑的聲音小,隻有二板聽得到。
廳裏的客人此時也在說著阿拔族的事跡。
阿拔族中原本是出現了一全宗師的,可惜在六年前被燕國賢王所殺,不過阿拔族得到了一件賢王的戰利品,便是那柄連國君都誇讚的劍。
所以阿拔族先有宗師為國損軀,後有六年前在與燕國幽州城大戰時立下戰功,從而從一個無名小族變如今的大部落,更是在上京城裏占據著一方地位,著實不簡單。
Advertisement
這一次比武擂臺,阿拔族裏要是再挑選出一位宗師,那可就不得了。
石姑幾人默默地聽著。
隨著阿拔族的勇士過去沒多會兒,茶樓裏突然又迎來一位客人,那客人才出現,廳中便沸騰了起來,便是樓裏的掌櫃和夥計也紛紛上前,弓著,卑微的招待著。
來人穿著青襖,頭上帶著狼帽,腰間一柄大刀,刀鞘上是顯赫的族中圖騰,細看下像是一團火。
“烏蘭族人。”
廳中有人驚聲開口,那是一名漢族商人,當即就埋下頭去,烏蘭族在上京也是權貴部族,小百姓得罪不起。
是烏蘭旗,石姑一眼認出來,當即嚇了一跳,連忙拉了拉二板的袖子。
好在夫妻二人帶著帷帽出行,看不到真容。
當初在幽州城裏囂張無比的烏蘭旗,是烏蘭族的旁支,在幽州城裏掌了兵權,欺負石姑一家,最後被石姑一刀結果了他的命子,斷人子嗣的仇可是解不了的。
原本被權貴部族告了狀,被本家召回的烏蘭旗,石姑是怎麽也沒有想到會在這兒遇上他,真是冤家路窄。
烏蘭旗一進來,也沒有看掌櫃和夥計,隻是目隨便掃了一眼大廳的人後,便快步上樓去了。
樓上是有什麽人與烏蘭旗相見,還是說烏蘭旗今日就這麽巧合的來茶樓裏吃茶。
Advertisement
石姑見人上了樓,立即起,“咱們趕走。”
先後得罪了烏蘭旗和阿拔裏,眼下還是不要招惹是非的好。
隻是石姑才要走,便有樓中夥計突然跑過來,收拾桌子時,快速將一張紙條遞給。
石姑剛要看,夥計惡狠狠地叮囑:“別,出門再看。”
夥計心頭暗忖:“這些人也不知怎麽的就得罪烏蘭旗大人?”
夥計很快收拾好茶,轉而去,這一舉並沒有影響廳裏的其他客人。
石姑幾人出了茶樓,來到一僻靜之,石姑打開手中的紙條,隻見上頭寫著:“諳蠻族四宗師無名,而今在虎族舊部鑄場打造兵。”
石姑抬頭看向二板,夫妻二人心照不宣,樓裏果然還有其他人,不然依著烏蘭旗的脾氣,他在知道他們份時不可能不對報複。
所以那個人不僅借了烏蘭旗的名頭,還瞞過了樓裏的掌櫃和夥計,那人到底是誰?又是什麽份?為何在他們進樓時一直盯著他們看。
石姑從僻靜出現,看向前不遠的茶樓,卻看到樓上的窗戶閉,本看不出什麽況來。
倒是在此時,茶樓外的街道上,先前去往擂臺打擂回來的阿拔族勇士,在經過此街道時被一夥黑人攔下,隨後了手。
Advertisement
二板當即將媳婦護在後。
石姑隻得從二板後探出一個頭來。
這北城的治安更,還沒有漢人區舒適。
“我們走吧,不去諳蠻族府邸了。”
石姑做下決定。
馬幫的夥計這就去牽馬。
二板是聽媳婦的話,媳婦讓走他絕不會留。
幾人錯開打架的街頭,牽著馬悄無聲息的離開了。
到了出城北門的時候,小兵正盤查著,便有落荒而逃的阿拔族人往北城外跑,裏罵罵咧咧,“……定是那烏蘭小子,我必將此事告知大家主。”
石姑心頭吃驚,烏蘭旗果然還是那個烏蘭旗,當初被傷了命子後去阿拔裏軍營求助,實則是故意說阿拔裏軍營的巫醫能接上他的命子撒下的大謊,結果此人記恨到現在。
想想要是烏蘭旗知道石姑就在上京,剛才還同在一座樓裏吃茶,不知會氣什麽樣,怕是要將剁碎了不可。
猜你喜歡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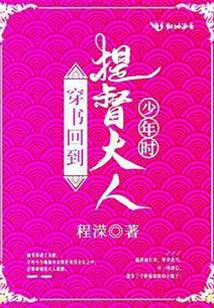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040 -
完結1044 章
法醫王妃別動刀
九王妃慕容諾有個+∞的膽子,你送她花,她看不上眼,你送她豪宅金山,她提不起勁兒,你讓她去驗尸,她鞋都不穿就沖在最前面!身為皇室顏值天花板的九王爺沐清風就很看不慣她,從來沒給過好臉色,寧可抱著卷宗睡覺也不回家。全王府都認定這對包辦婚姻要崩,直到有一晚慕容諾喝醉了,非要脫了沐......清風的衣服,在他身上畫內臟結構圖。蹲墻角的阿巧:完了,王妃肯定要被轟出來了!蹲窗下的伍叁七:王爺怎麼乖乖脫了,等一下……王妃怎麼也脫了?!!!
150.6萬字8 67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