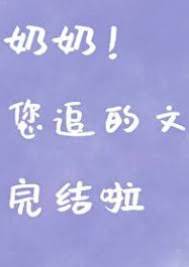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獨你悅人》 第172頁 番外
“梁空,我做噩夢了。”
“什麼夢。”
“我夢見,你不我,你轟轟烈烈地活在我的第三視角裏,跟我沒有一點關係,甚至我沒有機會認識你,然後很多年後校友聚會,你跟我問路,問完就開車走了,我就很難。”
聽見梁空膛裏悶悶一聲笑,隨即清脆一聲,玻璃杯被擱置在旁邊的大理石臺面上,瘦削單薄的後頸多了一層護衛。
是他的掌心。
蹭一蹭,一,將低落的緒捧起來。
“這不肯定假的嗎,夢都是相反的。”
“嗯”了一聲。
的確是假的。
夢境裏是那麼多年,清楚知道,彼此毫無集,他從來不。
現實是相反的。
全然不知道,他那樣喜歡著自己。
陪靜了一會兒,梁空低頭問,這麼膩歪著熱嗎?男人火氣大,他又剛從外頭回來,一灼燥,但見搖搖頭,梁空就不了,任由抱著。
“勞森來過嗎?”
回答:“中午來了,跟我講了很多杉磯好玩的地方。”
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梁空問:“有沒有什麼特別想去的地方?”
駱悅人想了想,仰頭看他:“想去第一次來杉磯,你帶我去的那家日料店。”
門口的暖簾換了,飾掛畫也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印象裏極衝擊的普魯士藍然無存,木架瓷瓶,皆都著一空寂的哀。
之前梁空頗費周折地挪了這家日料店的主廚去嶼鉑灣給做過一餐,駱悅人記得,這家店被梁空表哥買下來了。
Advertisement
無論是第一次來杉磯,還是後來在嶼鉑灣那次,都是梁空詢問的口味,負責點餐。
這還是第一次細看菜單。
配了樸素簡圖的折頁菜單,每道菜品都印著日文和英文。
日文看不懂,駱悅人只能通過英文猜大概,看到尾頁的特別菜品時,眼波一亮,忽覺新奇。
“為什麼鰻魚拌飯的名字要‘好的麥子’?是珍惜糧食的意思麼?”
一旁的服務生是兼職的國留學生,會說中文,態度也好,不過到崗時間不長。
“菜單是我們老闆擬的,好像有些特別含義吧。”
點餐結束,服務生欠離開。
駱悅人還在研究餐單的設計,因為現在自己也從事容產出,對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文字和圖片都格外敏留心。
細細看完一圈後,發現所有餐品的名字都是平鋪直敘的表述,食材加上烹飪手法,一眼就能看明白。
只有這道並不特別卻獨獨被歸為特殊菜品的鰻魚拌飯,起名比較象。
好的麥子。
駱悅人也點了,並沒有嘗出什麼特別,就是很尋常的鰻魚拌飯。
用餐結束,出了日料店,還在好奇這個。
異國街頭行人很多,梁空牽著的手走在其中,聽好奇不已地分析,轉頭跟說:“他前友的名字嘉穗,嘉就是指好的嘉,穗是麥穗的穗。”
好的麥子,就是嘉穗。
駱悅人恍然,想到那次冬天早晨離開杉磯,開著車送自己去機場的生。
好像跟一般大的年紀,說話聲音又甜又,笑起來眼睛彎彎的,特別熱好心。
Advertisement
“那為什麼跟鰻魚拌飯有關?”
梁空對別人的事並不八卦,也不留心別人的朋友,只是這位前任對陳淨野意義非凡,他多知道一些。
“不喜歡日料,也不吃生食,以前陪著陳淨野來過很多次,每次來都會點鰻魚拌飯。”
駱悅人聽懂了,應該是很喜歡陳淨野,所以一次次遷就他的口味。
可嘉穗已經是前友了。
“你表哥是忘不掉嘉穗,想告訴,他還嗎?”
梁空淡淡勾:“或許吧。”
“還人的。”未知全,駱悅人只在看客視角這樣歎一句,很快目就落在梁空上。
梁空察覺,垂眼看,還是年時那副略帶挑釁又暗含調戲意味的樣子:“又盯著我?”
駱悅人去抓他的手,著他掌心,異國老街上的夜霓虹映照在仰視的眼底,眸輕。
“如果是你,你就不會這樣,對吧?”
“哪樣?”
駱悅人說:“就是和一個人分開之後,明晃晃的,表達自己的想念和不舍,又或者,希對方知道,在離開後,自己過得並不好。”
世間的大多相似,但人與人完全不同。
如果有人問,為什麼會跟梁空走到一起,駱悅人絕不會說是他們格投契。
即使是這麼長時間,他們都沒有任何被彼此同化的跡象,例如,骨子裏的多愁善,經常會因為一個小小的問題,無限擴散,進而開始傷春悲秋。
有時候,試圖拉著梁空一起共。
他每每都能一句話破壞氣氛,人啼笑皆非。
Advertisement
譬如此時,暗指他總是喜歡把藏得很深。
總是一副混不吝不掛心的浪態度,十分只肯講三分,剩七分全藏在不為人知、也無需回應的細節裏。
他明明可以順著話接,說是啊,我你,即使你離開我捨不得,我也不太會表達。
然後可能得死去活來。
可他偏不。
他吊兒郎當說:“那你現在就離開我一個試試,我馬上死給你看,你看我這樣表達想念和不舍合不合適?”
駱悅人鼓著腮,憋笑著,對他深無語。
這個人啊,他會把心給你,但你不能指他當著你的面表演掏心掏肺。
他永遠做不來。
梁空沒牽的手上拿著冰飲,用杯底部在臉頰鼓起來那塊一下。
駱悅人歪歪頭,知道他在逗自己,幽幽睨他一眼,邦邦說:“你才不會呢!索卡說他問過你,你說你不願意為我死。”
梁空結一滾,咽下飲料,接話,囂張氣的樣子:“我命金貴,我可太怕死了。”
駱悅人晃晃兩人牽在一塊的手,低頭咬吸管。
不說話,懶得穿。
那話是高中畢業索卡問他的,因為索卡理解不了當時的梁空,就問他到底有多喜歡,是不是被魘住了,現在是得能為去死了嗎?
梁空答,他不會,他這輩子都做不到用死去證明喜歡一個人。
他這開局即是贏家的人生要風得風要雨有雨,太金貴了,他還沒瀟灑夠呢。
可他也說了另一句。
人不是時時刻刻都能理智思考的。
“如果真有一刻,有危險,需要我,我會想也不想地站在面前。”
Advertisement
是很怕死,也不惜命。
因為剛剛提到陳淨野的朋友,駱悅人想到那次離開杉磯,在機場跟嘉穗說過一句話。
說,以後再也不來杉磯了。
時隔多年,還是來了。
霾盡散地踏上這片土地,和梁空看這裏好看的晚霞與晨曦。
“梁空,你記得我跟你說過我爸爸嗎?他跟我媽離婚後,跟我說,讓我不要他們的影響,從此不再相信了,我當時跟他說,我相信,我只是不相信能長久。”
說完,自己補了一句:“是真的。我不相信能長久,我一直覺得喜歡是一種消耗,熱總是很短暫的,很快就會厭倦,會煩,會累,我看我大學室友談,周而復始,都是這樣的。”
所以整個大學期間,即使不缺人追,也從來沒有想過要跟誰嘗試這樣的。
梁空輕笑道:“這是期待太多了吧。”
“喜歡一個人,不就是有無限期待嗎?”
梁空點頭:“可以啊,可以期待。場如賭局,誰不是沖著贏來的?這無可厚非,但是下注前要想好,萬事無絕對,可能會本無歸。”
他說這話的樣子很帥,像他年時的名曲子,警報一樣,勢如破竹,銳利又孑然。
駱悅人著他:“那你呢?”
他眼一瞥,住的注視,輕聲又不羈說:“心甘願的事,我一向輸得起。”
那一刻的梁空,熠熠生輝。
想起高中在九州路的保齡球館,對面有家甜品店,給他買草莓蛋糕,又擔心反季節的草莓不甜,他當時說,管他甜不甜。
他一直都是很酷的人。
幾天後,七月二十五,梁空生日。
中午請了親友來家裏慶祝,生日蛋糕已經切過一回,晚上就他們兩個,駱悅人自己在廚房烤了一個小蛋糕,只有簡單的水果裝飾。
駱悅人上蠟燭,拿出打火機準備點燃,跟他說:“這樣你可以再許一個願。”
梁空說,他中午那會兒,已經許了三個願,沒什麼可許的了。
火苗竄出來又熄滅,被燙灼過的金屬片還有餘熱,駱悅人拇指搭在上面,微微蹙住眉心。
中午一群人唱著生日快樂歌,梁空許願的時候,壽星公本人草草應付似的,眼沒閉幾秒,就把蠟燭吹滅了。
就那幾秒,他居然許了三個願?
真許了三個,一點也不潦草。
梁空說:“健康,快樂,我。”
“三個。”
他說完。
駱悅人停在這省去主語的六個字裏,良久後,低聲問:“你怎麼不給你自己許一個?”
他又玩破壞氣氛那一套。
“爺都應有盡有了,再給自己許願,不合適吧。”
“那你怎麼不給自己許健康快樂?”
他靠著籐椅背,黃燈影裏瞧,無所謂地說:“健康看命,快樂靠你。”
駱悅人懂了。
這人選擇的迷信,無怪老太太說他從小有佛緣,又見誠心。
會客廳的臺有一夜風,駱悅人低頭,手掌護著風,象徵地點了幾蠟燭,他來吹。
拔去蠟燭,切下一小塊蛋糕,遞過去,要他嘗嘗自己的手藝。
然後,雙手托腮,目灼灼看著他。
“梁空,能跟你商量個事嗎?”
忽然正經起來,梁空有點不適宜,目移過去,手指揩了一下自己邊草莓味的油,點了一下頭說:“商量,講吧。”
“我待會兒親你,你別躲。”
梁空目在四周掃了一下,終於明白,不久前這塊小蛋糕做好,一手端蛋糕,一手拉著他,連上三樓,尋尋覓覓,找到這個臺來是為了什麼。
第一次來杉磯,就是在這個臺。
他躲開了那個讓做夢夢到都會哭的吻。
收回目,梁空把架起的二郎放下,兩隨敞開,拍自己的膝蓋,示意:“來吧。”
駱悅人角一揚,撲進梁空懷裏,瓣印在他上,還有殘餘的草莓油的味道。
彌補憾的一個吻,不再深,也心滿意足。
兩人呼吸灼熱匯,都睜著眼睛,卻都默契垂睫,若有所思地維持著這個親到不能再親的作。
猜你喜歡
-
完結633 章

天價暖婚:司少放肆寵
結婚前夕遭遇退婚,未婚夫不僅帶著女人上門耀武揚威還潑她一身咖啡。池心瑤剛想以眼還眼回去,卻被本市權貴大佬司少遞上一束玫瑰花。捧著花,池心瑤腦子一抽說:「司霆宇,你娶我吧。」「好。」婚後,池心瑤從未想過能從名義上的丈夫身上得來什麼,畢竟那是人稱「霸道無情不近女色」的司少啊!然而,現實——池心瑤搬床弄椅抵住房門,擋住門外的司姓大尾巴狼:是誰說司少不近女色的,騙子!大騙子!!
59.4萬字8 104591 -
完結490 章

嬌妻很大牌:秦先生,你被捕了
夏云蘇懷孕了,卻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誰,她只知道自己的嬸嬸跟別人合謀,要將自己送到其他男人的床上。很快,夏云蘇流產了。她被冠以水性楊花的罵名,卻發現自己的未婚夫搞大了堂妹的肚子。所有人都在奚落她,包括她的母親。直到那個男人出現,用一紙合同逼她…
85.1萬字8 33006 -
完結88 章

般配關係
【先婚後愛 暗戀成真 豪門霸總 白月光 雙潔 HE】【嬌俏傲慢女律師X深情狠厲大老板】為了家族利益,許姿嫁給了自己最討厭的男人俞忌言。在她這位正義感爆棚的大律師眼裏,俞忌言就是一個不擇手段、冷血無情的生意人。何況她心中還藏著一個白月光。婚後俞忌言配合她的無性婚姻要求,兩人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無事。直到許姿白月光回國,許姿開始瘋狂找俞忌言的外遇出軌的證據,想以此為由跟俞忌言離婚。得知俞忌言有個舊情人,許姿本以為勝券在握了,沒想到俞忌言竟將她壓到身下,承認:“是有一個,愛了很多年的人。”“你想要我和她親熱的證據是不是?”俞忌言輕笑,吻住她:“那好,我給你。”
20萬字8 24924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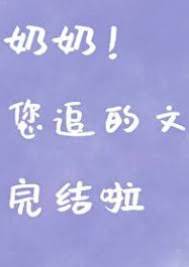
南風知我意
清遠公安裴西洲,警校畢業履歷光鮮,禁慾系禍害臉,追求者衆卻無一近的了身,白瞎了那顏值。 某天裴西洲受傷醫院就醫,醫生是個女孩,緊張兮兮問他:“你沒事吧?” 衆人心道又一個被美色迷了眼的,這點傷貼創可貼就行吧? “有事,”裴西洲睫毛低垂,語氣認真,“很疼。” “那怎樣纔會好一些?” 裴西洲冷冷淡淡看着她,片刻後低聲道:“抱。” - 緊接着,衆人發現輕傷不下火線的裴西洲變乖了—— 頭疼發熱知道去輸液:南風醫生,我感冒了。 受傷流血知道看醫生:南風醫生,我受傷了。 直到同事撞見裴西洲把南風醫生禁錮在懷裏,語氣很兇:“那個人是誰?不準和他說話!” 女孩踮起腳尖親他側臉:“知道啦!你不要吃醋!” 裴西洲耳根瞬間紅透,落荒而逃。 ——破案了。 ——還挺純情。 - 後來,裴西洲受傷生死一線,南風問他疼嗎。 裴西洲笑着伸手擋住她眼睛不讓她看:“不疼。” 南風瞬間紅了眼:“騙人!” 卻聽見他嘆氣,清冷聲線盡是無奈:“見不得你哭。”
36.3萬字8.18 155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