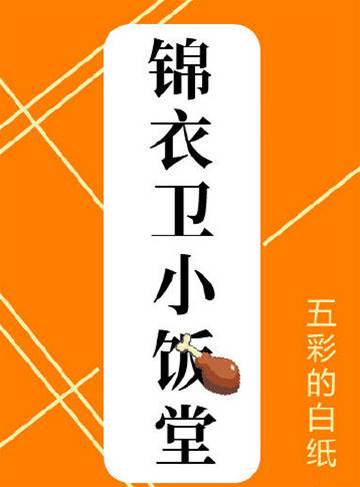《仵作娘子》 第56章 四喜丸子(十五)
秦業聽得一怔,“吳公子?”
蕭瑾瑜沉了沉聲,“他的腰骨斷了。”
“哦!”秦業恍然道,“你說的是在燕子巷最裡頭那家的吳公子吧?”
“正是。”
秦業嘆了口氣,把手裡的碎銀子擱到那張破舊的圓木桌上,爲難地著手,皺起眉頭道,“你要是問別人,我還能說幾句……這吳公子,他家管家老爺特意代好幾回了,什麼都不讓說啊……敢問,安公子跟吳公子是什麼啊?”
“沒什麼……就是我的一個小輩。”蕭瑾瑜神微黯,“他脾氣犟得很,出事之後便再不肯見我……不瞞先生,我是從京城來楚水鎮提親的,那日恰在先生這裡遇見跟他多年的管家,聽他病得厲害,就想從先生這裡打聽些他的近況,否則實在放心不下……”
蕭瑾瑜薄脣輕抿,眉頭聚了一個清淺的川字,細的睫微垂著,看著杯中緩緩浮沉的茶葉,捧著茶杯的手蒼白修長,微微發,這副憂心傷的模樣把秦業看得一下子慌了手腳,趕忙道,“安,安公子,你別急,別急……你是他家親戚,那有啥不能說的,是吧……你你你你彆著急,先喝點兒水,喝點兒水……我這就拿醫案去啊!”
“多謝先生了。”
“應該的,應該的……”
******
就聽著外面叮鈴桄榔好一陣子,秦業滿頭大汗地夾著幾本大小不一的醫案走進來,放到蕭瑾瑜面前的桌上,“我給吳公子治病有一個來年頭了,醫案寫得潦草,安公子別見怪……”
蕭瑾瑜又認真地道了聲謝,拿起最上面一本慢慢翻開。
秦業抹了把汗,一邊往快燃盡的炭盆裡添炭火,一邊嘆道,“安公子,你別怪我不會說話……吳公子這子,能撐到現在可真是不容易啊……”
Advertisement
“讓先生費心了。”
“也怪我才疏學淺,醫不……好在吳公子子強,被折騰啥樣都從沒有過輕生的念頭,好幾回眼瞅著都不行了,還是讓他給熬過來了。”
蕭瑾瑜看著寫得麻麻的醫案,也說不出心裡是個什麼滋味,“他就是這樣的脾氣……”
“說到底,還是讓他腰上那傷給害的,也不知道遭的什麼罪,讓人打那樣……治得太晚了,差點兒就連上半截子也給廢了……你是沒瞧見,我頭一回見他的時候,他整個子都不了,上褥瘡都爛得連片了,瘦得跟副骨頭架子似的,幹睜著眼睛連句話也說不出來,就一直盯著一個棋盤,那真是又嚇人又可憐啊……”
難怪當年蕭玦連個招呼都不打就匆忙離京了……
蕭玦那麼驕傲的一個人,就是被個尋常路人看到自己那副樣子也崩潰,何況是滿京敵友……
蕭瑾瑜心裡揪了一下,驀地一陣暈眩,手上一鬆,醫案“啪嗒”一聲掉到了地上。
秦業趕忙從炭盆邊站起來,走過來拾起醫案,一邊搭脈一邊張地看著臉煞白的蕭瑾瑜,“安公子,怨我上沒個把門兒的……你沒事兒吧?”
蕭瑾瑜任由他著自己的脈,另一手按著額頭微微搖頭,淺淺苦笑,“讓先生見笑了……”
“沒有的事兒……”秦業看蕭瑾瑜還算平靜,鬆開他的手腕,苦笑著嘆氣,“怨我,吳公子要是遇上個有本事的郎中,沒準兒他這會兒都站起來了,攤上我這麼個窮鄉僻壤的野郎中……實在慚愧啊……”
蕭瑾瑜聲音微啞,“先生言重了……先生對他如此用心,是他修來的福氣……”
Advertisement
“安公子別這麼說,我可實在不起啊……”
蕭瑾瑜輕輕搖頭,緩緩靠到椅背上,靜靜看著滿臉謙遜的秦業,“先生若不起,那便沒人得起了……除了先生,這世上還有什麼人能爲了治他,一連殺死一百多個人呢……”
秦業像是冷不防被人狠了一掌似的,連表帶一下子全僵住了。
“安公子,在下不明白……”
蕭瑾瑜把目落在那盆燒得正旺的炭火上,燒紅的炭火模糊紅豔豔的一片,嚨裡勉強發出的聲音傳到自己耳中已經飄渺得像從天外傳來的了,“我也不明白……你把我迷暈,能做些什麼……”
******
楚楚一直在縣衙停房忙到太西斜,跑回家仔細洗了澡換好服,才又跑回縣衙來藉著廚房煮排骨湯。
雖然外面連豬帶圈都燒灰了,可廚房到底是離那個豬圈最近的地方,廚子心慌膽得很,鄭有德也心有餘悸,索讓廚房關門一個月,主簿還煞有介事地在門楣上了張從觀音廟求來符,說是驅驅邪氣,可看著更讓人渾發了。
楚楚找人討來鑰匙進去的時候,整個廚房裡裡外外一個人都沒有。
反正是要給王爺做飯,纔不願意有別人幫忙呢!
從過年醉了一次酒之後,王爺的胃口一直不大好,每回吃飯就吃那麼兩口,誰勸也吃不下去,整個人看著都沒什麼神,這鍋排骨湯一定要做得香香的,讓他多吃點兒。
王爺還答應了,今晚親,像第一次那樣親,親多次都行。
想讓王爺親十次,不對,一百次……唔,一百次有點兒多,會把王爺累著了……那就五十次吧!
Advertisement
楚楚一邊樂滋滋地想著,一邊收拾著生上竈火,燜上米飯,洗淨那盆剁好的排骨,門路地煮起排骨湯來。
還特意選了兩段鮮的藕切進去,又撒了把杞子,湯煮得差不多了,又燒了一葷一素,一頓飯做好,原本冷冰冰的廚房已經暖呼呼香噴噴的了。
飯做好了,端進屋裡擺好了,放涼了,還沒見蕭瑾瑜回來。
楚楚趴在桌上耐心地等著,心裡還是忍不住犯嘀咕。
就是去酒坊看看酒,怎麼能看上一天啊?
難不是王大爺的熱勁兒上來,拉著他嘗酒,把他灌醉了?
還是王大爺知道了他是京城來的,跟他聊天聊忘了時辰?
要麼……
楚楚胡想著,想著想著迷迷糊糊就睡著了,再一睜眼,天都黑了,屋裡門外還是沒見有蕭瑾瑜的影子。
他答應好了回來吃飯的,他說了過年不騙人的,那是突然有急事,還是突然出了事呀……
楚楚這麼想著就心慌起來,等也等不下去了,奔出衙門一口氣跑到酒坊,遠遠看見酒坊門關著,心裡一下子急得要著起火來了。
旁邊秦氏醫館的門還開著一半,從裡面出明晃晃的亮,楚楚腳都沒停就衝了進去,喊了好幾聲,秦業才匆忙從後院走進來。
“呦,楚丫頭,這是怎麼了……咋跑這樣啊?”
楚楚連汗都顧不得抹一下,急道,“秦大叔,酒坊今天開門了不?”
“你這丫頭又過糊塗了吧,這還沒過初五呢,誰家開門做生意啊……”
楚楚悔得直跺腳,算著親的日子過了,怎麼就把正經日子都忘了呀!
“你倆人也真有意思……安公子纔來問了一遍,你咋又來問一遍啊?”
Advertisement
楚楚一聽這話,心裡一喜,忙道,“秦大叔,你看見他啦?”
“看見啦,就是今天白天時候的事兒……他來買酒,酒坊沒開門,他就到我這兒歇了歇腳……”
楚楚趕追問,“那他後來去哪啦?”
“說說話就走了……走的時候還跟我打聽上凰山那條道好走來著,估麼著是上山去了吧。”
“就他一個人?”
“是啊……咋啦?”
他昨晚還犯著風溼,上山,這麼晚都沒回來……
楚楚剛落下的心又重新揪了起來,比剛纔揪得更了。
“沒咋……謝謝秦大叔!”
“沒事沒事……慢點跑,別摔著!”
“哎……”
******
щщщ⊙ Tтkд n⊙ ¢ O
蕭瑾瑜恢復意識的時候,最先覺到的就是冰冷空氣中濃重的腥味,空得發熱的胃裡一陣痛,原本還有些昏昏沉沉的意識一下子就清醒了。
他能覺到自己正直躺在一張只鋪了一層牀單的破木板牀上,又冷又的牀板硌得他脊骨生疼,卻連翻挪一下的力氣都沒有。牀單上散發出腥與汗臭混雜的氣味,不用看就知道一定是髒得不能再髒了。
一百多人裡,不知道有多人死前躺過這張牀,躺過這張牀單……
蕭瑾瑜吃力地擡起仍有點兒發沉的眼皮,從一片昏黃模糊中漸漸辨出一間屋子的廓。
目所能及的半間屋子範圍裡,土牆,圓頂,牆上沒門沒窗,一邊牆角有個破舊的木樓梯,從地面一直延到頂子上。
說這是間屋子,卻更像是個地,溼,冷,憋悶,腥味裡夾雜著令人作嘔的黴腐味,而腥味的源頭就堆在他正前方的牆底下。
一四肢頭顱與軀幹拆分開來的隨意地堆著,像一堆尋常的垃圾一樣,的腦袋正面朝著蕭瑾瑜,一雙眼睛空地看著前方,極盡平靜卻看起來滿是悲哀。
在這堆被拆分開的裡,正好缺了一條胳膊。
蕭瑾瑜正盯著那堆看,與樓梯相接的頂子上聲音一,一束比屋裡更亮幾分的從樓梯上面投下來,秦業低鑽進來,轉手蓋上頂子,慢悠悠地從樓梯上走下來,把破舊的樓梯踩出刺耳的吱嘎聲。
看見牀上的蕭瑾瑜睜著眼睛,循著他的目看過去,秦業略帶憾地道,“我拉著板車往醫館裡拖人,正巧給他撞見,說書的人太快,不然也用不著他這把年紀的……你放心,我不會這樣對你。”
蕭瑾瑜靜靜淺笑,平靜得好像這會兒還是在坐在醫館堂小屋裡,圍著炭盆捧著熱茶,跟一個仁心仁的淳樸郎中閒聊一樣,“那要怎樣對我……”
秦業不急不慢地走到牀邊,緩緩捲起袖,“你跟吳郡王是親戚,年紀跟吳郡王差不多,也是殘廢的,在你上試驗醫治吳郡王的法子最合適不過……我給你把過脈,你雖然不好,但還是比吳郡王要好些,只要行幾套針,把你五臟六腑傷損到跟他差不多的程度,再敲斷你的腰骨就了……你放心,我會很小心,在醫治吳郡王的法子研究出來之前,你不會死的。”
秦業說得很平靜,平靜裡帶著種司空見慣的麻木。
蕭瑾瑜比他還平靜,平靜得好像剛纔說的不是自己,這會兒正被一件件剝下服的也不是自己一樣,“你在一百多人上研究了這麼久,不會一點收穫都沒有吧……”
“當然有。”秦業一邊嫺又小心地著他的服,一邊漫不經心地道,“早先用的都是活蹦跳的人,給他們灌上迷藥,讓他們躺在牀上不了,吃喝拉撒都在牀上,等不多些時候就能生出褥瘡來,給吳郡王治好褥瘡的藥就是這麼試出來的……再往後治他腰骨的傷,那就得把人腰骨敲斷了試,開始手勁兒位置都沒個準頭,還沒開始試藥人就死了,後來練了就有準兒了……”
秦業把蕭瑾瑜上的服淨,拉過一盆溫水,丟進去一個布巾,洗了兩把,開始給他從上往下洗子。
他病得起不來的時候,楚楚沒幫他洗子,有時也是他意識清醒的時候,他以爲自己已經習慣被人這樣洗了,可這會兒被秦業同樣一不茍地著,沒有那種溫暖清爽的舒適,只覺得一陣陣的噁心,噁心自己似乎越越髒的子。
秦業認真地著,仍然漫不經心地說道,“之後又發現吳郡王上的其他病對治腰骨的傷也有影響,就用一套前人研究的傷經損脈的針法,把敲斷腰骨人的臟腑傷到跟他一樣的程度……開始也是沒個準頭,試死了不,後來慢慢就了,但人跟人還是不一樣,吳郡王能撐這麼久,他們這些人都撐不過多時候,所以過一段日子就得再找個新的從頭來……”
蕭瑾瑜任他擺弄自己癱無力的子,靜靜地接話,“一年多……一百多個人,就沒人向衙門報失蹤嗎……”
“都是些附近的流民乞丐窮酸漢,死了活了沒人在意,能爲救治吳郡王而死,就算他們祖墳上冒青煙嘍……我倒是好奇,連縣衙都沒發現,你纔剛來這兒沒幾天,怎麼就知道那些人是死在我這兒的啊?”
猜你喜歡
-
完結486 章

三年後,她帶戰神夫君炸翻全京城
空間➕爽文➕雙潔➕多馬甲 “什麼?天盛國又又又出了新武器,投石機?機械馬?快投降!這誰打的過?” “什麼?天醫穀又又又出了新藥?趕緊搶,可不能錯過!!!” “什麼?玄靈宗現世了?趕緊讓各皇子們去學習!” “什麼?蓮福鳳女降世了?得此女既得天下?等等……怎麼被人捷足先登了???” 這不是雲家的那個醜丫頭麼? 某穆爺:“這顆珍珠,我先得了。” 眾人咬牙切齒,悔恨交加。 然而,正當天下要因此大亂時,雲妙站出來一句:“誰敢亂?” 各方勢力齊呼大佬,統一跪拜! 頓時,天下震驚,續太平盛世,四國再不敢動。 命天士歎服:此女能揭天下風雲,亦能平天下戰火,奇女子也!
90.2萬字8 31588 -
完結2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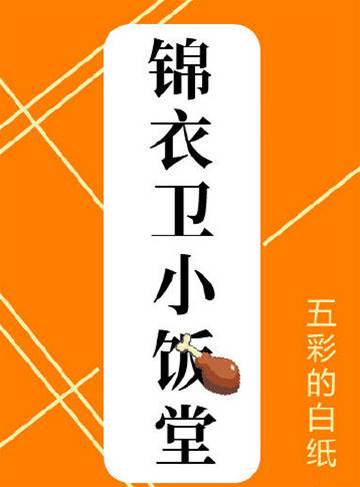
錦衣衛小飯堂(美食)
自從董舒甜到錦衣衛小飯堂后,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指揮使最近吃了什麼#錦衣衛1:“我看到夜嶼大人吃烤鴨了,皮脆肉嫩,油滋滋的,嚼起來嘎吱響!”錦衣衛2:“我看到夜嶼大人吃麻婆豆腐了,一勺澆在米飯上,嘖嘖,鮮嫩香滑,滋溜一下就吞了!”錦衣衛3:…
77.3萬字8.25 39928 -
完結2342 章

盛世紅妝傾天下
穿越前,蘇年是醫院的拼命三娘,外科一把手;穿越后,她變成戚卿苒,是人人唾棄的花癡病秧子。本只想好好養好這具破身體,誰知莫名發現自帶金手指,腦子里有一部醫書寶典。
217.4萬字8.18 25315 -
完結175 章

我靠美食白手起家
一睜眼,竟穿成無父無母、食不果腹的農家女,外贈一個嗷嗷待哺的傻相公。 莫輕輕恨不得在公屏上打出七個大字:非酋穿越須謹慎! 不過,作爲莫家小飯館唯一繼承人,這點困難怕什麼? 她帶着傻相公,靠美食白手起家。 燒花鴨,熗青蛤,桂花翅子什錦鍋。 溜魚脯,罈子肉,三鮮豆皮杏仁酪。 從小縣城,到京城;從河畔小食攤,到譽滿京城的莫家食肆。一步一個腳印,將生意越做越大,賺得盆滿鉢滿,還置辦了間大宅子。 莫輕輕愜意地往後一靠:我此生足矣! 衆人:不!你還差個伴兒! 莫家小娘子,樣貌好,廚藝絕,聽聞傻相公也是撿回的,實則還待字閨中,於是上門提親的人擠破了腦袋。 不料某日,一個錦衣華服的俊美公子沉着臉將求親者驅之門外。 路人1:那不是之前的傻相公嗎?收拾收拾還有模有樣的。 路人2:什麼傻相公,那是當今翰林學士、兼任國子監司業的蘇大人! 路人3:蘇大人怎麼跑這兒來了?難不成他也想娶莫小娘子? 莫輕輕一臉驕傲:不!那是因爲蘇大人也愛吃本店的菜! 蘇瑾笑而不語,卻暗暗糾正:世間美味,都不及你萬分之一的好。
26.4萬字8.18 102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