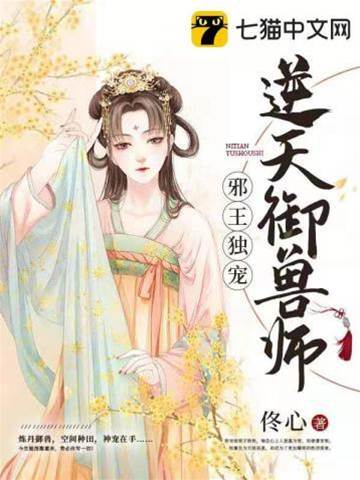《滿級醫修重回真假千金文》 318 告密
(4, 0);
庾家餘孽?!兩個守門的錦衛都微微變了臉,神一肅。【】
庾家落罪後,庾家滿門被抄,庾思、上清等主謀被判了斬立絕,京城的庾家人全數被收押,皇帝還命錦衛去了豫州緝拿其他庾氏族人,可以預見的是,庾氏闔族恐怕都會被發配邊疆。
這要是還有庾家餘孽流竄在外,那麼就是錦衛失職。 第一時間更新最新章節,盡在s͓͓̽̽t͓͓̽̽o͓͓̽̽5͓͓̽̽5͓͓̽̽.c͓͓̽̽o͓͓̽̽m
方臉錦衛正想進去通稟,卻見一道高大拔的影恰好從大門的另一邊走了出來,只是眼眸半瞇,就自有一不怒而威的氣勢。
「什麼庾家餘孽?」來人冷聲道,言辭簡潔,可每個字都仿佛帶著霹靂之力。
兩個守門的錦衛連忙對著來人行禮道:「何指揮使。」
怦怦!顧瀟不由心跳加快,著正前方的錦衛指揮使何烈。(5,0);
他咽了咽唾沫,努力地穩定著緒,抱拳行禮:「見過何指揮使。」
何烈的後方又走出了另一個錦衛,對著何烈附耳說了兩句。
何烈濃眉一挑,再看顧瀟時,眸深了一分,仿佛此刻才真正看到了顧瀟。
「顧瀟,」何烈一語道出了顧瀟的名字,單刀直地問道,「你說顧淵窩藏了庾氏餘孽?你可知誣告朝廷命是何罪?」
顧瀟的心跳再次失控地加速,心裡告訴自己:錦衛是皇帝的眼線,消息靈通,認識他是顧瀟,也不是什麼稀罕事。
顧瀟正道:「何指揮使,我所言句句是真,據我所知,庾思還有個外室逃竄在外。」
Advertisement
他說話的同時,灼灼的目地盯著何烈,心提到了嗓子眼,幾乎忘了呼吸。
旁邊的車夫也是如坐針氈,惶惶不安,覺街道上的那些行人全都在著他們,這一道道目像是帶刺似的。
「哦?」何烈淡淡道,不聲地看著顧瀟,連眼角眉梢都不曾一下,喜怒不形於。(5,0);
的確,庾思在京城有個得寵的外室,還懷了孕,偏偏錦衛幾乎將整個京城掘地三尺,也找不到人。
顧瀟還以為何烈不信,像竹筒倒豆子似的趕道:「我還知道,庾思那個外室生了個兒子。」
「何指揮使,他們母子兩個現在就窩藏在遠安街的原定遠侯府中,還請大人趕前去搜查,也免得讓人犯尋機跑了。」
何烈瞇了瞇眼,注視著臺階下方的顧瀟,一手地握著腰側的佩刀,沒有立刻表態。
他本就比顧瀟高大威武,此刻又站在石階上,仿佛一座巍峨的大山矗立在前方,只是他的存在,就會給顧瀟一種無形的力。
「……」顧瀟的額角滲出了冷汗。
若是錦衛顧忌大皇子,而不願意妄,完全可以當這件事不曾發生過。
顧瀟深吸一口氣,拔高嗓門,把早就準備好的說辭複述了出來:「太祖皇帝有言,凡實名舉報必接,有接必查,有查必果。」
他嘹亮的聲音幾乎響徹了半條街,走過路過的行人也大都聽到了。(5,0);
他今天來錦衛就是實名舉報,錦衛若是不接,那就有違太祖創立錦衛的初衷。
「還是說,錦衛不敢查?!」
顧瀟一字一句地又道,最後的這句話等於是把何烈拱了上去,就差直說對方堂堂錦衛指揮使怕了顧淵或者在徇私。
Advertisement
何烈俯視著顧瀟,瞇了瞇銳利的眼眸,一危險的氣息在無形間釋放了出來。
旁邊的方臉錦衛察言觀,上前了半步,代自家指揮使發出警告,字字如刀:「顧瀟,太祖皇帝亦云,若是誣告,可是要杖責五十、充軍三年的!」
可不是什麼阿貓阿狗都能無憑無據地跑來北鎮司囂的!
顧瀟心裡有那麼一點發虛,但還是沒有躲開視線,昂著脖子道:「我沒有誣告。」
「人如今就在顧府里,何指揮使只要帶人去顧府搜查就是了!」
何烈盯了顧瀟良久,目凜冽,直看得顧瀟的脖子後滲出了一大片冷汗。
有那麼一瞬,顧瀟幾乎想退了,卻聽何烈淡淡道:「好!」(5,0);
他這一個字就是一錘定音。
顧瀟如釋重負,角抑制不住地翹了起來,目灼灼。
何烈一聲令下,麾下的錦衛們就立刻行了起來,不過短短一盞茶功夫,一隊二十來人的隊伍就從北鎮司出發了,顧瀟自然也隨行。
錦衛所經之聲勢赫赫,鮮怒馬,那些路人、車馬無不避讓,頗有一種風聲鶴唳的氣氛。
一炷香後,一行人就在路人驚疑不定的目中抵達了遠安街的顧府,顧府的朱漆大門被錦衛重重地叩響。
「咚咚咚!」
門房一邊著「來了」,一邊急忙過來開門,見來者竟是錦衛,驚呆了。
其中一名錦衛威風凜凜地說道:「我們何指揮使有要事要見顧千戶!」
饒是這名錦衛的態度還算不錯,來應門的門房還是有些心神不寧,畢竟錦衛的威名在京城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任誰都知道錦衛登門十有八九沒好事。
Advertisement
門房略帶幾分地結地說道:「這位大人,我們大爺在小花園裡宴客。」(5,0);
一個婆子有些腳,但還是立刻往西北方跑去,打算去稟告顧淵。
何烈留了幾個錦衛在府外,自己帶著十幾人邁高高的門檻,對於府外那些聞聲過來看熱鬧的百姓全不在意。
「何指揮使,我領您過去吧。」顧瀟帶著幾分迫切地自告勇道,從人群後面了上來。
直到此刻,顧家的門房這才發現顧瀟竟然也在。
在顧瀟的引領下,一行錦衛就箭步如飛地朝小花園方向走去,步履間,自有一肅殺之氣。
所經之,仿佛凜冽的寒風呼嘯而過,顧府的下人們都提心弔膽,不知道到底出了什麼事惹得錦衛登門。
顧瀟自然注意到了這些下人的不安,想起之前被護衛驅逐的事,就覺得出了一口惡氣。
他昂首闊步地往前走去,已經迫不及待地等著看顧淵變臉的樣子。
小花園的水閣里,熱鬧依舊,樊北然、路似、岳浚等人一個沒走,還在喝酒劃拳,說笑玩鬧。(5,0);
哪怕是看到了錦衛的到來,這些人都相當平靜。
他們認識何烈,何烈也認得他們中的不人,這些公子哥雖然不是家中的長子、繼承人,可也都不是什麼默默無名之輩,一部分人有在軍中、五城兵馬司、上十二衛任職,也有幾個是有名的紈絝子弟。
顧淵落落大方地起了,對著何烈拱了拱手:「何指揮使。」
他的神與姿態相當放鬆,即便是面對令人聞風喪膽的錦衛指揮使,也是一派談笑自若,仿佛站在他跟前的只是一個尋常人。
何烈開門見山地道明了來意:「顧千戶,有人舉報貴府藏匿庾家餘孽。」
Advertisement
說著,何烈的目看向了幾步外的顧瀟,「舉報人就是令堂弟。」
水閣,靜了一靜,一眾公子哥面面相看,皆是一怔。
顧淵還沒說話,路似搶先一步質問顧瀟道:「顧瀟,你莫名其妙攀扯什麼庾家餘孽,就是為了報復阿淵剛才把你趕出去嗎?!」
路似冷哼了一聲,重重地放下手裡的酒杯。(5,0);
眾人輕蔑的目如一把把刀子般向了顧瀟,顧瀟渾不在意,反而將下抬得更高了。
「報復?」何烈疑地挑眉。
解釋的人是樊北然:「剛才我們喝酒喝得好好的,顧瀟突然不告而訪,跑來搗,就讓阿淵給趕了出去。你們來得這麼快,想必是他離開這裡後,就去了北鎮司吧。哼,這還不是報復嗎?!」
「我沒有報復!」顧瀟下高高昂起,朗聲道,「我說的都是實話,這府里分明就有嬰兒的哭聲,可我大哥矢口否認,非說是貓,我看他就是心虛。」
「而且,我找府里的舊仆打聽過,最近這半個月夜裡有不人都聽到了嬰兒的夜啼聲。」
「何指揮使,您趕命人搜,千萬不能讓人給跑了!」顧瀟急切地說道。
旁邊的丫鬟婆子們不由面忐忑之。
們中的不人也聽說過夜裡有嬰啼聲的事,不由咽了咽口水:難道說,二爺說的都是真的?
水閣的空氣變得有些凝滯。(5,0);
「顧千戶,」何烈拱了拱手,語氣不咸不淡,「令堂弟實名舉報,錦衛也是公事公辦。」
意思是,錦衛也沒針對顧家的意思。
顧淵淡淡地掃了顧瀟一眼,俊逸的面龐平靜無波,爽快地對何烈道:「那就查吧。」
「不過,府里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守寡的叔母,還請指揮使不要驚憂到眷。」
何烈自然知道顧淵的親妹妹是何人,方正的臉上一下子添了幾分笑意,允諾道:「顧千戶放心,不會驚擾到貴府的二……位姑娘以及令叔母的。」
何烈原想說「二姑娘」的,話說了一半,生生地改了口。
「請便。」顧淵一派坦然地說道,又吩咐梧桐找幾個管事給錦衛領路。
何烈只隨意地揮了下手,隨行的十幾個錦衛就四散開來,訓練有素地分幾組開始在府搜查。
這件事頃刻間就傳遍了闔府,府中的家丁、丫鬟、婆子們皆是戰戰兢兢,心裡七上八下的。(5,0);
倘若錦衛真的搜到了庾氏餘孽,那可就是窩藏朝廷命犯,怕是顧家免不了一個抄家流放的悽慘下場,他們這些下人也沒什麼好下場。
府上下都被一層淡淡的影籠罩著。
水閣的一眾公子哥還是言笑晏晏。
路似半點也不見外,喧賓奪主地請何烈也坐了下來,又笑嘻嘻地吩咐人上茶,順便揶揄了顧淵一句:「阿淵,你沒金屋藏吧?」
顧淵:「……」
「哎,憑阿淵這種不解風的子?」樊北然嘆息地搖頭,與路似一唱一搭,「你忘了嗎?上回我們去聽小曲,人家花魁娘子好意給他斟酒,他差點沒把人胳膊給折了!」
「真是不懂憐香惜玉啊!」
幾個公子哥看熱鬧不嫌事大,你一句、我一語地調侃起顧淵來。
沒人請顧瀟坐下,他就只能這麼傻愣愣地站在,看著他們喝酒,看著他們閒聊,看著他們繼續投壺……心口的怒火一點點地往上竄著。(5,0);
不急,將來有顧淵哭的時候!顧瀟定了定神,在心中暗道,角又翹了翹。
樊北然又喝了一杯酒,看似在笑,其實目一直在注意顧瀟,心裡有些不安:顧瀟去錦衛舉報,若證實是誣告,那可是要杖責五十加充軍三年的。顧瀟既然敢這麼做,怕是布了什麼局,留有後手。
樊北然與路似等人不著痕跡地換了一個眼神。
錦衛這一搜查,就是足足半個多時辰,才三三兩兩地回來水閣復命。
「指揮使,」帶隊的倪總旗對著何烈抱拳稟道,「屬下等已經搜查了整個府邸,沒有發現可疑之人。」
半個時辰也不可能掘地三尺,錦衛也就是大致搜查了一遍,排查了一下顧府的人員,大上沒發現什麼問題。
那些丫鬟婆子們如釋重負。
何烈銳利危險的目看向了顧瀟,顧瀟被他看得咯噔一下,趕道:「等等!」
猜你喜歡
-
完結114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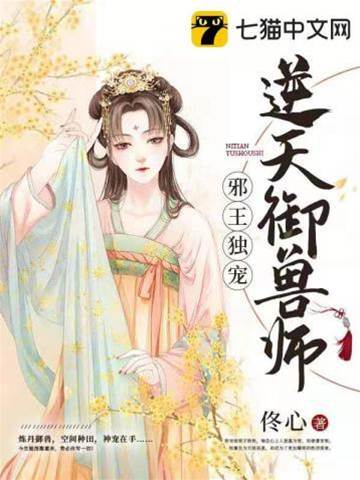
邪王獨寵逆天御獸師
前世她傾盡一切,輔佐心上人登基為帝,卻慘遭背叛,封印神魂。重生后她御獸煉丹,空間種田,一步步重回巔峰!惹她,收拾的你們哭爹叫娘,坑的你們傾家蕩產!只有那個男人,死纏爛打,甩都甩不掉。她說:“我貌丑脾氣壞,事多沒空談戀愛!”他笑:“本王有錢有…
215.2萬字8 21339 -
完結2714 章

凰妃九千歲
她搖身一變,成為了權傾天下,令人聞風喪膽的第一奸臣! 害她的、恨她的、背叛她的,一個都別想跑!
251萬字8 48872 -
完結800 章

凰臨天下
九界之中,實力為尊。她是神尊境的絕世強者,卻不料在大婚之日,被所嫁之人和堂妹聯手背叛,淪落為下界被家族遺棄的傻子二小姐。涅槃重生,再臨巔峰的過程中,一朝和天賦卓絕,暗藏神秘身份的帝國太子相遇。“據說太子殿下脾氣不好,敢冒犯他的人下場都淒慘無比。”數次甩了太子巴掌的她,默默摸了摸鼻子。“據說太子殿下極度厭惡女人,周身連隻母蚊子都不允許靠近。”那這個從第一次見麵,就對她死纏爛打的人是誰?“據說太子殿下有嚴重的潔癖,衣袍上連一粒灰塵都不能出現。”她大戰過後,一身血汙,他卻毫不猶豫擁她入懷,吻上了她的唇。
136.1萬字8 2445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