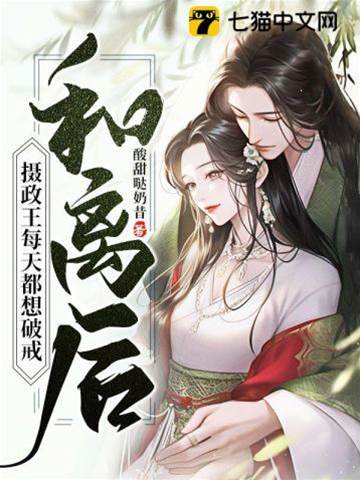《我見侯爺多病嬌》 第16章 全身上下隻有嘴是硬的
陳大夫嚇得睜大了雙眼,狗爬式地爬到那中年男人邊,猛地就是一腳:“你他媽說什麽鬼話!老子打死你,竟敢滿口胡話幫著慕雲歡欺瞞百姓,你真的該死啊!”
那中年男人一回過神來就被眾位百姓指指點點,這下陳大夫還沒有緣由地就狠狠給了他幾掌,他這怎麽能忍,立馬就梗著脖子要反抗,糙的掌用力扇在陳大夫的臉上,這聲音震天響!
陳大夫本來就被慕雲歡打得滿肚子怒火,瞬間就和那中年男人扭打在了起來。
慕雲歡瞧著他們一邊打一邊罵的模樣,看得高興並沒有打算攔。
狗咬狗,為什麽要阻止?
當然應該在旁邊當耍猴戲看個開心才對!
慕雲歡收斂了笑容,出幾點眼淚看向百姓,委屈控訴:“大家也看見了,昨天陳大夫嫌貧富不肯救他,我這人向來心又善良,就救了他。陳大夫嫌貧富,看人下菜碟,想必大家平時也沒他的白眼,我作為濟善堂的管事將他趕了出去,他就懷恨在心,竟然夥同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來汙蔑我,想要陷害我濟善堂的名聲。”
濟善堂除了陳大夫個別是嫌貧富以外,其餘的大夫給他們看病的診金都是盡量能便宜就便宜。百姓都是有目共睹的、
眾百姓一聽,隻覺得慕雲歡和這濟善堂實在是無辜,明明是清理門戶,卻被陷害,紛紛出聲替慕雲歡打抱不平。
伴著百姓們的謾罵,無數的蛋和爛菜葉都朝正在打架的陳大夫和中年男人上砸去。
瞬間兩個人上黃的蛋和爛菜葉,看著狼狽至極。
被百姓們這麽一罵一砸的,陳大夫和那男人才從憤怒中清醒了過來,裹著蛋慌忙逃走了。
Advertisement
陳大夫和中年男人一跑,百姓們沒了熱鬧可看,接著就散了。
慕雲歡想要把那木還給沈離夜:“謝了,燒火還給你。”
說著,就要轉進濟善堂。
臨風急忙扯住的袖,滿臉張地搖頭,想要讓看看自己侯爺。
慕雲歡看見臨風的神,雙手抱臂瞧了沈離夜一眼,問臨風:“他又怎麽了?”
臨風此時也是有苦難言,自家侯爺的臉已經黑了好一會了,那眼神像是要把人活地弄死一樣。
得,自從他家侯爺開竅想人之後,他都快猜不出侯爺在想什麽了。
真是令他頭禿。
沈離夜聽見慕雲歡的話,本就沉下來的臉,更是黑得像是化不開的濃墨一樣,周刺骨冰涼的戾氣和殺氣肆意織。
他都沒有和如此近距離地對視過!
那個狼心狗肺的東西憑什麽?
臨風抿了抿,試探著開口:“慕姑娘,有沒有可能,你說的燒火,是黑檀木做的,主子特意弄來給您的。”
慕雲歡頂著臨風的目眨了眨眼睛,低頭認真看了看,好家夥,還真是黑檀木。
了耳朵:“沒仔細看。”
黑檀木可是要比紫檀木都要貴。
嘖,不愧是天下第一莊莊主,就是有錢。
一燒火都犯得上用黑檀木做。
慕雲歡瞧沈離夜還黑著臉,臨風則是表示莫能助。
了眉心,看向他,嗓音好聽,輕聲哄他:“你去客棧就是為了拿這個,給我打人用啊?”
這阿七真是比上百個陳大夫加在一起都難纏!
Advertisement
不管怎麽說,目前他都是對好的,還有這燒火……
沈離夜冷白,眉間是掩不住的鬱,沒說話,儼然在和賭氣。
見他不說話,慕雲歡沒什麽耐,但對上他那雙眼眸,又是沒由來的心,放了語調:
“出去這麽久,冷不冷?”
好像是理虧。
沈離夜瞧著那雙清澈的眸,幹淨得沒有半分雜質,心中怒氣倏地就緩解了幾分,沉聲說:
“冷。”
慕雲歡迎上他的眸,嫣紅的微勾:
“哪裏冷?”
聞言,沈離夜瞧見明的笑容,心才慢慢好了起來,他輕咳了咳,隨後朝出手:
“手冷。”
說完,沈離夜自己都怔愣了一秒,像是沒想到自己在麵前會用這種語氣,這麽自然的說出這種話。x33xs.
慕雲歡聽出他的意圖,笑著微挑了挑眉,索繼續縱容他:“暖暖就不冷了。”
下一秒,的荑就附上沈離夜冰冷的大掌。
濟善堂裏,明豔絕的彎腰站在冰冷鬱的男人麵前,的雙手裹著他的大掌來回地著,時不時低頭朝兩人張的手哈氣。
五極好,皮白皙,紅飽滿水潤,幫他取暖時,清澈眼眸中都泛著認真地微,一顰一笑間像是要勾人魂魄去。
沈離夜看著麵前的,像是沒有想到會這樣幫他取暖,手掌上溫熱的像是電流一樣,瞬間傳遍全鑽進他的心裏。
鼻尖縈繞著上獨有的冷香,沈離夜失了神。
“還冷不冷?”慕雲歡正抬頭,就撞進那雙微涼幽深的眼眸中,有太多看不懂的緒。
Advertisement
沈離夜這才回神,低哼了一聲:“還是冷。”
該死,又看看得失了神。
他什麽時候竟變得這樣矯?
慕雲歡此時心不錯,選擇繼續縱容:“多暖暖。”
“還是冷,暖不熱…”
“知道了…”
慕雲歡縱容地繼續給他暖手。
臨風簡直沒眼睛看,以前在戰場打仗的時候,什麽艱險苦寒的地方沒呆過?
那些地方一呆就是好幾個月,作為三軍表率,自家侯爺向來都是最能吃苦,什麽大風大浪沒見過。
眼前這個腹黑裝弱的人肯定不是他家侯爺!!!
過了好一會兒,慕雲歡才放開了沈離夜,嗓音微冷:
“阿七,你這脾氣得收收。”
每次發脾氣鬧得莫名其妙的,難纏得很,跟個巨嬰一樣。
慕雲歡對他的態度冷漠了些,這話說的疏離,和剛剛給他暖手的人判若兩人,像是隻是一時興起,好脾氣地哄了他兩句一樣。
沈離夜眸中又冷了些,心中莫名煩躁,說話也強勢冷起來:
“日後你不哄就是了!”
語氣中全是不悅。
就算知道是在用北疆,但一想到和那男人距離那麽近,他心中就是止不住的暴躁煩悶!
還有現在疏離冷漠的態度,沈離夜看著就覺得紮眼又紮心。
竟敢說他脾氣大?!
臨風瞧著這兩個人,怔愣住了,剛才不是你儂我儂,好好的嗎?
怎麽現在一言不合就吵起來了?
不是,他是從哪裏沒跟上的?
慕雲歡聽見沈離夜的話,突然就對他這樣來了興趣,也沒說話,手了他紅得快要滴的耳垂。
Advertisement
耳垂一片麻,沈離夜心底煩悶暴躁,卻毫都控製不住自己耳廓發紅發熱。
看著的那雙桃花眼泛著凜冽的寒氣,像是充斥著殺氣的無邊地獄,可他耳朵又紅得不行,慕雲歡勾笑著問:
“怎麽,全上下隻有是的?”
不想讓哄,他耳朵紅個什麽勁兒?
真不希哄,那他鬧什麽?
被一眼看穿,一句話點破心事,沈離夜眼眸慍怒,他猛地站起,雙手撐在桌麵上,將困在其中,他怒道:
“日後不許與別的男子那般親近!”
慕雲歡材高挑,在子中已經算是高的了,但還是隻到沈離夜的下。
這看著,就像沈離夜輕輕鬆鬆地將整個人圈在懷裏。
撲麵而來的男氣息極侵略,勾起慕雲歡心中莫名的緒,勾笑得開心:
“看不出來,你這病秧子還真的有兩副麵孔。”
可不是嗎?
沈離夜此時周殺伐氣息強勢又凜冽,像是從山海裏爬出來的活閻王,哪裏還有半點平時在麵前裝得病脆弱的病秧子模樣?
他睨著,又怒又地說不出半句話。
明明他如此桀驁強勢地說出那句話,但耳垂上傳來的溫,又讓他被迫直麵那因為靠近而生出的愉悅。
慕雲歡的耐心被耗完,渾寒氣半點都不輸於沈離夜,紅微勾:“憑什麽聽你的?”
沈離夜咬牙,頓了片刻最後隻留下一句:
“我說不許,就、不、許!”
說完,沈離夜拂袖而去。
臨風急忙向慕雲歡解釋道:“慕姑娘,你千萬別生氣,我家主子…他也不是故意吼您的,他脾氣一上來就控製不住,你消消氣,消消氣哈!”
說完,臨風就急忙追進了堂。
慕雲歡雙手抱臂站在原地,指尖還殘留著他耳垂微熱的溫度。
病秧子脾氣還大,他似乎隻有耳朵紅得充的時候才有點溫度。
了眉心,也就懶得管沈離夜了,現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沒時間陪他過家家。
今天這事兒,陳大夫肯定是人指使的,他要是沒人撐腰,不可能明知道是聖醫和濟善堂主人的時候,輕易向發難。
最大的可能就是慕思思。
如果那中年男人和陳大夫是一夥人指使的話,陳大夫直接帶著那個中年男人來鬧事,肯定會把男人救醒,到時候他們倆咬死是就行了,本沒必要再從犄角旮旯裏找個騙子冒充男人的媳婦兒。
那中年男人雖然忘恩負義,反過來栽贓他的救命恩人,但應該和陳大夫不是一夥人。
那他又是誰指使,誰又會想要害?
眼前,先把陳大夫背後的人解決了再說。
。您提供大神朝辭的我見侯爺多病
猜你喜歡
-
完結620 章
秀色滿園
成爲地位卑下的掃地丫鬟,錦繡冷靜的接受了現實。她努力學習大宅門的生存技能,從衆多丫鬟中脫穎而出,一步步的升爲一等丫鬟。丫鬟間的明爭暗鬥,小姐們之間的勾心鬥角,少爺們的別有用意,老爺太太的處心積慮,錦繡左右逢源,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到了適婚年齡,各種難題紛至沓來。錦繡面臨兩難抉擇……尊嚴和愛情,到底哪個更重要?---------------
157.9萬字8 43123 -
連載886 章

穿越女尊農門妻主不好當
她本是現代女神醫,一手金針起死人肉白骨,卻意外穿越到一個女尊王朝。一貧如洗的家,還有如仇人一般夫郎們,水玲瓏表麵笑嘻嘻,心裡。沒辦法,隻能賺錢養家,順便護夫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82.4萬字8 21764 -
完結2595 章

神醫毒妃腹黑寶寶
穿越當晚,新婚洞房。 雲綰寧被墨曄那狗男人凌虐的死去活來,后被拋之後院,禁足整整四年! 本以為,這四年她過的很艱難。 肯定變成了個又老又丑的黃臉婆! 但看著她身子飽滿勾人、肌膚雪白、揮金如土,身邊還多了個跟他一模一樣的肉圓子……墨曄雙眼一熱,「你哪來的錢! 哪來的娃?」 肉圓子瞪他:「離我娘親遠一點」 當年之事徹查后,墨曄一臉真誠:「媳婦,我錯了! 兒子,爹爹錯了」
470.9萬字8.18 60927 -
完結199 章

癡傻王妃太難追
在丞相府這讓眼里,她就是那個最大污點,丞相府嫡女未婚生下的粱羽寧,從小受盡侮辱,終死在了丞相府,一朝穿越,心理醫生重生,她看盡丞相府的那點把戲,讓她們自相殘殺后笑著退場,大仇得到! 可在小小的丞相府能退場,在感情的漩渦越來越深之時,她能否安然離開? 一場大火,翩翩佳公子,變成了殘忍嗜血的戰神,接連死了八位王妃,當真是自殺,還是人為?
45萬字8 10423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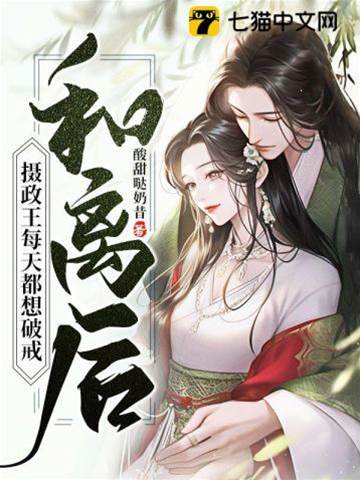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4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