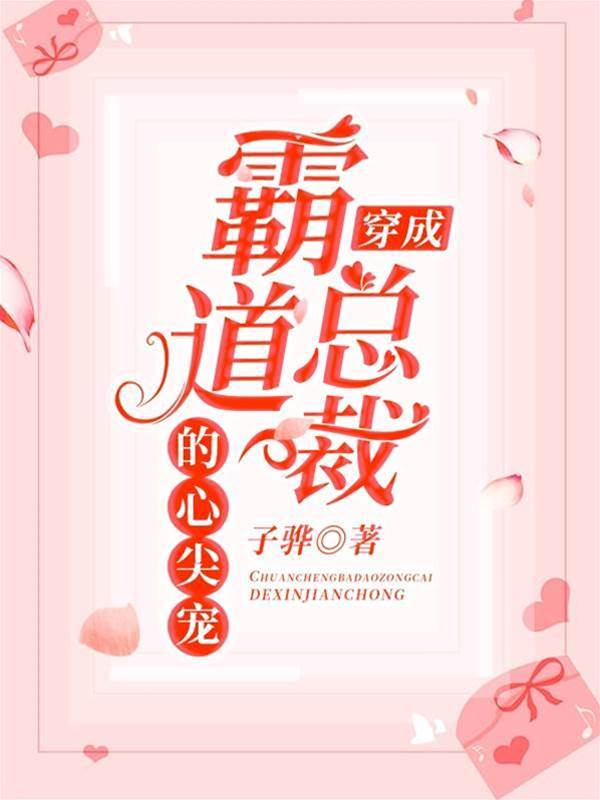《御前美人》 第45頁
只是沒想到這天會來得這麼快。
就為了姜央?
想不到這冷自私的白眼狼,還有的一面。頭先為了姜央,不顧勝算提前起事;現在又為了姜央,這麼早就和撕破臉。
太后不屑一嗤。
三年前就勸過先帝,那小子就是個養不的白眼狼,可先帝還是沒忍心取他命,只罰他在西苑思過,最後到底是養虎為患。
先帝自去歲起,每況日下。煊兒那場婚禮,原是想辦來給他沖喜的。誰想喜沒沖,還釀了大禍!兒子沒了,先帝盛怒之下,也沒了。
短短一夜,從風無限的貴妃,淪落為階下囚,九死一生討回個太后的尊榮,也不過是從天牢搬到慈寧宮這座更為華麗的囚籠而已。
而這一切,都是拜他所賜!
腔子裡滾著滔天怒火,太后反倒冷靜下來,從容俯撿起地上的剪子,繼續修剪花枝,「哭什麼?哀家這不是還沒被他釘在宮門上?既然他打算撕破臉,咱們也不怕跟他撞個魚死網破。他登基後是收服了不人,咱們不也沒閒著?真鬧起來,誰死誰活還不一定。」
Advertisement
尋到一枝格外突兀的花枝,撐開剪子抵在枝節上,角溢出一冷笑,「就從那個姜家小丫頭手。他不是對人家癡心不改嗎?哀家倒要看看,他這顆心究竟能癡到什麼地步!」
咔嚓
花枝落地,昨夜未散的珠還在花瓣尖搖晃,未及墜落,就被一隻繡鞋狠狠碾了土。
養心殿,順堂。
姜央正和雲岫一塊坐在窗下打絡子。
不知何忽然捲來一陣風,冷颼颼的,伴著一惡寒,不自覺「噝」聲哆嗦了下,袖子遮蓋下的兩隻藕臂一顆顆冒起細細的栗。
「姑娘,怎的了?」雲岫放下線,關心道。
「沒事。」姜央搖頭,「大約是裳穿了,凍著了。」邊說邊仰頭瞧窗外的天。
驚蟄過後,帝京頭頂的天就跟被捅了個窟窿似的,雨水總沒個消停,到今日才將將放晴。穿過雲翳隙,斜斜打在繡鞋尖的南珠上,暖暖的,恍惚有種初夏的味道。
這倒更顯得剛才拿寒意奇怪了。
姜央癟癟,沒多想,低頭繼續整理手裡的線,餘里闖進來一道急切的影,又是小祿。
Advertisement
姜央不由嘆氣。
雲岫卻是捂笑個沒完。
自打上回姑娘撤了陛下的晚膳,這養心殿的一日三餐就全歸了姑娘管。而這一管起來,就沒了邊,不僅要琢磨陛下吃什麼,還要琢磨怎麼讓他吃下去。
「他又不肯吃飯了?」小祿才剛跑到門口,沒等張,姜央就先發問。
小祿訕笑著撓頭。
其實陛下這點心思,誰看不明白。同樣都是姜姑娘做的飯菜,人家在,他就老實吃;人家不在,他便是死也不肯一筷,非要他們把人給請到他眼前,訓他幾句,他才肯好好吃飯。
都是弱冠之年的人了,還跟個孩子一樣,從前看他當劊子手了,哪裡見過他這樣?真真人大開眼界!
可無奈歸無奈,差事還是得辦,不然沒法代。躬下子拱手一揖,小祿枯著臉道:「姜姑娘聰慧過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就隨奴才走一趟吧。」
這都是什麼詞?拿當菩薩拜了嗎?姜央太,心底對某人這一無恥行徑甚為鄙夷,可到底沒辦法,只能起抻抻衫,隨小祿一道出門。
東梢間裡還是老樣子。
Advertisement
衛燼窩在南窗下讀書,一鬆散的藏青燕居服。天過鏤空的萬字紋照進來,把他照得周鍍金,沒了猙獰的團龍作飾,倒顯出幾分清雋。
午膳就擺在他面前的炕桌上,照例是一碗暖胃的大棗蓮子粥,並幾碟爽口小菜,都是姜央親自掌勺,香味俱全。可擺上來都有一炷香的工夫了,竟是一筷未。
「阿狽這是打算死自己嗎?」姜央邁步進門,直截了當道。
小祿在跟前引路,險些崴到腳。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喊「阿狽」了,前侍奉的人早就習慣。可冷不丁聽見,小祿還是會忍不住兩打擺。敢這樣稱呼天子,古往今來第一人吧!
衛燼也不惱,下半張臉書本遮擋,打進門起就已經綻開花,偏生上半張臉還不聲,不咸不淡地斜了眼炕桌上的粥,冷哼:「天天喝粥,連點葷腥都沒有,朕的舌頭都木了。」
「那還不是阿狽自己作的?倘若之前喝點酒,這會子何至於只能吃這些勞什子?還想吃,哼。我這幾日嗓子疼,還想吃糖呢,不也一樣沒得吃?」
Advertisement
姜央提坐在他對面,拿湯匙舀一勺粥輕輕地吹,遞到他邊,「啊——」
跟餵孩子一樣。
衛燼嗤之以鼻,卻是老實張開,吃完一口,便亮著眼睛期待餵下一口。
小姑娘生得好看,做事又溫細緻。清風鬢間的發,側頭在肩上輕輕蹭了下,晨里拉長的影斜鋪到步步錦上,襯著邊上的蘭花架,那畫面拓下來,足可欣賞一輩子。
再看,還能品出幾分尋常夫妻的味道。
強撐了這麼久,這一刻,他眼梢還是浮起了一點仰月的笑紋,偏頭瞧窗外。飛鳥橫渡,雲翳如浪在長空流湧起伏,約夾雜幾聲悶雷。
又要下雨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