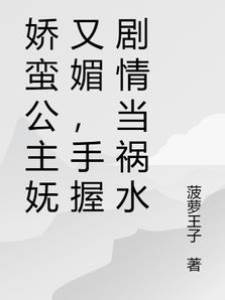《十二年,故人戲》 14.第十三章 明月共潮生(4)
;
房間裡能有一星半點聲響就好了,可沒有。走廊也是安靜的。
船上的地毯可以吞沒腳步聲,哪怕有人跑過去,也絕不會驚擾到這裡的兩個人。
和他目相對。
「跟著……」輕聲重複,「是如何跟?」 查看最新章節,請訪問𝕊𝕋𝕆𝟝𝟝.ℂ𝕆𝕄
「你以為是如何?」他反倒是笑。
沈奚怕自己誤會了,可兩人的手膩到一這麼久,總能說明什麼。
「三哥在家中可有……妾?」
傅侗文笑,搖頭。
「這幾年,你家裡沒為你定過別的親嗎?」
他又搖頭。
本要說談一場新式的,像慶項那樣,給孩子自由,又不能明著說,以傅家老三的名聲來一句「互不束縛」,九九會被人當**一度,或幾度。;
這浮名平日了,今日就會被反噬,也怪不得別人。
他見不出聲,才問:「可還有要問的?」
這回,換搖頭了。
「三哥這個人——」他停頓在那裡,又笑說,「不算很好,也不會太壞。你姑且試一試。」
金玉華筵,他走過上千遭,浮花浪蕊,更是遇到不計其數。可有這麼一日,他傅侗文也能放低姿態到這個地步,對一個孩子。
沈奚眼睛不敢著他,看看地板,又看棉被上頭,有自己落下的一頭髮。想著,一會兒要將它撿起來,繞圈,捻個結。
想著,想著,輕輕地「嗯」了聲,嚨里發了聲,耳也燒了起來。
這是應了。
糊裡糊塗地,又和傅侗文談數句,約莫是睡了,好,我將這燈關上了,好。
燈被撳滅。;
Advertisement
傅侗文將放到棉被裡,這才又從床尾走回去,到他那一頭,上了床。這床一,的人也跟著一。萬幸他不再說話。
這就是要了。
這麼大的一樁事,兩個人卻對話寥寥,甚至沒有一句是直白的。可又想,現在是新時代了,談並不算是什麼大事。又不是前朝。
人慌牢牢的,揣著不安。
結果做了夢,也夢到的都是他浴在燈下的臉和雙眼,像夜晚的火車,那輛送京的車。在門邊,四周都是陌生的旅人,下車時是在正門。
簡陋的木牌子上寫著幾個字母,當時並不認識。
後來來了紐約,再回想,依稀能拼出來那是PEKING。
車站人流集,是跟著人出來,始終跟在給帶路的陌生人後,木柵欄外,圍滿了等著拉客的馬車和騾車,坐得是人力車。那天,車站外只有兩輛人力車,占用了一輛。;
斷斷續續的,拼湊出那年的逃難。
天亮時,傅侗文拉開窗簾,去了洗手間,沒多會出來。
沈奚也溜下床,不甚清醒地洗漱。乾淨臉後,將巾捲起來,準備放到水池旁。喜歡這樣,這樣會讓覺得乾淨,儘管每日都有人來換烘乾的巾。
巾卷到半途,他先離開了房間。
新的一天,和過往無甚差別。
譚醫生自從昨晚被撞破後,反倒大方了,終於將往半月的友也帶到私人甲板。有了相親的之間,舉手投足儘是親。至多保持了半小時的距離,譚慶項就將朋友摟在前,兩人一道坐在躺椅上,共新送來的水果。
沈奚和傅侗文卻比往常還要正經,看譚慶項拿來的書,他翻看新送來的報紙。
Advertisement
至多是,想拿茶杯時,他會順道為往前推一推。
心猿意馬,他氣定神閒。;
真是高下立見。
十一點,管家遞了張名片來,說是今日上船的新客人里,也有前往上海的中國人。聽說了這裡有救過人的外科醫生,才遞了名片上來。
傅侗文接過,上頭寫著上海仁濟的名頭。
畢竟是來拜訪沈奚的,他還是將名片給了:「你來看吧。」
「應該沒問題吧?」沈奚頭回被人拜訪,想見,又怕惹麻煩。
「中途上來的,問題不大。」譚慶項給吃了定心丸。
「那就見吧。」開心起來。
見到同行,總比琢磨該如何談要輕鬆得多。
來的是兩個人。
一個金髮碧眼,一個黑髮華人。
那個華人是個三十歲上下的高個子男人,戴著一副墨鏡來,也是留學生的做派。他見到屋裡的幾個人,將墨鏡摘下來,熱絡地和他們做著介紹。他錢源,是仁濟醫院的醫生,旁邊那位是他的同學兼同事。沈奚早被譚慶項科普過,北京協和醫學堂和上海仁濟在國的地位,對這位前輩很是尊重。;
長途旅程遇到同胞,又是同行,譚慶項也很快參與到談話中。
「這個船醫還說,他從未見過中國的西洋醫生,」沈奚笑,「先生你一來,又多了一位。」
「盲人象,他在海上十年,又能見到幾個中國人?」那人含笑,「西方人的固有想法,總會改變的。」
是啊,總會變的。沈奚不由向傅侗文。
傅侗文禮貌地在一旁,對輕舉了舉茶杯,示意他在聽。
這微妙的一個小作,只有看到了。
「沈小姐,為何會選擇讀醫學?」錢源閒聊著。
Advertisement
「因為……我是廣東人,接西醫比較早。」
「這樣,也對,」錢源笑,「國的西醫是在那邊發展起來的,澳門也是。你小時候就會去西醫診所看病了?」
沈奚點點頭。
;
「沈小姐,這樣吧。我先說來意,我這位同事在上船後船長的邀請,去見過了你的病人。在他看來,你完的很出,所以他想面見你。問問你,回國是如何打算的,是否願意去仁濟。」
那個英國人也在說,「沈小姐,國在骨科這裡還沒有專門的診室,但仁濟已經有了這方面很多的經驗,還有,我們仁濟醫院早已經領先了國的西醫醫院。尤其在外科上。」
「現在骨科還沒發展起來,你可以考慮跟著我這位同事繼續深造,我們仁濟開創了外科消毒法的應用,這在中國是最早的。」
沈奚很是意外:「謝謝你們,可我……」看向譚慶項,不太確定,「我是個剛畢業的學生,你們的邀請讓我很惶恐。」
兩人相視而笑。
錢源解釋:「歸國的醫學生太了,外科上更。我們需要更年輕的學生。」
沈奚點點頭,大概了解了。;
「這船是到上海,請問你們的目的地是?」
沈奚又去看傅侗文:「北京。」
「哦,是北京,」錢源蹙眉,憾地問,「沈小姐家在北京?」
沈奚猶豫。
「是我太太。」傅侗文替答。
「這樣。」錢源更是憾了。
原本他會憾,可能這位難得歸國的留學生,會要去協和,現在看來,應該只是讀書消遣。看這私人甲板就能猜到,這位傅先生家大業大,並不需要妻子拋頭面去工作。
Advertisement
不過兩人還是對沈奚很是欣賞,又聊了許久,聽譚慶項說到翻譯醫書,馬上拿出來了珍藏本,送給他們兩人:「並不是早年的孤本,是手抄本。權當留念。」
是仁濟早年翻譯出版的《中文醫學詞典》、《西醫略論》和《婦嬰新說》。譚慶項在兩人在時還沒表,等人告辭了,馬上拿起那本詞典:「這可是咸年間的書,名副其實的第一套西醫翻譯書。」譚慶項興致地給沈奚普及。;
這對他在心臟學上的翻譯,極有幫助。
譚慶項剛說完,那個錢源又出現,抱歉地摘帽點頭,笑著對沈奚說:「方才忘了說,我剛給我們的院長寫了申請信,也許馬上就能買一架X機。如果你以後真的從事這一行,如果你需要,可以給我來信,我會安排你的病人來仁濟優先使用。」
「謝謝你。」沈奚被他的這種醫者心打,對他點頭致謝。
錢源笑著,將的手執起,低頭一吻:「很榮幸。」
他的作很自然,沈奚雖被嚇到,卻沒好意思阻止,只是在他到自己指背的一瞬,就算是了禮,急匆匆地收回手。
「傅先生,不會介意吧?」錢源反倒去看傅侗文。
傅侗文把玩著茶杯,微笑著回:「後不為例。」
錢源沒將他的話當回事:「是我唐突了,再次告辭,各位。」
訪客離開。;
譚慶項也不去管他們,連自己朋友也丟在一旁,只將心思放在了書上。
甲板安靜著。
傅侗文將空茶杯擱在了桌上,兩手斜在西口袋裡,離開這裡。
沈奚見他走了,更待不住,半分鐘後匆匆丟下句話:「你慢慢看。」人也追著出去了,途中不見人,問了管家,才曉得他去了頭等艙的圖書館。這船上統共兩個圖書館,頭等艙只對自己艙的人,二等艙那個倒是對一二三開放。
本就只對一個艙開放,又因為是有書單的,需要什麼管家送去就好,完全不必親自去。
所以,平時不見什麼人去。
中國人喜歡的書架,是能的,簡單的是木架,厚重的書。西方反倒更熱衷將書架打造得厚重,書倒像是塞在裡邊的一排排的裝飾,去陪襯頂到天花板的書架。
剛上大學見到圖書館,腦海里第一個蹦出來的念頭是:這要倒下來,可是滅頂之災,誰都逃不掉的……自那後,每每走,就會有抑。;
在這裡也是。四下無人,更沉悶。
沈奚提著心,左顧右盼。
快走到底才見到他的人,沒在看書,手裡也沒拿著,反倒將西裝隨便折了兩折,塞到半空著的書架上。他將手臂撐在書架上,頭低著,去看腳下的地板。
「你不舒服嗎?」沈奚到他邊去。
傅侗文偏過頭來。那雙眼沒有,甚至一開始都沒焦距,慢慢地,他人的思維匯聚到一,眼睛也終於開始有了四周圍景的影子,包括的樣子。
「我很好。」他說。
是很不好。沈奚想,背靠在書架上,挨著他的手:「你不高興?」
傅侗文搖頭。
「到這裡來。」他抬高右臂。
沈奚欠,鑽過去,他又將手臂一左一右撐在了兩邊。
在這麼大的圖書館,他為畫了個圈,小小的,方寸之間。輕輕屏息,怕自己的呼吸都落到他臉上。;
「方才,想到侗汌。」
是這樣的原因,想。
「仁濟過去也會幫片上癮的人,他常提起。」
「四爺他……」沈奚沉默一會,轉去問,「你看醫學雜誌,是因為想起四爺?」
他微笑,在默認。
不會安人,但想嘗試:「你去紐約,我們再見到那日,你讓我你什麼?」
「三哥。」
「同樣是你一聲三哥,我也會做到很好。」仿佛在宣誓。
他安靜著,笑著。
「替我解開領帶,好不好?」他說。
沈奚沒想他的話,不舒服,那便出去好了,這裡空氣是不比外頭。糊塗著,還是把領帶扣給他鬆開了,又去扭開紐扣。到這個地步上……
領帶掛在那裡,領子也松垮了。;
有人在玉盤裡放了明珠,左右晃著,珠子從這頭向那頭,又從那頭溜了回來。的心就是那顆珠子,來去,抓不到邊沿,停不下。
多琵琶夜上樓,香薰鴛被白團扇,他都是坐著看戲的那個,在這一,卻是登了臺。卻真像那戲詞裡說的,引「……繞過這芍藥欄前,靠著湖山石邊,和你把領口兒松,帶寬……則待你忍耐溫存一晌眠……」
「這樣,很不樣子。」他笑著說,最後的字音低了,突然低頭,去含上的,下。
驚雷炸開,眼前電火石。
避而不及,無措地將他襯衫前襟,擰出了厚厚一層褶子:「三哥……」只是下被他,含著,咬著,子就了半邊。
可一張了口,他的舌尖就進去了。
這般風流浮浪,像有雙手去點了一捻香,引人去寬解帶橫臥……
他的手,擱在書架上。他的,挨在的上。他的人在和親吻著,齒香舌。這就是親吻嗎?漉,迷,水盈盈,香艷四……還是他的本就和旁人不同。;
西裝從書架落,到地板上。沈奚不住,人也下去,被他一隻手握著腰,將子骨提上來,連帶著子也拉到了膝蓋上,將手埋在下,的上。
沒來由地一陣眩暈,地山搖,一層層書架倒下來,倒在眼前。
睜眼去瞧,一切如舊。
不過是他吻又深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56 章

穿成侯門寡婦後,誤惹奸臣逃不掉
【雙c 傳統古言】沈窈穿越了,穿成了丈夫剛去世的侯門新鮮小寡婦。丈夫是侯府二郎,身體不好,卻又花心好女色,家裏養著妾侍通房,外麵養著外室花娘。縱欲過度,死在了女人身上……了解了前因後果的沈窈,隻想著等孝期過了後,她求得一紙放妻書,離開侯府。男人都死了,她可不會愚蠢的帶著豐厚的嫁妝,替別人養娃。 ***謝臨淵剛回侯府,便瞧見那身穿孝服擋不住渾身俏麗的小娘子,麵上不熟。但他知道,那是他二弟剛娶過門的妻子。“弟妹,節哀……。”瞧見謝臨淵來,沈窈拿著帕子哭的越發傷心。午夜時分,倩影恍惚,讓人差點失了分寸。 ***一年後,沈窈想著終於可以解放了,她正要去找大伯哥替弟給她放妻書。沒想到的是,她那常年臥病在床的大嫂又去世了。沈窈帶著二房的人去吊唁,看著那身穿孝服的大伯哥。“大伯哥,節哀……。”謝臨淵抬眸看向沈窈,啞聲說道:“放你離開之事,往後延延……。”“不著急。”沈窈沒想到,她一句不著急, 非但沒走成,還被安排管起侯府內務來。後來更是直接將自己也管到了謝老大的房內。大伯哥跟弟妹,這關係不太正經。她想跑。謝臨淵看著沈窈,嗓音沙啞:這輩子別想逃,你肚子裏出的孩子,隻能是我的。
31.5萬字8 9189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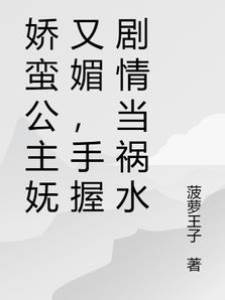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5722 -
完結497 章

禁斷關係
【混不吝大灰狼VS偶爾急了會咬人的小兔子】1V1丨雙潔。初心喜歡謝冕很多年,如願以償和他談婚論嫁,不想他的初戀突然回國,一時腦熱,她在閨蜜的慫恿下一不做二不休。結果做錯了人,招惹上離經叛道的竹馬。初心試圖撥亂反正,“謝承祀,我們八字不合。”“八字不合?”男人漆黑眉眼上,覆滿肆意張狂的邪,“在我這兒,我說合它就得合。”“......”-後來,眾人皆知不信佛的謝承祀,跪著上了一百八十八級臺階,在寺中誦經三天三夜,為初心祈求餘生平安喜樂。
46.7萬字8.18 28723 -
完結118 章

乖,別怕!病嬌反派致命撩寵女配
病嬌瘋批?甜寵?偏執?反派?女配穿書?雙潔?救贖?校園【不黑原女主】係統存在感低 【主角團全員覺醒,男主純情病嬌戀愛腦,青春熱血小甜餅】 溫柔痞帥病嬌忠犬美強慘X古靈精怪沙雕社牛少女 誰說搞笑女沒有愛情? 甜甜的戀愛這不就來了嗎! 洛冉冉穿進一本瑪麗蘇小說裏成了惡毒女配,還要完成係統崩壞前交代的【拯救虐文】任務,把BE扭轉成HE。 書裏的瘋批大反派少年黎塵,是手持佛珠卻滿手鮮血的小少爺。 洛冉冉努力完成任務,可過程中她居然被這個反派纏上了,大魔頭要親親要抱抱還化身撒嬌精,接吻怪…… 任務結束洛冉冉離開,二次穿書,她被少年抵在牆角,他笑的妖孽,捧起洛冉冉的臉說:“乖,別怕,不聽話要受到懲罰哦。” 我從來不信佛,不信神,我隻是你的信徒。——黎塵 — 黎塵:“冉冉,那你能不能喜歡我一下啊?” 洛冉冉:好吧,誰能拒絕一個又撩又可愛的大帥比呢? 黎塵:“冉冉,你親了我就得負責。” 洛冉冉:“……” 黎塵:“冉冉,鮮血染紅的玫瑰才好看對嗎?” 洛冉冉:“大哥別激動哈,咱們有話好好說!” 【甜寵救贖,曖昧拉扯,明目張膽偏愛寵溺。】 女主直球 男主戀愛腦 作者女主親媽
29.5萬字8.33 4470 -
完結180 章

備忘錄被同步到他手機上后
1、 家里那位塑料老公,是黎穗平生見過最毒舌的人。 搭訕男約她出去逛逛時—— 周景淮:“抱歉,她遛過狗了。” 母親催生時—— 周景淮:“結扎了。” 母親:“為什麼?” 周景淮:“限時八折,這種便宜錯過就沒了。” 她替小狗打抱不
26.6萬字8.18 6426 -
完結284 章

可愛多和不好惹
整個寧中的人都知道,又拽又狂的學霸大佬江知宴是個不好惹的風云人物,但沒想到三班的小姑娘初芷特勇,專門處處和大佬對著干。 某天坊間傳聞說大佬已經被小姑娘馴服了,不僅天天送她回家,還親自給她背書包呢! 對此,當事人江知宴冷哼一聲,“我哪是送她回家,我是回自己家。 眾人,“哦~原來是初芷借住在大佬家。” 江知宴,“我給她背書包是因為里面裝著我的籃球服。” 眾人,“哦~原來大佬在背自己的籃球服。“ 誰料想,某天不知情人士放出狠話要替受虐待的大佬報仇,結果還未出手就被大佬反擊殺。 江知宴眉眼輕挑,有些煩躁的撥了下自己額前的碎劉海,抬腳就踹人,“你放學堵她不讓回家,老子晚上給誰補數學?!”
51.8萬字8 29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