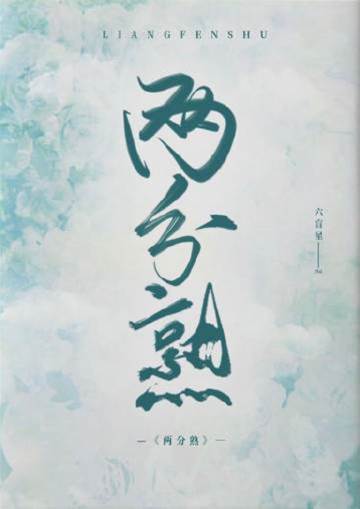《圓橙》 第195頁
與平常不同,這次他抱的不。
不過一個舒服亦溫的姿勢,近似于依偎,說不清道不明的溫繾綣,下輕輕抵在頸邊。
“你呀……”
失笑間,還是手回抱。
起初倒真只覺得好笑,覺得這太不符合蔣那張揚又霸道的格,活似給他轉了個,暴君變作小郎。
可笑聲在口輕飄飄晃過去一圈,卻連自己也說不明白為什麼,好笑變作無端的心疼,手指輕過他纏滿繃帶的背后。
“全世界,我當然最關心你。”
輕輕說,甚至不需要他問:“有什麼好特別驚訝的呀?上次在香港,我不就說了嗎,我們之間,和其它所有人都不一樣。”
“我知道。”
“那你還這樣,”打趣,“你該不會是知道我有點外貌協會,故意裝西子捧心吧?”
“……”
笑,故作一本正經:“不過老天爺就是偏你——你看你做這種表也好看,氣死人了。”
“那當然。”
“……蔣,你真的好不怕。”
Advertisement
誰能想到,看起來最不可一世,永遠萬事萬盡在囊中的蔣,其實卻是個最沒安全的小屁孩呢?
舒沅有些憋不住笑。
可又回頭想想自己高中時代,甚至是整個青蔥時里,蔣許多次心、猶如昂首闊步向前,卻不忘背手向來的倔強,曾責怪過,也對自己怒其不爭,可不知為何,或許是連自己也已經長大許多,現在再想起,自以為百煉鋼般堅心臟,卻忽而一灘春江溫水。
會就彼此為更好的自己嗎?
從前不知道,但現在,或許已經有了答案。
輕輕拍了拍他后腦勺。
沒頭沒尾的,忽而拋出一句:
“那,等你頭發長長了,更帥了,我們去結婚吧,蔣。”
話音剛落。
蔣顯然一愣。
整個瞬間僵,下意識發出個疑音節:“哈?”
“我說我們去結婚,不對,復婚。”
舒沅只得耐心補充:“主要是,不拿了那本復婚證,我怕你老哭——到底你是生我是生啊?”
Advertisement
哭?
他終于回過味來,開始死鴨子:“我沒哭!”
男子漢大丈夫,那能哭嗎,那的淚水,……等等,結婚?
重點似乎歪了。
舒沅“哦”了一聲。
“你沒哭啊?那可能是我看錯了。要不然先別結了?讓我再瀟灑兩年——”
“……”
室忽而安靜了五秒。
一頓過后。
仿佛突然找到了久違的樂子,被他驟然張到收手臂、又一時啞然到不知從何反駁的態逗笑,捂住肚子趴在他肩膀上,忍不住大笑出聲。
蔣被笑得耳都泛紅。
也任笑。
不知有多復雜且不可外說的心理活波濤洶涌,總之到最后,到底不過出一句別別扭扭的:“結吧,”他低聲說,“阿沅,我會對你很好很好。”
“有多好?”
“……至,就……別人的滿分只有‘十分’,我、我會努力給你‘一百分’。”
照抄標準答案的某人如是說。
似乎唯恐不答應,又側頭親親的臉頰,宛若孩提時向心的小姑娘示好,一子小心翼翼的提醒和親昵——當然,他那時候只知道把小姑娘推到地上弄哭、對主示好的小姑娘惡聲惡氣,被蔣母提著耳朵教訓也學不乖,這還實屬初學第一次。
Advertisement
還好,即便他總對全世界輕慢相待,他的“小姑娘”,依舊在很久很久之后來到,一切都不遲。
“打完司,就回去結婚。”
他恍如通了七竅,掰手指般一一細數:
“我們辦婚禮,買十件、不,二十件婚紗任你挑,昭告世界,放熱氣球,把沿江所有LED打上我們的名字,開流水宴,開三天三夜也沒關系,把所有老老小小的親戚,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人都請來——”
噫!
舒沅想象了一下那局面,的確揮金如土,氣派豪闊,但,這就是直男的示方式嗎?
滿臉黑線,不由吐槽了句:“老公,真的好土。”
“……”
“但,也蠻可就是了。”
笑:“覺你會很幸福的樣子。”
而自己又何嘗不是?
甚至不是因為婚禮有多大,想象中的婚紗有多漂亮,只是因為,他原來不曾說過,卻早早在心里無數次描繪了婚禮的樣子。
試問哪個孩,沒有與心的人共度余生的夢想。只是曾經以為,自己的夢想之一,永遠不可能再實現。
Advertisement
卻好在。
這一路風雨相隨,朝暮同往,蔣,他依然還似當年模樣,從未改變。
*
四日后,舒沅等人啟程回國,開始最后籌備名譽侵權案司。
但這次,送完比蔣更加病懨懨的蔣母回到家,卻并沒有先去找顧雁,領回被寄養多日的橙子,而是先陪同蔣回到昔日別墅,爬到三樓,來了一通徹徹底底的翻箱倒柜。
蔣蹲在邊。
看不懂到底在找些什麼,讓找鐘點工也不行,只能時不時在旁搭把手幫忙。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1070 章

奉子成婚:古少,求離婚(又名:離婚時愛你)
新婚夜,他給她一紙協議,“孩子出生後,便離婚。” 可為什麼孩子出生後,彆說離婚,連離床都不能……
171萬字8 363685 -
完結46 章

你如星辰不可及
蘇清下意識的拿手摸了一下微隆的小腹,她還沒來得及站穩就被人甩在了衣櫃上。後腦勺的疼痛,讓她悶哼了—聲。
4.2萬字8 18278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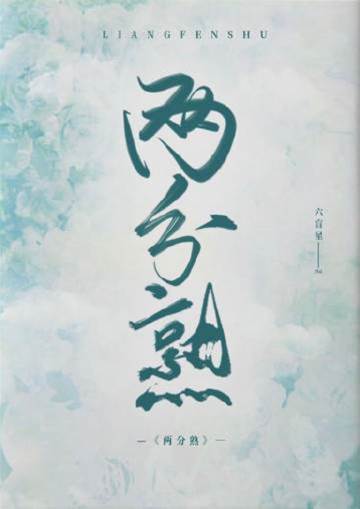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298 -
完結493 章
惡魔的寵愛
“以你的身材和技術,我認為隻值五毛錢,不過我沒零錢,不用找。”將一枚一塊的硬幣拍在床頭櫃上,喬錦挑釁地看著夜千塵。“好,很好!女人,很好!”夜千塵冷著臉,他夜千塵的第一次,竟然隻值五毛錢!再次見麵,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她是低到塵埃的花。一份價值兩億的契約,將她困在他身旁……
84.9萬字8 148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