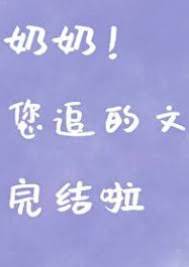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分手六年后,被竹馬上司堵進酒店》 第326章 回國
秦硯苦笑一聲,把米粒抱起來,坐到沙發上,輕輕著它的后背,“怎麼,就連你也不要我了?”“沒良心的小東西。”“是誰把你從宋城帶出來的?誰把你送到邊的?”“一走,正眼都不看我了?”米粒沒打采的喵了一聲。秦硯心里像是堵了一團棉花一樣,讓他有些不過氣來,這房子明明不大,可是卻讓人覺得空的厲害。以前林覓住在這里,后來又多了個李婉意,他雖然從沒有說過,可自小跟林覓相依為命,沒有誰真正關心過他,就連秦家的那些所謂親人,看到他也只是想要利用而已。只有李婉意,住進來之后,像個真正的長輩,會督促他早睡覺,盯著他按時吃一日三餐,還時不時用蹩腳的話提醒他不能忽視了林覓。可現在,什麼都沒有了。李婉意死了,林覓也走了。對他一定很失。他就這麼靜靜的在沙發上坐著,一直到了夜里,都沒有開燈。窗外的燈照進來,映照出他的影孤獨凄涼。晚上十點,桌上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秦硯看了一眼,接起來,“喂。”是手下的電話,匯報最新的進展,“秦總,據白小姐的供人,我們找到了李士的第一害現場,要……報警嗎?”報警的話,人證證都在,毫不費力就能把白小小和的那些手下送進監獄。蓄意殺人這種罪名,這輩子都不可能活著走出監獄。可秦硯之前下令要把白小小送回墨西哥,給維邦,卻并沒有安排手下的那些人怎麼辦。所以手下覺得有必要請示一下。秦硯拿著手機放在耳邊,瑩瑩亮照的他臉上明明暗暗,他開口,聲音冷漠又殘忍,“不用,把那些人都送回墨西哥吧。”報警送進監獄,便宜他們了。白小小和那些雇傭兵,都是以旅游簽的簽證過來的,他們沒有國的任何份證明,嚴格意義上甚至都不算國的人。應該不會讓程乾冰太為難。秦硯盤算了幾秒,又問了一句,“維邦那邊聯系上了嗎?”手下猶豫了一下,才道,“聯系上了,不過維邦說他早就對白小姐不興趣了,您這樣做是辱他。”秦硯輕笑,“告訴他,我就是在侮辱他,讓他隨意發揮。”這句話,幾乎定下了白小小的命運。手下又遲疑的道,“白小姐從下午就一直鬧著要再見您一面。”秦硯眼神冰冷,“沒有必要。”說完便直接掛了電話。他手機上很快就響起提示音,是手下把李婉意遇害地點的位置發過來了。他看著那個定位,低著頭沉默了一會,然后起拿了外套出門。那是他人的母親,也是他尊敬的長輩,無論如何,他都要過去送最后一程。秦硯驅車來到手機上的定位,因為沒報警,周圍都是由他的人站崗,秦硯的車一停下來,就有人過來給他開門。“秦總。”秦硯點點頭,面無表的走進去。這是一棟私人別墅,不是白小小剛來國時他買的那一棟,應該是后面自己添的,大概買的時候就打算理一些見不得的事。別墅里,一進門,就看到客廳里一大片跡,仔細看,是從臥室里一直蔓延到樓梯上,再從樓梯上到客廳,像是被人拖行下來。痕跡專家上前介紹道,“據現場留下的痕跡,李士被抓過來之后,一開始關在樓上臥室,應該跟白小姐起了爭執,白小姐拿花瓶砸了李士的頭。樓上花瓶的跡經過鑒定是李士的dna,之后李士倒在地上,白小姐用一把匕首割開了李士的頸脈,臥室跡呈噴灑狀,再然后,李士從臥室里爬出來,一路從樓梯爬到客廳,最終在客廳里失而亡。”秦硯的腦海中,隨著痕跡專家的聲音,慢慢的有了那副畫面。他眼中緒更加暗,良久才道,“我上去看看。”樓上臥室,果然如痕跡專家所說,和帶的花瓶,到都是鮮。因為時間已經過去了好幾天,腥味沒那麼重,秦硯在這棟別墅里待了半個多小時,最終抬離開。走出別墅的時候,他吩咐手下,“把這里燒了吧。”媽,人生如夢,愿你魂安。活人的罪,我會好好贖。你最牽掛的兒,我一定會找到,求得的原諒,好好照顧。我以命發誓,疼,永不負。……一個月后,米國一家甜品店。林覓從門外進來,走到最里面的位置,看著已經等在那里的影,出了一微笑,“你又來的這麼早,搞得我每次都好像遲到似的。”周紹文把給點的青梅葡萄推過去,臉上掛著淡淡笑意,那雙好看的眼睛里,全是面前人的影,他不以為意的笑著道,“紳士本來就該等待,而且我也早已習慣了等待。”林覓聽到這話,臉上沒有半分波瀾,笑的云淡風輕,“那你恐怕要繼續等下去了。”知道周紹文對的心思,可,誰說人邊必須要有個男人的?現在覺得一個人好,有錢,有工作,肚子里還有個孩子。
Advertisement
人生苦短,何必沾染滋味。已經全心全意的過一個人,事實證明到最后沒什麼好結果。不如單一人。周紹文有些無奈的看著笑,“你啊,給我留點期待怎麼了,非要把話說得這麼絕。”林覓卻很認真,“我是想告訴你,我不值得你在我上浪費時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周紹文攤了攤手,“你也別太自了,誰說我非你不可的,我就不能再喜歡一個嗎?實話跟你說吧,我快訂婚了。”林覓有些意外的挑眉,“真的?什麼時候的事?”周紹文努力讓自己笑的純粹一點,說,“家里介紹的,好一姑娘,我跟相了有半個月了,不出意外的話,很快就會訂婚了。”周家從有到無,又從無到有,即便現在恢復了一些元氣,可依舊遠遠不如當初。想要再進一步,唯有聯姻。大哥已經結婚了,聯姻的對象非他莫屬。以前他還抗拒,可現在……反正最后娶的不是,那娶誰有什麼區別呢?把這個消息告訴,也能讓安心一些。這一個月的時間,他能看出林覓面對自己的時候,那的愧疚之意。激他在最難的時候幫離開,卻又因為不能回饋他想要的而不知所措。既然如此,不如就讓他來主打破的無措。至從今以后,面對自己,能坦然很多吧。林覓聽了周紹文的話,果然笑了,眉眼之間都是真摯的祝福,“恭喜你,能遇到喜歡的孩不容易,要好好對人家。”周紹文笑著看著,“還用你提醒我?”哪怕不,他也會做好一個丈夫和父親的本職。因為周紹文要訂婚了,林覓跟他相起來終于覺得坦然了許多,問,“說吧,你來找我有什麼事?”今天可是公司收購的大日子,如果不是周紹文把話說的那麼嚴肅,肯定不會丟下工作來見他的。一個月前,在周紹文的幫助下來到了米國,在短暫的頹喪之后,很快就振作起來,先利用自己的積蓄給母親買了塊墓地,鄭重的把母親安葬之后,然后租了一套一室一廳的房子,解決了最本的生存需求之后,就開始投簡歷。憑借著以前優秀的履歷,很快就拿到了一份金融所的工作,年薪六十萬元,工作駕輕就,很快就適應了。林覓等著周紹文的回答。周紹文卻是沉默了,過了一會兒才說,“你……關注過國的事嗎?”林覓臉頓時就僵了一下,國的事有什麼好關注的?周紹文這是在問有沒有關注秦硯。沉默了片刻,才道,“既然離開了,以前的事就跟我再沒有關系了,人要向前看,不是嗎?”周紹文苦笑了一下,“是,你一向都是這麼理智又堅定的,他對你來說只是一段路上的風景,可他……好像很難忘記你,他一直在找你。”周紹文也沒想到,有一天,他會為敵說話。他也不甘心。可他已經沒有機會了,雖然很不想承認,可秦硯是真心的。他試著說,“人都會犯錯,秦硯雖然這件事做錯了,可是他意識到之后,很快就知錯就改,他理了白小小,也理了手底下那些人,這一個月,他全球各地的找你……”林覓眉頭皺了起來,不想再聽下去,聲音有些僵的打斷他,“我不關心他怎麼樣。”可以說的要求太極端,可在看來,不能給與全心全意的信任,這樣的不想要。要的很純粹,摻雜不了別的。白小小這件事,已經讓步了太多太多。可是秦硯依舊沒有理好,一直到事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才解決問題,有什麼用?母親能活過來嗎?得委屈和辱,能抹去嗎?秦硯重重義,很欣賞。可是不要了。他重他的重他的義,都跟無關了。也知道,白小小這件事,秦硯未嘗不是害者。可傷害不能挽回。不想見他,至短時間,只想一個人安靜的在這個陌生的地方生活。工作忙碌反而讓過的更加踏實。周紹文看著臉上抗拒的表,心中針扎一樣難,可是有些事,他不能瞞著。相的人,不該就此錯過。秦硯這一個月做事的架勢,像是完全變了個人,他覺得至該給秦硯一個機會。“林覓,你聽我說,”周紹文打斷林覓的拒絕,看著,緩聲道,“我知道你不想聽到他的任何消息,可是有些事,我希你知道,至于要怎麼選擇,我不會干涉你,不管你怎麼選擇,我都會支持你。”他說到這,停了一下,才接著道,“秦硯用自殺式的手段,協助警方破獲了緬北特大詐騙案,秦家從上到下所有人全都被抓進去了,蘇家也難逃一劫,因為采取的手段太激烈,他了很重的傷,傷到了肺腑,如今在icu里,已經躺了六天。”林覓的手放在桌子上,驀然收。周紹文看到的反應,就知道并沒有完全放下,頓了頓,才又道,“國沒有專家敢給他手,他在墨西哥有一個醫療隊,里面收錄了眾多頂尖專家,但他不肯過去,我猜他是為了等你,怕你回來找他的時候他不在,怕你會難過。”
Advertisement
林覓臉有些發白,抿著,一言不發。周紹文輕聲道,“他的傷,只能墨西哥那個醫療團隊才能治好。他不肯過去,那個醫療團隊收錄的專家都是有污點的,那些人不敢回國,秦硯不配合,傷就好不了,我不確定他還能撐多久。”林覓聽到這里,猛的抬起頭來,有些抖,“你說什麼?”周紹文輕輕嘆了口氣,“他傷得很重,如今在icu,也只是吊著一條命罷了。”林覓沒說話,站起來就走了。周紹文看著的背影走遠,輕輕嘆了口氣。他不知道今天說的這些話,能為這兩個人的幫上多大的忙,可他確實盡力了。林覓如果想回國,他會盡一切努力盡快安排。如果聽了這些話還是不想回去見秦硯,那……他也沒辦法了。林覓從甜品店出來之后,就快步往前走,腳步很快,就像是為了證明什麼,可等反應過來的時候,才發現自己走的是回公司相反的方向。臉上有些意,了一下,到了一手的水,下雨了?抬起頭,藍天白云,艷高照。是哭了。真是可笑,竟然哭了,為了秦硯?為了那個間接害死了母親的兇手,哭了?不是早就下定決心,再也不回頭了嗎?不是早就選擇跟他一刀兩斷了嗎?可現在又為什麼會哭呢?這一天,林覓沒回公司,打電話給上司請了假,在街上坐了整整一下午。然后若無其事的回了自己租的房子。一夜無眠。第二天,開車去了母親的墓地。墓碑上,李婉意笑容甜,是年輕時候最的模樣。“媽……”話沒出口已經哽咽,鼻子一酸,眼淚就掉了出來,即使已經過去了一個月,還是沒能走出來。不能釋懷,不能坦然。努力讓自己變得忙碌,好像這樣就能忘記一切,可其實,每天晚上閉上眼,腦海中都是母親生前的一顰一笑。如果和母親的緣分停留在當初誤會母親為蘇洵凱運毒的時候,一定不會這麼難過。可的母親是個好人,也是個好媽媽,從小到大,就只有這麼一個親人,絮絮叨叨的疼,不厭其煩的嘮叨一些年輕人不聽的話。天知道多麼這樣的母。可現在,一切都沒了。該恨秦硯的,該埋怨他的。可為什麼,聽到他的現狀,心卻痛的讓無法呼吸。“媽,對不起,我要回國了。”哭著跪在那座墓碑前面,慚愧和懊惱讓無地自容,覺得無法面對母親。可卻得回去看看。不回去,秦硯會死的。大概知道周紹文這番話為什麼會傳到自己的耳朵里。秦硯那個人,狡詐多端,他故意設下這個局,以他自己的命為餌,通過周紹文的,讓知道他的況。他賭不會無于衷。可笑的是他賭對了。再怨恨,也做不到眼睜睜看著他去死。……三天后。飛機落地,林覓踏上了京市的土地。一落地便打了個車,去了周紹文給的那個地址。是一家私人醫院,沒有提前跟任何人說,上了六樓,從走出電梯就發現,這一層走廊全都被人守著。林覓知道這些都是秦硯的人。對這些人沒有一點印象,原以為要費些功夫才能進去見到秦硯,沒想到秦硯的手下竟然認出了,有些驚喜的道,“太太?!”這一聲,頓時吸引了走廊里所有人的目,林覓被他們炙熱的目盯得有些不知所措,正要開口,幾個手下就圍上來道,“太太,您總算回來了!秦總就在病房里休息,我帶您去!”林覓只得跟著他們往前走。走到一間病房外面,手下都不了,說,“太太,秦總在里面。”林覓點了點頭,抬手推開病房門。里面空間并不大,一室一廳的樣子,病床上,一個瘦削的影躺在那里,正閉著眼睡著,手上上滿了管子。周紹文說他在icu命懸一線,看來況比周紹文說的要好一些。林覓站在門口沒有。不知道是不是心有靈犀,原本躺在床上閉著眼睛的男人,突然睜開了雙眼。林覓不期然撞進他的黑眸里,看著他眼中由死氣沉沉變得不敢相信,然后變得驚喜和激。腳底下像是生了,一都沒。秦硯被這突如其來的驚喜砸中,聲音竟然哽咽了,可憐兮兮的了一聲,“老婆……”你終于回來了。林覓看著他一個大男人竟然紅了眼眶,忍不住嗤笑了一聲,一出聲才發現自己竟然也哽咽了,眼圈紅的比他都厲害。他的況,顯然比周紹文說的好太多,周紹文夸張了不知道多倍。這又是他的計謀?故意把傷說的很嚴重,回來,看到傻乎乎的真的回來了,把原則扔掉不要,他是不是很得意?林覓咬了咬,轉就走。“老婆!”秦硯還沒從驚喜中回過神來,就看到要走,理之中,竟然扯掉了上的管子,掀開被子朝追過來。
Advertisement
猜你喜歡
-
完結193 章

我的霸道兵哥
她是他的藥,蘇爽甜寵撩。 大佬一:【八零兵哥】妹妹不想嫁那個當兵的,家裡人讓姐姐替嫁。(已撩完√) 大佬二:【禁欲影帝】驚!禁欲系影帝顛覆人設,豪宅藏嬌十八線……呃十八線都不是的龍套小女星!(正在撩) 大佬三:【霸總他叔】霸道總裁看上灰姑娘,想和門當戶對的未婚妻退婚,未婚妻轉頭勾搭上霸總他叔——大霸總! 大佬四:待續……
47.4萬字8 23379 -
完結308 章

盛宴之后
帥氣的老公跟大方和善的姐姐茍合在了一起。 她被打的遍體鱗傷,不但孩子不保,最后還被關進了精神病院。 她跪在那個她叫著姐姐的女人面前,求她放過她媽媽。 女人卻一陣冷笑,咬牙切齒的看著她:“譚小雅,這輩子,你已經輸了,你沒有資格跟我談條件……你這個賤種,跟著你媽一起下地獄吧。” 譚小雅瘋了一般的想要跟她拼了,最后卻慘死在自己老公的手下。 本以為自己這輩子就這麼敗了,可冥冥之中,竟又重生歸來。 他們給了她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摧殘,歡享一場饕餮盛宴。 且看盛宴之后,她如何逆天改命,將前世負了她的,一一討回來! 她要讓所有給過她屈辱的人,全部跪倒在她的膝前,卑微乞求她的原諒。
56.9萬字8 24291 -
完結872 章
她比糖更甜
豪門顧家抱錯的女兒找到了,所有人都在等著看這個從窮鄉僻壤來的真千金的笑話。熟料一眾骨灰級大佬紛紛冒頭——頂級財閥繼承人發帖,“求教,如何讓樂不思蜀的老大停止休假?例:顧瓷。言之奏效者獎金一億!”國際黑客組織瘋狂在各地電腦上刷屏,【致顧瓷:萬水千山總是情,回來管事行不行?】著名研究所聯名發表文章——《論顧瓷長時間休假對全人類發展與進步的重大危害》京都權勢滔天的太子爺怒起掀桌,“都給爺爬,顧瓷我的!”
138.8萬字8 152966 -
完結106 章

投其所好
身為翻譯官,周宴京見過無數美景,都不及祖國的大好河山,與丹枝穿旗袍時的婀娜多姿。.首席翻譯官周宴京剛上任,就因眉宇清俊、言辭犀利給眾人留下深刻印象。有網友打開百科資料,發現家庭一欄寫著——“已訂婚。”…
38.6萬字8 9572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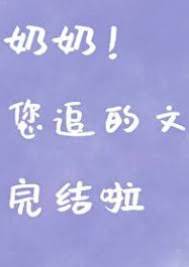
南風知我意
清遠公安裴西洲,警校畢業履歷光鮮,禁慾系禍害臉,追求者衆卻無一近的了身,白瞎了那顏值。 某天裴西洲受傷醫院就醫,醫生是個女孩,緊張兮兮問他:“你沒事吧?” 衆人心道又一個被美色迷了眼的,這點傷貼創可貼就行吧? “有事,”裴西洲睫毛低垂,語氣認真,“很疼。” “那怎樣纔會好一些?” 裴西洲冷冷淡淡看着她,片刻後低聲道:“抱。” - 緊接着,衆人發現輕傷不下火線的裴西洲變乖了—— 頭疼發熱知道去輸液:南風醫生,我感冒了。 受傷流血知道看醫生:南風醫生,我受傷了。 直到同事撞見裴西洲把南風醫生禁錮在懷裏,語氣很兇:“那個人是誰?不準和他說話!” 女孩踮起腳尖親他側臉:“知道啦!你不要吃醋!” 裴西洲耳根瞬間紅透,落荒而逃。 ——破案了。 ——還挺純情。 - 後來,裴西洲受傷生死一線,南風問他疼嗎。 裴西洲笑着伸手擋住她眼睛不讓她看:“不疼。” 南風瞬間紅了眼:“騙人!” 卻聽見他嘆氣,清冷聲線盡是無奈:“見不得你哭。”
36.3萬字8.18 137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