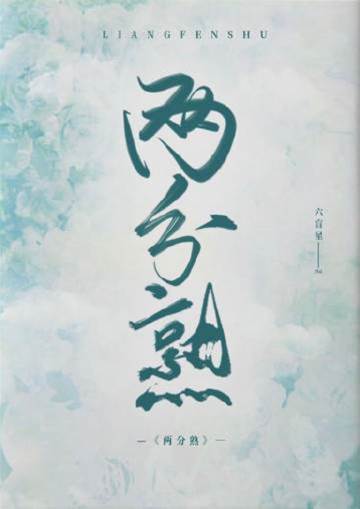《嬌吻!小美人一哭,徐總寵溺輕哄》 第1卷 第124章 手帕
被哄了好一會兒,小棉花糖才止住泣。
逢秋把抱在懷里,干凈的指尖著一塊小小的淡繡花手帕,輕輕掉孩子眼角和臉蛋兒上的淚珠。
小棉花糖看著媽媽,逢秋一抬手,就出自己白白的小手攥住逢秋著的手帕。
漆黑干凈的圓圓瞳孔看著逢秋,乖巧地眨眨眼,剛才還在哭,這會兒就對著逢秋笑了起來。
孩子的笑容和大人的不一樣,孩子的笑容、單純,對世界沒有任何防備心。
逢秋彎了彎眸,低頭看著響響,目溫,“響響不怕,媽媽在呢。”
小棉花糖眨眨眼,小手指攥手帕。
逢秋笑了笑,索把手帕給玩了,接著認真叮囑小棉花糖:“只能玩,不能吃。”
響響好像也沒打算吃,就是玩玩,這只小棉花糖還是更喜歡吃自己的小拳頭。
不一會兒,月嫂沖好送過來。
小棉花糖出生后一直是母和混著吃,剛開始是因為逢秋還不怎麼會當媽媽,喂不好,孩子吃得不開心,也難。
后來是因為徐清堅持反對讓小棉花糖只吃母,他是怕小棉花糖養只吃母的習慣后,一天到晚都粘著媽媽,逢秋不僅累,也會失去自己的個人生活。
“太太,我來喂小小姐喝吧。”月嫂道。
Advertisement
逢秋彎眸看了看響響,接著抬眸向月嫂,“我來吧。”
月嫂抿了抿,把玻璃小瓶遞給逢秋。
心里是比較張的,這一家是當月嫂以來接過層次最高的豪門,不僅有錢還有權勢。
戰戰兢兢,唯恐哪里伺候得不到位,丟了工作是小事,怕的是得罪徐家和虞家。
不過一段時間過去,月嫂發現這對夫妻并沒有起初想象中的那麼可怕,他們夫妻恩、家庭幸福,對待保姆和月嫂的態度都很溫和。
相比于以前那些覺得自己有幾個錢就高人一等看不起傭人的雇主,徐清和逢秋簡直比他們強上百倍。
真正居高位的人,他們上是沒有“狹隘”這個詞的。
逢秋喂響響喝的時候,白白的小手還攥著手帕,兩只小手著手帕玩,小含住喝,吮吸的時候小一一的,像小貓似的發出細細的嘬嘬聲。
小棉花糖能一心三用,玩手帕、喝、看媽媽。
喂完,逢秋抱著孩子站起,在客廳門廊下來回踱步,看著庭院里的亭臺水榭、蔭綠樹,心放松愉快。
“太太,門口有一位姓謝的先生來看您,他說他是您的朋友。”保姆從連廊走過來對逢秋說。
逢秋抿了抿,聲音,“帶他進來。”
Advertisement
“好的太太。”
五分鐘后,保姆領著謝明安走進客廳,逢秋抱著響響坐在沙發上陪玩手帕。
和生孩子前相比沒什麼變化,一樣的漂亮、一樣的幸福,甚至看起來比以前更加有魅力。
孩穿著白和咖短,濃的長發用一白帶挽在腦后,雙頰邊垂落蓬松烏黑的發,淺淺彎眸,角含笑,很溫很漂亮。
謝明安扯了扯,“冒昧前來,會不會打擾到你?”
聽到聲音,逢秋抬頭看見謝明安,孩溫地彎起角,“不會,謝先生,請坐。”
隨后逢秋對保姆說,“阿姨,你去泡杯茶,我記得徐清之前買了一包金瓜貢茶,用那個泡。”
“好的太太。”
“你傷了。”跟保姆說完話,逢秋才看到男人藏在大下的打著石膏吊著繃帶的手臂,下意識蹙了蹙眉。
謝明安神微頓,淺綠眸中鷙一閃而過,隨后彎笑了笑,氣息溫爾文雅,“先前被咖啡店的博古架砸到了,沒什麼事,過幾天就去醫院拆石膏。”
逢秋點點頭。
謝明安的目落在懷里的小孩子上,看到響響那張可的小臉蛋兒,謝明安斂了斂眉,語氣儒雅真誠,“很漂亮的一個小孩,像你。”
“眼睛像我先生。”逢秋說。
大概恩的夫妻有了孩子后都是這樣,都想從孩子的上找出對方的影子。
Advertisement
謝明安把自己郁的緒藏得很好,面對逢秋時,他臉上有一張近乎完的面,有時候這張面,甚至能騙過他自己。
每當這個時候,他都會想起那些看似已經被忘的事,過去的一幕幕浮現出來,他走馬觀花似的一遍遍重溫那些徹骨銘心的記憶。
管中的每一個細胞都在躁,每一神經都在表達他的執念,大腦告訴他,他從沒有放棄過逢秋,也從不甘心永遠失去。
保姆泡好茶端給謝明安,謝明安抿了口,抬眸看向逢秋,笑著說:“確實是好茶,我應該喝到了徐公子的藏品,金瓜貢茶,普洱茶中的頂尖,徐公子買茶的時候應該花了不錢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過你喜歡就好。”逢秋聲音溫。
孩子乖乖地躺在懷里。玩膩了手帕,干凈圓的漆黑小瞳孔一會兒看看逢秋,一會兒又看看旁邊那個陌生人。
看了幾次后,好像終于確定這個男人不是爸爸,小棉花糖就不看他了,小腦袋瓜著媽媽心口聽媽媽心跳。
離開前,謝明安從懷里掏出一對專門為小孩子定制的羊脂玉小手鐲,極好,價值不菲。
“送給小棉花糖的見面禮。”謝明安說。
逢秋抿了抿,眉眼彎彎,溫淺笑,“謝謝,要不要抱抱小棉花糖?”
Advertisement
“我不太會抱小孩子,別把弄哭了,下次吧。”謝明安斂了斂眉,站起走到逢秋旁邊,垂眸認真看了看小棉花糖,眼睛確實很像徐清,漆黑深邃,圓圓的小瞳孔很干凈很單純。
這只小棉花糖對世界沒有一點惡意,是幸福的,沒被世界傷害過的純粹的幸福。
“其實你可以抱一下的,很乖,也不怎麼怕生。”逢秋語氣溫。
謝明安抿了抿,終究是沒有抱這只小棉花糖,他只用自己溫熱的指尖輕輕了一下孩子的小拳頭。
猜你喜歡
-
完結91 章

偏要你獨屬我
分手兩年後,秦煙在南尋大學校友會上見到靳南野。 包間內的氛圍燈光撒下,將他棱角分明的臉映照得晦暗不明。 曾經那個將她備注成“小可愛”的青澀少年,如今早已蛻成了商場上殺伐果斷的男人。 明明頂著壹張俊逸卓絕的臉,手段卻淩厲如刀。 秦煙躲在角落處,偷聽他們講話。 老同學問靳南野:“既然回來了,妳就不打算去找秦煙嗎?” 男人有壹雙桃花眼,看人時總是暧昧含情,可聽到這個名字時他卻眸光微斂,渾身的氣息清冷淡漠。 他慵懶地靠在沙發上,語調漫不經心:“找她做什麽?我又不是非她不可。” 秦煙不願再聽,轉身就走。 在她走後沒多久,靳南野的眼尾慢慢紅了。在嘈雜的歌聲中,他分明聽到了自己的聲音。 “明明是她不要我了。” - 幾年過去,在他們複合後的某個夜晚,靳南野俯身抱住秦煙。 濃郁的酒香包裹住兩人,就連空氣也變得燥熱稀薄。 男人貼著她的耳畔,嗓音低啞缱绻,“秦秦,我喝醉了。” 他輕啄了壹下她的唇。 “可以跟妳撒個嬌嗎?” *破鏡重圓,甜文,雙c雙初戀 *悶騷深情忠犬×又純又欲野貓 *年齡差:男比女大三歲
27.3萬字8 18406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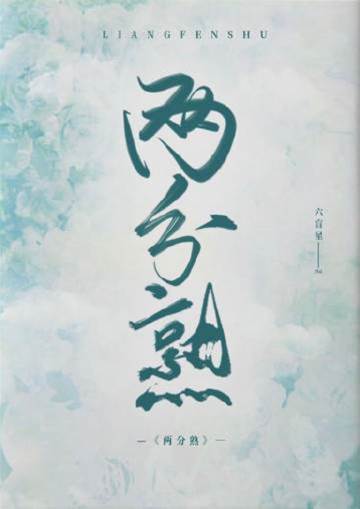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302 -
完結62 章

要和我交往嗎
徐其遇被稱爲晉大的高嶺之花,眉目疏朗,多少女生沉迷他的臉。 餘初檸不一樣,她看中的是他的身體。 爲了能讓徐其遇做一次自己的人體模特,餘初檸特地去找了這位傳說中的高嶺之花。 可在見到徐其遇第一眼時,餘初檸立即換了想法。 做什麼人體模特啊,男朋友不是更好! 三個月後,餘初檸碰壁無數,選擇放棄:) * 畫室中,餘初檸正在畫畫,徐其遇突然闖了進來。 餘初檸:“幹、幹什麼!” 徐其遇微眯着眸子,二話不說開始解襯衫鈕釦:“聽說你在找人體模特,我來應聘。” 餘初檸看着他的動作,臉色漲紅地說:“應聘就應聘,脫什麼衣服!” 徐其遇手上動作未停,輕笑了一聲:“不脫衣服怎麼驗身,如果你不滿意怎麼辦?” 餘初檸連連點頭:“滿意滿意!” 可這時,徐其遇停了下來,微微勾脣道:“不過我價格很貴,不知道你付不付得起。” 餘初檸:“什麼價位?” 徐其遇:“我要你。”
16.8萬字8 4333 -
完結435 章
一手遮腰
【清醒心機旗袍設計師vs偏執禁慾資本大佬】南婠為了籌謀算計,攀附上了清絕皮囊下殺伐果斷的賀淮宴,借的是他放在心尖兒上那位的光。後來她挽著別的男人高調粉墨登場。賀淮宴冷笑:「白眼狼」南婠:「賀先生,這場遊戲你該自負盈虧」平生驚鴻一遇,神明終迷了凡心,賀淮宴眼裡的南婠似誘似癮,他只想沾染入骨。
66.3萬字8 51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