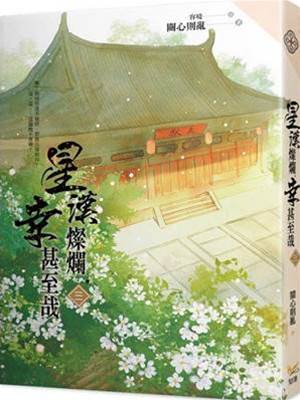《回到明朝當王爺》 第455章 離間-456 戰端初現
馬上的大漢泄氣地怒吼一聲,拔出長刀吶喊一聲,一撥馬頭向岸上沖去,那些桿繩上掛著鮮艷麗的服,那些營帳防雨效果極好,冬天防風保暖也極為出,他當然看的出來,那些東西馬上就是屬于自已的財產了,他可不舍的破壞掉。
與此同時,陸地的幾個方向,方才還盛待客的韃靼牧人,就象一群群兇猛噬的狼,揮舞著刀劍沖殺過來。能在草原上千萬里跋涉經商的行賈,就算自已不通武藝,也必然雇傭有兇悍勇猛的護衛,他們的戰斗力不容小覷。
然而現在他們人數、馬匹、沒有防備,駱駝四散吃著野草,也來不及布駝陣防衛,可以說這些商賈完全信任他們,萬萬不會想到他們犯草原上極大的忌,公開在自已的領地洗劫行商,這為他們的突然襲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那些支起攤子準備做生意的商賈本來不及反抗,他們驚恐地呼喊著伙伴,飛快地向營區逃去。
韃靼人的營帳,每頂之間至隔著數十丈遠,而這些商賈為了照顧車馬和貨,那些營帳設立的很近,彼此的間距有限,再加上為了固定帳蓬斜斜釘立在地一條條繩索,這為他們周旋逃命提供了機會。
烏恩其豈容他們做出反應,一聲號令,兇悍如虎的戰士們就撥馬沖進了營區。近百頂營帳象一片森林,將雙方不到兩千人的隊伍完全吞沒在其中。絆馬索、陷馬坑、突兀來的冷箭、還有吹箭、飛斧、標槍。
最聽人驚訝的是還有些和他們高大的材相比簡直就是些小挫子的人手里揮舞著長刀,發出咿呀的怪從營帳中撲出來,還沒沖到面前就一頭栽倒在地,連滾帶爬來的飛快,跟滾地葫蘆似的到了馬下,不是砍斷馬就是刺穿馬腹,帶著一頭一臉的鮮厲鬼似的跳開。
Advertisement
他們怒吼著,騎在馬上了活靶子,到四面八方全方位立式的進攻,而戰馬的優勢本無從發揮,想要撥馬沖出去,廝殺混中命令已經無法下達,他們是來洗劫的,本沒有攜帶旗幟,誰會想到迎來的卻是一場屠,這時想號令上當的部下退出去,已經完全來不及了。
遠遠的,他們的婦人和孩子站在營盤看著自已的父兄英勇地沖進那些商賈的營地,不發出熱烈的歡呼。
他們的眼睛里放著興的芒,因為很快的,他們的親人將把他們需要而買不起的家什、玩、華的綢、昂貴的珠寶、的地毯和鮮艷的袍給他們送回來........
一陣暖風吹來,挾著野草味、花香味、牛糞味、羊糞味,還有........腥味。
這些由各族最兇悍、最殘忍的流浪者組的掠食隊伍,人人兇大盛,就象一只只擇人而噬的虎狼一般,不擇手段,用盡一切手法毫不手地屠著這些闖者。短兵相接、白刃加的時候,這些馬上的英雄遠非他們的敵手。
上砍人、下砍馬,如泉涌,這群一見了就兇大發的野原紅著眼睛,發出比韃靼勇士更兇狠、更慘厲的嚎,一個個全都變了渾浴的屠夫。
幸好,吞彌做為首領,還沒有忘記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在他的命令下,幾個通曉蒙語的部下,開始一面廝殺,一面忘形地用蒙語互相吶喊鼓勁,他們所泄的幾個地名、部落名,乃至首領的名字,已經足以讓這些拼命掙扎著想要逃出死亡陷阱的韃靼相信,這是瓦剌人派來的一群兇手。
這群人種組如此復雜的隊伍,也只有領地同西域和極北之地接壤的亦不剌才招募得到,不是麼?
Advertisement
……
賽馬者沖回來了,那些負責攪他人行進路線的輔助者們已經遠遠的落在了后邊,而且眾目睽睽之下也沒有人再敢做出阻礙他人行進的事。沖在最前邊的人都在快馬加鞭,向著終點的彩旗飛奔著。
崔鶯兒不負重沖在最前面,同樣是千里挑一的駿馬,同樣是萬中無一的騎,重就了決定七十里賽程最終勝利者的必要條件。隨其后的,是封雷、布和、蘇赫魯、真部的哈刺等人。
站在高臺上的白音、阿古達木等人都松了一口氣,暫時的勝利不要,真正要決出一個三藝第一的英雄是很難的,沖在最前邊的那位塔卡部的年輕人雖然跑了賽馬第一,但是他過于單薄的想要贏得摔跤比賽那可能麼?
至于箭,他們對自已的子侄也甚有信心,相信最后這些獲得單項勝利的人將不得不再戰一場,一場角逐王的比賽。最后選取一名各項名次皆優異在前的騎士為王的夫婿,他們還有機會,最后的時刻還沒有到來。
楊凌欣然站在帳前,看著遠被歡呼的牧民簇擁著紅娘子趕向王的營帳,輕笑了兩聲。銀琦王一直待在帳,陪伴著活佛和練指揮使等貴客品茶飲酒,從來不曾跑到帳外去關注賽事的進行,但是那達慕舉辦了三天,第一項比賽的冠軍出現時,的神間還是不免有些張。
聽到有人高聲稟報比賽的結果,優勝而出的人是楊英時,銀琦的肩頭一塌,明顯從張中松馳了下來,那角,也不出了一淺淺的笑意。晶亮的眸子微微一轉,瞟了活佛等人一眼,那剛剛綻現的笑便被收起了,可是兩抹彎彎的眉梢兒,還是不經意地抖擻出一片喜氣。
Advertisement
一位步履蹣跚的年高老者,穿著干凈的蒙袍,走到了紅娘子的馬前,捧著潔白的哈達,唱起了優的贊歌:“廣眾聚集的那達慕,穎而出的這馬,脖頸上系著龍王的彩帶,骨上打著經師的烙印。大象般的頭顱,魚鱗般的腭紋,蒼狼般的雙耳,明星般的眼睛,彩虹般的尾,絨般的頸鬢。每個關節長滿茸,每茸上鎏金溢彩。這匹天造地設的神駒寶馬喲,把那吉祥圣潔的鮮抹在你的頭上........”。
他對馬的姿,甚至馬的每一個部位都備加贊揚,并舉著一只漆金小碗蘸著子抹在駿馬的腦門上,最后把馬高高舉起,敬獻給楊英。
紅娘子見他用手指頭蘸著馬在馬上胡涂抹一番,最后還把剩下的馬讓喝掉,不暗暗蹙眉。可這是草原上的風俗,許許多多牧民都在用熱誠、崇敬的目盯著看,而那些敗在手下的勇士們眼地看著手中的小碗,似乎還滿懷嫉妒。
崔鶯兒苦笑一聲,著頭皮舉起碗來,把眼一閉,將那半碗馬生生地灌了下去。草原上沸騰起來了,遠遠近近的牧民圍了一個大大小小的圈子,手拉著手兒載歌載舞,到是一片祥和安樂的氣氛。
綺韻站在帳前,微笑著看著歡樂歌舞的牧人,聽著那音樂的節奏,下微微點著,應和著他們的節奏,似乎也要隨歌而起了。這時一個人悄然走到了的后,低嗓音稟報了幾句。
綺韻肩頭隨著牧人的歌聲輕輕晃著,若無其事地轉過頭,吩咐道:“讓他們手,不要干預。等他們功之后,把艾慎帶回來,其余的人全部消失”。
“是!”后的人影又悄然離開了。
Advertisement
“韻兒”。
“大人”,綺韻扭過頭,臉上換上了甜甜的笑。
“你怎麼也晃來晃去的,喜歡他們的舞蹈麼?”
“他們的舞蹈歡快灑,別有一番味道,還不錯”。
楊凌走近了來,攬著的腰著那些載歌載舞的牧民,笑道:“我倒更喜歡你跳的舞蹈,比這要好看一百倍”。
“我?”綺韻的眼珠溜溜兒一轉,詫異地道:“我有在大人面前跳過舞麼?我怎麼不記得?”
“怎麼沒有?記的那是你第一次到我府里,住在書房,纖腰上系著一條黃金的腰鏈,跳的那天竺舞蹈........,水為、蛇為骨,嫵的扭、魅的眼神,好一條要命的狐貍”。楊凌嘿嘿地笑。
綺韻咬著,笑盈盈地打了他一下,手掠了掠發,眼波流盼地聲道:“那........人家今晚再跳給你看,跳給你一個人看,好不好?”
“唔!唔唔........好!”,綺韻忽然發現楊凌放在腰間的手拿開了,他的兩只眼睛著前方,臉上的表無比的嚴肅,那下還在很認真地點著,好一副和正在談‘公事’的無恥臉。
綺韻會意地移眸橫睇,不出所料,崔鶯兒在封雷、荊佛兒等人的陪同下正從帳前經過,雖然不便過來相見,那雙澄澈如水的眸子可一直盯著這兒瞧呢。
“哼!老爺就只怕!”綺韻忿忿地哼了一聲,一邊若無其事的背起了雙手,一邊把那靴尖兒上了楊凌的腳面,肩膀向前一傾,輾呀,輾呀……
猜你喜歡
-
完結387 章
腹黑毒女神醫相公
冬暖故坐著黑道第一家族的第一把交椅,沒想過她會死在她隻手撐起的勢力中.也罷,前世過得太累,既得重活一世,今生,她只求歲月靜好.可,今生就算她變成一個啞巴,竟還是有人見不得她安寧.既然如此,就別怨她出手無情,誰死誰活,幹她何事?只是,這座庭院實在沒有安寧,換一處吧.彼時,正值皇上爲羿王世子選親,帝都內所有官家適齡女兒紛紛稱病,只求自己不被皇上挑中.只因,沒有人願意嫁給一個身殘病弱還不能行人事的男人守活寡,就算他是世子爺.彼時,冬暖故淺笑吟吟地走出來,寫道:"我嫁."喜堂之上,拜堂之前,他當著衆賓客的面扯下她頭上的喜帕,面無表情道:"這樣,你依然願嫁?"冬暖故看著由人攙扶著的他,再看他空蕩蕩的右邊袖管,不驚不詫,只微微一笑,拉過他的左手,在他左手手心寫下,"爲何不願?"他將喜帕重新蓋回她頭上,淡淡道:"好,繼續."*世人只知她是相府見不得光的私生女,卻不知她是連太醫院都求之不得的"毒蛇之女".世人只知他是身殘體弱的羿王府世子,卻不知他是連王上都禮讓三分的神醫"詭公子".*冬暖故: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欺他辱他者,我必讓你們體會
149.1萬字8.18 72932 -
完結284 章

一等狂妃傾天下
“唐蓮是魔鬼!”北國之內,提起唐家三小姐人人皆是一臉懼色,嘴角抽搐,男人聞之不舉,女人聞之變色,北國皇帝更是懸賞萬金全國通緝,而在一月之前…… 世人皆知唐家的廢柴三小姐無才無德無貌,典型的三無人員,一副白癡樣,爹不疼娘不愛,受盡世人白眼。 再次睜眼,廢柴的身軀里入駐了二十一世紀特工之魂,殺伐狠絕,傲世狂歌,一身血腥,震懾天下。 “欺我者,我必還之;辱我者,我必殺之。天阻我滅天,地擋我毀地,誰要敢不知好歹,滅了你全家!想要做我的男人,就要拿出本領來征服我。你們這些蠢貨,信不信老娘一巴掌把你們拍到牆上,想摳都摳不下來!” 一朝塵變風雲起,鴻鵠高歌獨此間。驚世凰穹蒼生亂,逐鹿天下奪至尊! 一襲紅衣,風華絕代,風起雲涌,群雄逐鹿,一展雄風,世間唯她獨尊! 女強VS男強!強強聯合! 更有無敵可愛天才寶寶!
72.4萬字8 33132 -
完結1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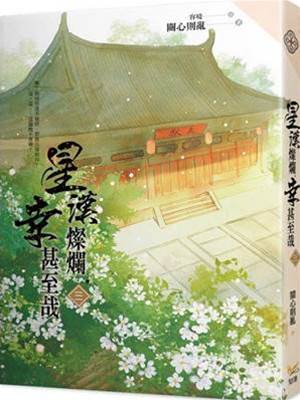
星漢燦爛,幸甚至哉
許多年后,她回望人生,覺得這輩子她投的胎實在比上輩子強多了,那究竟是什麼緣故讓她這樣一個認真生活態度勤懇的人走上如此一條逗逼之路呢? 雖然認真但依舊無能版的文案:依舊是一個小女子的八卦人生,家長里短,細水流長,慢熱。 天雷,狗血,瑪麗蘇,包括男女主在內的大多數角色的人設都不完美,不喜勿入,切記,切記。
90.7萬字8 54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