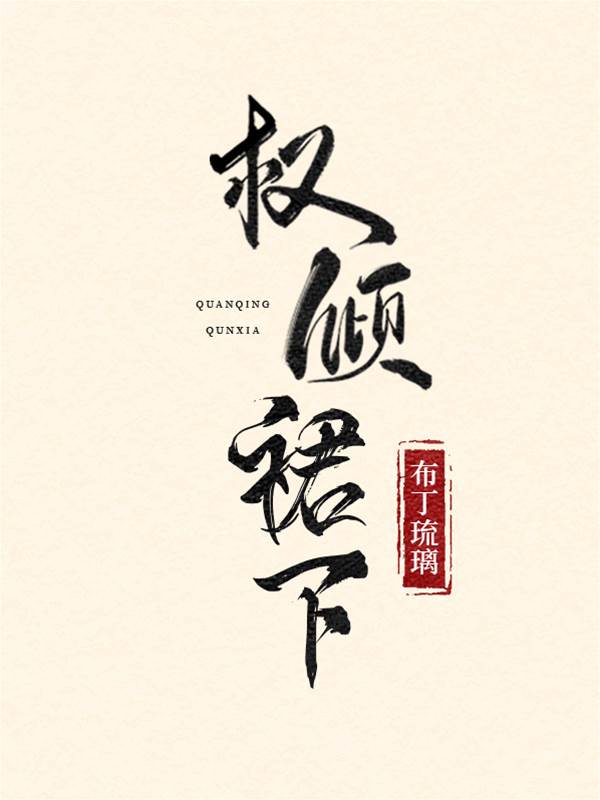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為奴三年后,整個侯府跪求我原諒》 第280章 她就是我的
不打量起楚知熠來。
哪怕這會兒穿著麻布,上的線條也依舊若若現。
眼神銳利如鷹,臉上那道傷疤更是讓他本就俊朗的面孔添了幾分兇惡。
他連熊都能殺死,要對付更是輕而易舉了。
可喬念又覺得,他不是壞人。
村里人對他的評價都很好,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個好人。
既然是好人,那就不會強迫別人。
于是,喬念深吸了一口氣,這才開了口,“白大哥,我不想婚,這銀子我不能收。”
“……”
楚知熠詫異地抬眸看著喬念,夜幕已然落下,屋子里點著燭燈。
他看不清的面孔,卻能看清楚那雙瑩亮的眸中閃著的慌。
知道是自己方才的話惹了誤會,楚知熠這才道,“河灣村民風淳樸,卻也難保有一兩顆老鼠屎,你收床底下,安全些。”
五十兩,不是小數目,足夠普通人家食無憂地活個幾年了。
喬念又是一愣。
誤會了?
臉頰瞬間滾燙了起來。
別人好心好意救了,倒好,竟是覺得別人目的不純!
濃烈的歉疚襲來,喬念忙是開了口,“對不起白大哥,我,我不該誤會……”
楚知熠并未在意,“是我話,詞不達意,你別放心上。”
說罷,便是將靠在墻邊的木板放下,合躺了上去。
Advertisement
一個從將救起就一直睡在院子里的男人,怎麼可能對有別的心思?
喬念又暗暗罵了自己一句,這才轉回了屋,將銀子藏在了床下。
夜里,老鼠屎果然來了。
睡夢中,喬念約約察覺到有人在自己的臉頰。
當下便是警覺地睜開了眼來,正好與那一雙細長的眸子對上了。
“啊!”
一聲驚呼。
對方顯然沒想到喬念居然會突然醒了,還沒反應過來,下一瞬,楚知熠已是從窗戶外一躍而。
一拳就打在了對方的臉上。
力道極重,對方一下子就倒在地上。
而與此同時,另一邊的窗戶旁,一個人影閃現而去。
喬念見狀,出一顆石子便照著那人影了過去。
恰好就在了對方的上。
但,力道不夠,對方雖然吃痛摔了一跤,卻還是很快爬起,繼續跑走了。
喬念眉心低沉,暗暗嘖了一聲。
這一手功夫,果然還沒練到家。
而楚知熠已是走到了倒在地上的那人面前,一手抓起對方的領,一手朝著對方的臉頰狠狠扇了過去。
扇般的手掌,只一下就打得那人頭暈眼花,連連求饒,“白,白哥,我錯了,錯了。”
楚知熠沒聽,又是一掌,直接將人給扇暈了過去。
這才起,轉頭看向了喬念,“你會武功?”
喬念也沒想到天這麼黑,楚知熠居然還能看到方才出手了,忙是微微點了點頭,“會一點點。”
Advertisement
一點點?
借著夜,楚知熠打量著喬念。
帶著他親手所刻的平安扣,應該是荊巖的妹妹才對。
會一點點武功,可能是荊巖教的。
可,方才出手的那一招,是蕭何的。
跟蕭何也認識?
既然跟蕭何學了這一招,又為何會被人打得滿是傷?
到底,是什麼份?
……
蕭何從軍回來的時候,直接就去了自己的書房。
卻不想,一推開門就見到了蕭衡。
眸微微一沉,他如若無事般上前,淡淡問道,“怎麼來我這兒了?長河那邊不用看著?”
“不用,派人盯著了。”蕭衡亦是淡淡開口,一雙眸子卻如鷹隼般一直盯著蕭何。
眼見著蕭何的目若有似無地從桌案上拂過,蕭衡冷聲一笑,食指與中指夾起了一張信紙來,“大哥在找這個?”
蕭何臉沉了下來,沒說話。
那是派去長河分支的人寄來的書信,每日都有,每日都寫著還未尋到。
蕭衡角的譏諷卻是越來越濃,“大哥這樣的是什麼意思?是想找到念念后瞞著我遠走高飛?”
他這副樣子,倒是有幾分捉的意思。
只惹得蕭何心頭發笑,“蕭衡,是我的妻。我與去何,與你無關。”
“你的妻?”蕭衡斜靠在椅子上,笑意漸漸收斂,“你們早就和離了。”
Advertisement
就算那封和離書是蕭母給的,可那上頭卻是實實在在按了蕭何的手印。
他昏睡不醒的那十二個時辰里,喬念早就與他沒有任何關系了!
這件事,是蕭何的痛點。
他那負在后的手驟然握,看著蕭衡,聲音微冷,“就算如此,你也不該將幽!若非是你,念念也不會跳下長河,到如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尸!”
卻不想,蕭衡猛然站起,“本該就是我的!才是侯府嫡,與我有婚約的人本該就是!若非當日你非要來橫一腳,我已經明正大娶了了!”
蕭衡厲喝著,語氣中滿是責怪,“我為做過些什麼,你最清楚!我有多在意,你也最明白!你是我親哥!”
“就因為我是你親哥!我才沒有對付你!”蕭何亦是厲聲呵斥。
侯府,孫獻,他都了。
唯獨沒有蕭衡。
“是人,不是一件品!有自己的生活,不屬于任何人!”
何去何從,應該是自己說了算!
哪怕他一心想要陪著,也只是陪去想去的地方!
而不是將幽在某一,限制的自由,還口口聲聲說著!
蕭何的話,仿若一把尖刀,狠狠扎在蕭衡的心口上。
可,那雙厲的雙眸越發偏執,“不,就是我的,你們誰都搶不走!長河分支附近,我會派人去找,不勞大哥費心。”
Advertisement
說罷,他方才將手中的信紙拍在了桌案上,“把你的人都召回來,否則,別怪我不客氣。”
他說完就要往外走,卻不想,蕭何只淡淡一聲,“我不會召回來的。”
聞言,蕭衡心中忍的怒火終于迸發。
垂在側的雙拳握,猛地轉便是朝著蕭何的臉上招呼了過去。
蕭何子往后微微一仰,看看避過,卻不想,蕭衡的拳頭再次襲了過來。
他只能步步后退。
相反,蕭衡卻是步步。
卻不想,蕭母忽然出現在書房外。
蕭何一驚,眼見著蕭衡的拳頭襲來,他終于還是站定了腳步,沒躲。
猜你喜歡
-
完結441 章

將軍,夫人又要爬牆了
秦家有女,姝色無雙,嫁得定國公府的繼承人,榮寵一生繁華一生。可世人不知道,秦珂隻是表麵上看著風光,心裡苦得肝腸寸斷,甚至年輕輕就鬱鬱而終了。重活一世,秦珂還是那個秦珂,赫連欽也還是那個赫連欽,但是秦珂發誓,此生隻要她有一口氣在,就絕對不嫁赫連欽。
83.1萬字8 22233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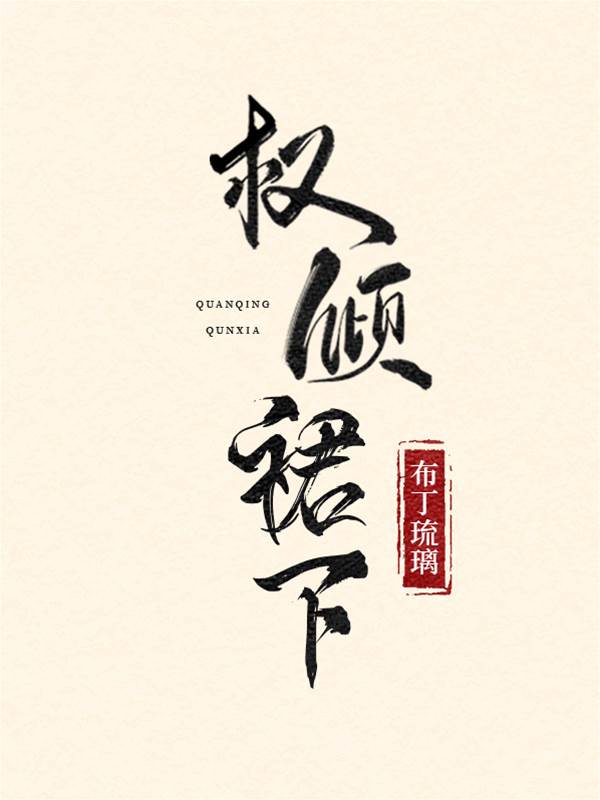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266 -
完結142 章

陛下今天也很好哄
蕭知雲上輩子入宮便是貴妃,過着千金狐裘墊腳,和田玉杯喝果汁,每天躺着被餵飯吃的舒服日子。 狗皇帝卻總覺得她藏着心事,每日不是哀怨地看着她,就是抱着她睡睡覺,純素覺。 是的,還不用侍寢的神仙日子。 蕭知雲(低頭)心想:伶舟行是不是…… 一朝重生, 爲了心心念唸的好日子,蕭知雲再次入宮,狗皇帝卻只封她做了低等的美人,還將破破爛爛的宮殿打發給她。 蕭知雲看着檐下佈滿的蛛絲,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誰知人還沒進去呢,就有宮人來恭喜婕妤娘娘,好聲好氣地請她去新殿住下。 蕭知雲(喜)拭淚:哭一下就升位份啦? 男主視角: 伶舟行自小便有心疾,他時常夢見一個人。 她好像很愛他,但伶舟行不會愛人。 他只會轉手將西域剛進貢來的狐裘送給她踩來墊腳,玉杯給她斟果汁,還會在夜裏爲她揉肩按腰。 他嗤笑夢中的自己,更可恨那入夢的妖女。 直到有一天,他在入宮的秀女中看見了那張一模一樣的臉。 伶舟行偏偏要和夢中的他作對,於是給了她最低的位分,最差的宮殿。 得知蕭知雲大哭一場,伶舟行明明該心情大好,等來的卻是自己心疾突犯,他怔怔地捂住了胸口。 小劇場: 蕭知雲想,這一世伶舟行爲何會對自己如此不好,難道是入宮的時機不對? 宮裏的嬤嬤都說,男人總是都愛那檔子事的。 雖然她沒幹過,但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某天蕭知雲還是大膽地身着清涼,耳根緋紅地在被褥裏等他。 伶舟行(掀開被子)(疑惑):你不冷嗎? 蕭知雲:……去死。 伶舟行不知道蕭知雲哪來的嬌貴性子,魚肉不挑刺不吃,肉片切厚了不吃,醬味重了會嘔,葡萄更是不可能自己動手剝的。 剝了荔枝挑了核遞到蕭知雲嘴邊,他神情古怪地問道:是誰把你養的這麼嬌氣? 蕭知雲眨眨眼(張嘴吃):……
22.6萬字8 22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