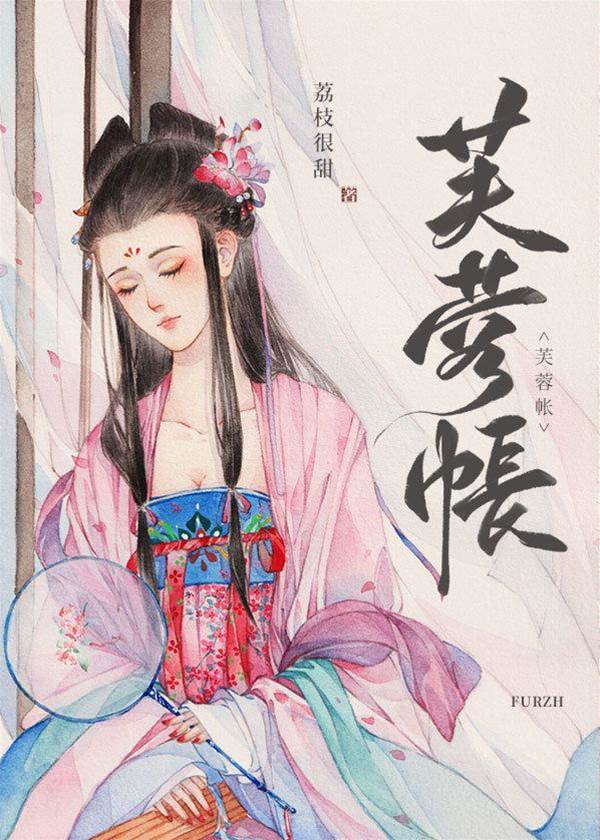《江山萬裡不如你》 第238章
太廟是皇室宗廟,里面供奉的是通朝歷代帝王,且不是居功甚偉,功勛卓著的帝王還沒資格被供奉其中。
因為太廟的特殊地位,所以凡有祭祖典禮,一定會在選在太廟舉行。其他一些祭祀儀式偶爾也會借著太廟的場地舉行,譬如祈雨,譬如祭天。
這次祭天儀式的規模尤其龐大,算是十年一遇的盛況。因此想要找到太廟的位置并不難,隔很遠就能聽見鐘鼎禮樂與儀仗的喧鬧聲傳來。
等抵達太廟后,六兮在廟堂不遠把馬匹藏好,尋了個低矮悄悄翻過墻頭。
好在里面雖然人群熙熙攘攘,宮侍從往來不絕,可是人人都忙于理自己手頭的事務,并沒有人注意到。六兮得以順利地在其中搜尋。
然而,寅肅每個可能居住的房間都找了一個遍,卻始終尋不見寅肅的影子。
更加奇怪地是,太廟正殿雖然已經點上了香火,可味道卻并不是之前在悅書閣聞到的迷香味道。
難道說那群人知道行跡敗,所以臨時改了行方略,不打算在太廟手了?
那他們會去哪?
寅肅又在什麼地方?
或者……他們會不會是已經得手了
這個可怕的推測讓六兮一下子心跳加快,顧不得再小心蔽,沿著正殿臺階鋪著的紅毯快步奔出,神急切而焦慮。
結果未出大門便被守衛攔了下來,冰冷的長戟叉在的頸前。
“你是何人?竟敢攪鬧太廟祭典!”
“我是來找皇上的,你們知道他在哪嗎?”六兮焦急道,“快些多些人手,今天恐怕會有人對他不利!”
“有人要對皇上不利?”兩個守衛冷笑道,“我看想對皇上不利的就是你吧!”
六兮連忙辯解說,“我是皇上…邊的宮。”
Advertisement
“皇上邊的宮怎麼會找不到皇上?我看你就是刺客!”
六兮愣在了原,終于想明白過來。眼前這兩個都是太廟的守兵,只在太廟值,連后宮妃嬪都不認得,又哪里會認得。
眼看著那兩個守衛要按著的肩膀把押去廷杖,一位路過的老太醫終于走過來將人攔下,正是前面送給六兮藥爐的那位王守春。
“兩位且慢手。”
王太醫緩緩說道,“大典之日,兩位何必為難一個宮啊?況且這是祭天盛典,宜當肅穆莊重才是,你二人一的兇氣何統?還要刑杖罰,若見了,沖撞了大典,你們擔待的起嗎?”
說罷目含威瞪視著二人。
兩個守衛面面相覷,只得放了人匆匆走了。
六兮終于松下一口氣,連忙向這位相助的老太醫行禮致謝。謝過后正要急著再上路尋找寅肅,手腕卻突然一,竟是被那位老太醫拉了回去。
六兮快速回手,警惕地問道:“太醫這是何故?”
老太醫把上下掃量一番,試探著問道,“你三天前是不是人拿了一張藥方去太醫局了?”
六兮疑地點了點頭,反問說,“你是……”
“我王守春,是送你藥爐的那個王守春。”
“啊!原來是您!”六兮激之下卻也有疑問,“可是,王太醫,你是怎麼認出我的?”
王太醫面帶微笑,和藹地說道,“適才見兩個守衛為難你,本不想管。可路過的時候卻聞到你上像是有一藥味,卻又不醇正,是熬糊了吧?”
六兮愧地點了點頭。
王太醫笑道,“也怪我,只送你了一套工,卻沒有教你如何使用。哪天有空你可來太醫局一趟,我親自教你。”
“如此,淺淺謝過王太醫。”六兮激不已,連聲道了謝,又問道,“可你我并不相識…太醫如此幫我,我該如何回報?”
Advertisement
王太醫朗聲笑了笑,“舉手之勞而已,倒也不要什麼回報。只是,你那日所寫的方子是從哪本醫書上看來的,不知可否借我一覽吶?”
原來是求書。
那本醫書早已經背的滾瓜爛,隨時可以默寫一本新的出來。六兮自然爽快地答應下來,“太醫客氣了。只要淺淺幫得上,莫說只是借書,就是送您一本又有何妨?”
王太醫喜出外,“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哎?淺淺姑娘怎麼不在皇宮待著,也到太廟來了?”
“呀!糟了!”六兮剛剛談得歡喜,居然差點把正事給忘了。
六兮趕忙問他說,“我是來找皇上的,不知太醫知不知道皇上在何?”
“皇上?”王太醫仰首略一思索,回答說,“往年舉行各類祭祀大典都是下午才開始。現在這個時間的話,皇上多半是在附近那家仙客居的酒樓里歇息著吧。只是那便離得遠些,姑娘有馬車嗎?沒有的話……”
“有的,有的。”六兮終于松下一口氣,再次向太醫道了謝便騎上馬急急往仙客居趕過去了。
此時,寅肅正在仙客居中與幾個近臣飲酒。
太廟里的禮樂實在是吵鬧,而且這時候正是那幫侍從與宮們跑進跑出布置廟堂忙得最厲害的時刻,人多眼雜,總歸是不安全。
在這仙客居四樓的的客房,遠離了下面的囂雜,耳果然清凈多了。寅肅靠著窗,著樓下的人來人往,一杯接著一杯喝得盡興。
旁邊幾個人你看我我看你,卻是大氣也不敢。
以往他們幾個老臣隨著皇上來這的時候,大家可都是有說有笑——皇上出一次皇宮不容易,明正大的出皇宮更是難得,每每皇上在大典前拉他們來這里躲清凈多都有點惡作劇的意味,臉上的表常讓老太傅想起皇上小時候逃課的鬼模樣。
Advertisement
今天可好,從上了酒樓到現在,他一句話也沒說,只自顧自飲著悶酒,像是個想要借著酒水澆滅腹中火氣的竹。
眾大臣也都跟著正襟危坐,生怕一不小心就招來王怒。
整間屋子安靜倒是安靜了,可死氣沉沉,憋得人心里發慌。有幾個甚至已經出了滿腦門的冷汗。
天城府尹悄悄用胳膊肘搗了搗老太傅,低聲說,“皇上這是怎麼了?是誰又惹著他了?”
老太傅翻個白眼,輕嗤一聲,“我哪知道。”
天城府尹不死心,又催促說,“那你問問唄。”
老太傅聞言猶豫良久,仗著自己位高權重,終于敢開口說一句,“皇上,快晌午了,要不要點些菜?”
天城府尹滿臉黑線:是讓你問這個嗎……
寅肅這才回過神來,興致缺缺地揮揮手,“你們吃吧。你們只管吃好喝好,不用管我。”說罷又轉頭去看底下的長街去了。
只是這一看不打,居然在宮外的長街看到了六兮的影。
六兮此刻正騎著一匹快馬再宮外的長街策馬奔騰,驚得一路飛狗跳。
“怎麼在這?”寅肅一下子坐正了子,神嚴肅。
一旁的天城府尹見狀也忙向窗外看一眼,揚眉怒道,“哪來的野婦敢在天城街上騎馬,也不怕踐傷人命!皇上莫驚,下這就去把此婦捉回來。”
“那是朕的寵妃。”寅肅淡淡開口,“去抓吧。”
“這……”天城府尹悻悻住了口。
寅肅則重新調轉了視線去追蹤長街上的倩影,卻不想剛剛探出頭,眼睛便被刺目的閃灼到。
寅肅晃晃腦袋,用手掌了眼睛再次探頭去看,這次終于看清了剛剛反的東西,居然是一支箭的箭頭,小半支箭都從三樓的窗戶里出來,在太底下閃著森然的。
Advertisement
有刺客?
寅肅心中一驚,忙回,可細一想卻又不對,剛剛那支箭明明是在瞄著街上。
不好,他是要殺六兮!
寅肅再次探去看那支箭,箭頭果然是追逐著馬背上的六兮的方向移。
眼看六兮停了馬,形不,正是擊絕佳機會,寅肅不敢耽擱,一個箭步躍上窗戶,大手抓住了窗臺反一腳踢進三樓,正中那人的額頭,他也順勢三樓。
那刺客見事敗,也不敢回頭讓寅肅看到自己的臉,匆匆爬起便往外跑。
寅肅正要去追,胳膊卻一陣刺痛。偏頭一看,才發現原來是那人見一個黑影從四樓落下便把原本瞄向六兮的弓箭抬高了幾分,倉皇放了一箭,結果正中寅肅的左臂。
寅肅疼痛難忍,一下子便跌坐在地上。
原本在四樓的群臣急忙忙奔下來,見寅肅左臂中箭,癱倒在地上,眼看著已經青紫了,出了滿頭的大汗。一時間眾大臣都驚慌失措,“不好,箭上有毒!快太醫!”
“這里這里又不是皇宮,哪來的太醫!”老太傅連忙跑上前去把寅肅摟在懷中,劃破他的袖管一看,紫黑的紋路以傷口為中心像蛛網一般擴散了開來的。
“毒竟如此之烈?快!快備馬,送皇上去醫館!”
等他們抬著寅肅匆匆下樓的時候,六兮也已經停好了馬來到店中。看到寅肅竟是被眾人抬下了樓,臉更是慘白無,六兮腦中轟然炸響:果然還是來晚了嗎?
六兮失神般走上去,抖地喊他的名字,“寅肅……”
寅肅似乎是有所應,勉力睜開眼睛,見是站在面前,便努力扯起笑笑說,“你沒事就好……”
“什麼意思?”六兮不明所以。
那幫老臣也顧不得跟解釋事原委,只重復說一句,“皇上他中了箭,箭上帶毒,需要快快送醫!”
六兮趕忙追問,“可知道是什麼毒?”
“啊呀!這誰能知道!你就不要這麼多話了好嘛!”
這里的都是皇上的近臣,多數都認識六兮。即便是不認識的,剛剛在四樓雅間也聽皇上親口說了寵妃一詞,因此都不敢為難,只催促快些讓開路,不要聒噪,畢竟時間不等人,等毒侵五臟六腑便是神醫親臨也無回天之力了。
猜你喜歡
-
完結782 章

軟軟嬌妻馭惡夫
惡霸宋彪,是十里八鄉人人提之色變的混賬無賴。 “小娘子,等著老子去下聘娶你。” 顏卿,是舉人家賢惠淑良的姑娘,不管是模樣還是性子,誰見了都要誇上一聲好。 卻是被這個宋惡霸盯上了,眼看著是羔羊入虎口,怕是要被吃得骨頭渣都不剩。 顏小娘子抬起眼,水盈盈的鳳眼迎上男人一張黢黑大糙臉,“好。”
128.7萬字8 57909 -
完結1187 章

旺夫命:拐個夫君熱炕頭
沈九娘穿越了,還嫁了一個活一天少倆半晌的藥簍子,自己這是隨時可能做寡婦的節奏啊。不過好在一家人和和睦睦,婆婆溫柔,小叔可愛,相公又是個極品貼心暖男,日子倒也過得去。家里一貧如洗,她能賺,她一個農大高材生收拾點兒莊稼還不是小菜一碟;有極品親戚…
210.7萬字7.91 53916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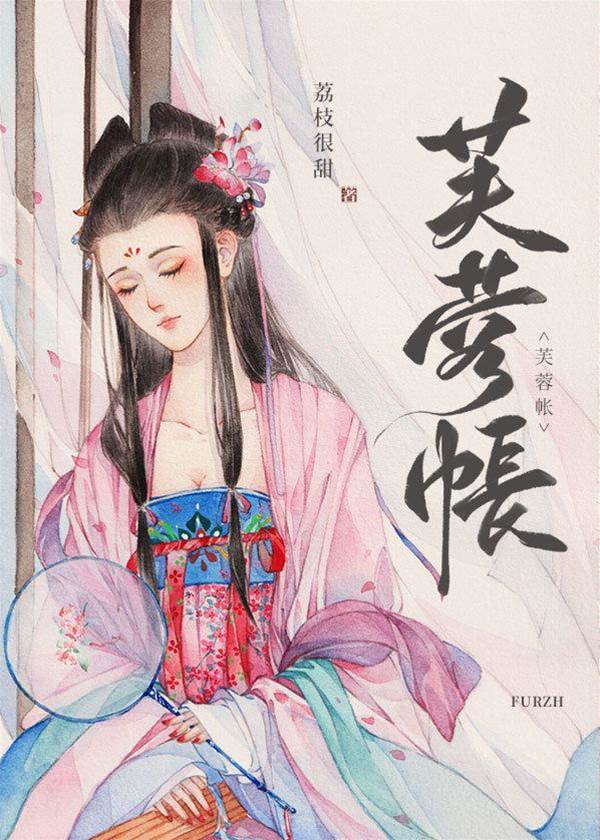
芙蓉帳
文案:錦州商戶沈家有一女,長得國色天香,如出水芙蓉。偏偏命不好,被賣進了京都花地——花想樓。石媽媽調了個把月,沈時葶不依,最后被下了藥酒,送入房中。房里的人乃國公府庶子,惡名昭彰。她跌跌撞撞推門而出,求了不該求的人。只見陸九霄垂眸,唇角漾起一抹笑,蹲下身子,輕輕捏住姑娘的下巴。“想跟他,還是跟我?”后來外頭都傳,永定侯世子風流京都,最后還不是栽了。陸九霄不以為意,撿起床下的藕粉色褻衣,似笑非笑地倚在芙蓉帳內。嘖。何止是栽,他能死在她身上。-陸九霄的狐朋狗友都知道,這位浪上天的世子爺有三個“不”...
37.3萬字8 286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