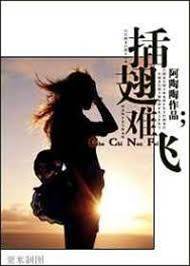《禮物》 第103章 第 103 章 他的小秋,……
第103章 第 103 章 他的小秋,……
關系公開後, 梁曼秋和戴柯習慣了地下,在家沒有過分親昵,跟當初戴四海和阿蓮在一起也一樣。
這是年人該有的禮儀。
一些小打小鬧總算放開了, 戴柯可以明正大抱摔梁曼秋, 一起倒在沙發上, 哈哈大笑。
梁曼秋通常在下面,笑出淚喊救命,戴柯咬著下問服不服。
帶魚呆呆看一會,抓住他的玩車屁顛顛跑進主臥,“媽媽,姐姐喊救命。”
阿蓮:“姐姐為什麽喊救命?”
帶魚:“哥哥把姐姐在沙發上, 姐姐喊救命。”
阿蓮哼笑一聲, “哥哥和姐姐鬧著玩呢。”
帶魚:“可是姐姐喊救命!”
阿蓮:“你去救姐姐吧。”
帶魚:“我不敢,哥哥好可怕。”
類似投訴層出不窮,“媽媽, 哥哥發瘋了”“媽媽, 姐姐踩哥哥大,哥哥哎喲哎喲”, 阿蓮有時不耐煩,“哎呀, 弟弟你玩你的,不要管他們。”
更多的是, “媽~媽!哥哥姐姐出去玩又不帶我!”
只要梁曼秋和戴柯在家, 帶魚只有被嫌棄的份。
國慶前夕,梁曼秋繃了大半年,終于收到捷報,功保研北大法學院。
回海城找了一份律所實習生的工作, 開始驗朝九晚五的生活。工作日一個人在碧林鴻庭,周末回翡翠灣看帶魚他們。
戴柯新警培訓封閉三個月,一直到2020年春節前才見上面。
這幾年聚離多,跟戴柯最近的距離在寒暑假,天天黏一起,平常最多一周見上一次。梁曼秋已經記不起一年有360天朝夕相伴的日子。
以後他們各自出差,還會有各種措手不及的分別。
過新年,戴柯進第二個本命年,梁曼秋特地準備了新年禮。
Advertisement
“是什麽?”戴柯翻看掌厚,比掌大一圈的禮盒,“巧克力?”
梁曼秋:“還不是人節。”
再說,人節的巧克力應該他送給。
戴柯嗅到不祥的氣息,“梁曼秋,別告訴我你送了紅衩。”
梁曼秋瞪圓了雙眼,“哥哥好聰明,怎麽猜到的?”
戴柯說:“禮我收下,但是我不會穿。”
梁曼秋搖他胳膊,“哥哥!你穿吧,本命年穿紅衩可以逢兇化吉,平安順利。”
戴柯:“拉倒,兇神又看不到我衩。”
梁曼秋好一瞬才轉過彎,“哎呀,就圖一個好彩頭。穿嘛哥哥,穿吧。”
戴柯恍然想起初中同學的評價,他妹說話真的有點嗲。
不過,他就吃這一口。
大D妹的語腐蝕他的鐵漢意志,本就不堅定的心容易春風漾。
“穿可以,我有個條件。”
梁曼秋:“你說。”
戴柯:“我穿上去,你給我下來。”
梁曼秋剛想說,豈不是等于白穿,轉念反應過來,啞了啞。
戴柯:“不?”
“行吧。”
梁曼秋不敢想象,漲得比衩還紅的東西突然彈出來,要是湊太近,還會打到臉上。
戴柯不信命,偶爾無聊地想過,第一個本命年時被老戴著穿紅衩,才走大運遇見梁曼秋。
等戴柯穿上紅衩,他們沒做功,相擁笑倒在一起。
太土了。
誰能看到大紅還能起反應。
哪怕它是CK。
除非紅移到梁曼秋上,越越好。
戴柯以牙還牙,“等你本命年,我也要送你一套。”
梁曼秋嘀咕:“哥哥,別以為我不知道,你一定又送.趣.。”
而且是沒罩.杯的款式,只有一幅花邊鋼托,把該強調的部分托得越發拔,圓的圓,尖的尖,兩紅越發迷人眼,恨不得咬上一口。
Advertisement
戴柯:“送刑。”
梁曼秋立刻想到大紅的綁帶,勒在白皙上,對比鮮明,忌的塊催發破壞。
戴柯最不缺乏這種東西。
“下流。”梁曼秋輕輕笑罵,有一點不好意思,又有一點好奇。
戴柯沒反駁,用肢語言呈現給,一直到離別前夕。
梁曼秋點了兩次行李箱,確認東西沒有。
戴柯沒那麽嚴謹,“了在北京買,還有首都沒有的東西麽?”
“哥哥。”
“說。”
梁曼秋咕噥:“我說首都沒有哥哥。”
“我跟你說東西。”戴柯沒掉進編織的文字陷阱,打了一下屁。
梁曼秋:“知道你不是啦。”
戴柯坐床沿,拉過趴他大上,掀拉一氣呵,往溜屁扇了一掌。
聲響清脆,伴著聲息,分外催。
戴柯將翻面,正經摟坐上。
離別在即,梁曼秋和戴柯看著對方時常恍惚,好像航班提醒是假的,收拾整齊的行李箱也是幻覺。
他們還會像過去有一個暑假,天天晚上膩在碧林鴻庭的舊家。
梁曼秋指尖劃過他線條冷的臉,“哥哥,你在想什麽?”
戴柯:“沒想什麽。”
梁曼秋開玩笑:“還以為你又想下流的東西。”
話畢,知錯了,戴柯的吻異常溫幹淨,落在的,脈搏跳的側頸,平直的鎖骨。
只是有一點紮。
梁曼秋輕聲笑:“哥哥,你的胡子怎麽那麽紮了?”
戴柯拉下睡寬闊的領口,含住空檔的,含糊應聲:“你男人24歲,不是18歲了。”
他們的關系蛻變六年了,年以後,時間對他們的雕琢日漸變小,不再像十二三歲時,彼此能看到對方長大的跡象。
時間又給他們留下寶貴的驗,彼此日漸悉的,每次不同的歡愉,還有嬉笑打鬧。
Advertisement
帶刺的吻讓接越發深刻。
梁曼秋戴柯日漸的嫻與沉穩。褪去,越發直白面對自己的念,打開心接納他。
嵌合的一瞬,戴柯溫耗盡,又回歸原始的瘋狂。
他吻,咬,。刺麻從的,落到口。
戴柯吸得用力,要把沒有的香,盡數吸出來似的。
痛讓覺變得敏銳,一一寸的快意瞬間放大,梁曼秋覺下一瞬自己就能癱了。
梁曼秋喜歡戴柯正面抱,可以偶爾看他的表。平時漫不經心的男人,閉著眼,為沉醉和用勁,又迷人,令安心,也勾走的魂。
“哥哥。”
梁曼秋附在戴柯耳邊,聲音像拼死拼活跑完800米。
戴柯含含糊糊的一個嗯,像應了,更像故意勾引。
搗水和拍掌的聲響異常響亮,混進談裏,銷蝕了對話的邏輯。
前言不搭後語也好,戛然而止也好,不值得深究,每一句話都是廢話,僅剩一個目的。
讓他用力幹。
戴柯學會了控制速度,慢悠悠問:“舒服嗎?”
梁曼秋沒能回答上來,聲音被.碎了,只剩下斷斷續續的單音節。
戴柯牢牢勾住,先跪著抱起,再站到床邊。
梁曼秋的重心隨著戴柯搖晃、騰空,不由抓穩他結實細膩的肱二頭,倒一口氣,怕下來,也怕他出來。
戴柯抄著梁曼秋的膝彎,握住的腋下,高和力懸殊,他將穩穩釘在半空,不斷擡腰進擊。
擔心的落,哪一種都沒出現,他的力氣和長度不允許意外。
空調冷氣沒法阻擋熱,他們都沁出一層細的汗,最親的地方也汗涔涔黏糊糊的。
梁曼秋擔憂:“哥哥,是不是、了?”
戴柯暫停拉出半截,頭還埋在裏面,低頭看。狂的發掛滿白粒粒,套子口也糊了一圈,畫面靡豔,不堪目。
Advertisement
他說:“老子還沒赦,都他媽你的。”
“啊?”梁曼秋沒法思考,又被撞暈了。
“不信你,”戴柯說,放慢速度,隨時等著橫一手,“老婆,一下。”
戴柯每次總能飆出新鮮又恥的廢話,梁曼秋總比不過他,紅著臉,“知、知道了。”
戴柯力過人,地盤穩實,再次沖碎的聲音與鼻息。
戴柯像一棵桉樹,梁曼秋了盤著樹幹的考拉,狂風暴雨裏,搖晃的只有考拉和樹冠,樹依舊穩穩紮在地裏。
他們往肢語言裏澆灌意,在悉裏發掘新鮮,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用深刻的方式銘記對方。
次日一早,梁曼秋的航班下午1點起飛,戴四海把車開來碧林鴻庭。
阿蓮:“真不要我們一起去?”
戴柯:“不要。”
戴四海:“這車能坐得下,五座呢,剛好我們一家五口,換SUV不就是等這一天麽?”
戴柯:“你們去一個一個挨著哭,要哭瞎。”
梁曼秋癟癟,“我才沒哭。”
戴柯把行李箱挪好位置,關上尾箱門,“你現在就記住這句話。”
梁曼秋噘:“就不哭。”
戴柯:“誰哭是小狗。”
帶魚:“姐姐你什麽時候回家?”
梁曼秋猶豫:“姐姐可能——”
阿蓮:“姐姐國慶就回來了。”
帶魚:“啊?國慶啊,好久啊,你怎麽去那麽久?”
小孩還沒時間概念,不是下一秒都覺得太久太久。大人接了離別,還不習慣離別,不敢輕易說久。分別時的任何展都抵不過這一刻的悲傷。
梁曼秋出笑,也不小心出淚意,“國慶很快的,弟弟過四個周末就到了。”
帶魚:“好吧。”
“走了。”戴柯發SUV,後視鏡裏的二婚夫妻和他們的小孩越來越小,直至拐過一個街角,消失不見。
戴柯在旁忽地嚯一聲,“有人要汪汪了。”
梁曼秋:“臭哥哥,專心開車。”
海城機場轉瞬抵達。
戴柯停好車,推著梁曼秋的行李箱,和手拉手走到安檢口。
“進去吧。”該說的嘮叨一路,戴柯沒再廢話,給了屁一記悉的助推起飛,只是比年時期力氣輕了許多。
“那我走咯。”梁曼秋的手夾著登機牌,晃了晃。
戴柯:“滾吧。”
梁曼秋沒,遲疑片刻,“哥,要不你先走。”
海城今年的夏天格外短暫,戴柯這樣線條的人也嗅到秋的寂寥。
他毫不猶豫轉,再慢一步就走不掉似的。
梁曼秋看著戴柯頎長的背影,不知哪年褪去潦草的形象,姿拔,步態從容穩健,一看就是過訓練的。
這個人從來不曾跟表白,不說喜歡也不說,若說憾,梁曼秋不能說沒有。沒有的東西太多,沒有正常的父母,沒有安定的年,擁有了戴柯,不敢太貪心。
不敢斷定的全部含義,能肯定只有一項,的語言很多。戴柯的眼神會說,肢作會說,唯獨不會說。
要替他們說出來。
“哥——!”梁曼秋撒開行李箱拉桿,朝著戴柯飛奔而來。
戴柯回頭,轉下意識走近兩步,稍稍彎腰接起,托住屁,摟後背。
這是他見過最熱烈直白的表達。
梁曼秋坐穩在他手上,捧著他的臉,直視那雙深邃的眼睛,“哥哥,你一定要等我回家,一定一定要等我。”
戴柯空打一下屁,“癡線,敢不按時回家我就出去抓你。”
“還有——”
梁曼秋抱住他的肩膀,腦袋埋進他的肩窩。耳鬢廝磨的溫暖裏,一道水意過他的側頸,溜進領,涼得分外明顯。
“戴柯,我你,很很你。”
這是梁曼秋第二次直呼其名。
第一次是高中時威脅戴柯不準朋友。
從不安的懷疑,到安心的肯定,他們磕磕絆絆走過了很多年。
“梁曼秋,老子當然知道。”
戴柯的手繃出暴凸的青筋,摟得越發實,也終于吃了一大口“眼淚拌空氣”的味道。
然後,梁曼秋掙紮了一下,從頭上下來,拉著行李箱頭也不回紮進安檢口。
一個多小時後,戴柯把SUV停在路邊,降下車窗。
飛往首都機場航班準時起飛,機上海城航空的紅祥雲標志越發小巧、模糊。
他的小秋,陪了他十二年,乘著秋風飛向了更高遠的天空。
—正文完—
猜你喜歡
-
完結1325 章

致命偏寵
黎家團寵的小千金黎俏,被退婚了。 黎家人揭竿而起,全城討伐,誓要對方好看。 * 後來,黎俏偶遇退婚男的大哥。 有人說:他是南洋最神秘的男人,姓商,名郁,字少衍; 也有人說:他傲睨萬物,且偏執成性,是南洋地下霸主,不可招惹。 綿綿細雨中,黎俏望著殺伐野性的男人,淺淺一笑:「你好,我是黎俏。」 做不成夫妻,那就做你長嫂。 * 幾個月後,街頭相遇,退婚男對黎俏冷嘲熱諷:「你跟蹤我?對我還沒死心?」 身後一道凌厲的口吻夾著冽風傳來,「對你大嫂客氣點!」 自此,南洋這座城,風風雨雨中只剩最後一則傳言—— 偏執成性的南洋霸主,有一個心尖小祖宗,她姓黎,名俏,字祖宗!
209.6萬字8.18 109319 -
連載3440 章

渣女圖鑒
某當紅頂流在接受娛記採訪時,被提及感情問題當紅炸子雞說他永遠也忘不了他的前女友,當問道兩人因何分手時,他說因為他給他的前女友買了一個抹茶味的冰激凌某跨國集團總裁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被調侃是鑽石王老五鑽石王老五深情款款的說,他在等他的前女友回頭,記者驚奇,當問道分手原因時,他說因為分手那天約會他穿了一件駝色的大衣某影帝在新電影發布會上,被記者追問,何時與某影后公開戀情實力派影帝語氣嚴肅,態度冷漠的澄清,自己與某影后不熟,心中只有前女友一人,請媒體不要造謠,以免前女友誤會某電競大神,在全球世界杯上奪冠,舉著獎杯,當著全世界人民的面,向前女友表白某賽車手,在…………後來,有心人通過各種蛛絲馬跡,發現這些人的前女友,居然是同一個人!世界震驚了!
412.1萬字8 38945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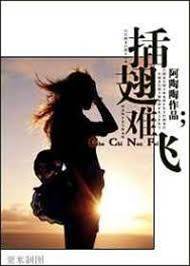
插翅難飛
美麗少女爲了逃脫人販的手心,不得不跟陰狠毒辣的陌生少年定下終生不離開他的魔鬼契約。 陰狠少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孩,卻不知道怎樣才能讓女孩全心全意的隻陪著他。 原本他只是一個瘋子,後來爲了她,他還成了一個傻子。
23.5萬字8 17235 -
完結521 章

在偏執大佬懷里打滾
孟清寧前世在和衛決的訂婚宴當眾宣布非傅競澤不嫁。 多年后衛決成了豪門新貴,而她卻被未婚夫伙同表妹陷害慘死。 一朝重生 孟清寧依舊是高高在上的孟大小姐 而衛決卻是白手起家,備受奚落的小公司合伙人。 她知道他未來會是這個行業的大佬。 可這一世孟清寧只想腳踩渣男渣女,照顧父母,淡情薄愛,再也不信男人 可漸漸地,她好像被衛決寵上了天。 “當初不是說好,不談情只合作的麼?” “嗯?”大佬嗓音低沉:“說反了?只談情,不合作。”
91.8萬字8 23504 -
完結377 章
夜夜狂歡,病嬌大佬要寵愛
“哥哥,疼!”伊苡茉窩在厲昱珩懷里,小臉上滿是淚痕。厲昱珩眼底滿是心疼,“乖,再忍一下,就好了。”他手中拿著酒精棉,看著她腿上的傷口,恨不得受傷的是他自己。她是他撿來的寶貝,從此他的世界里只有她。他,陰鷙、冷漠、狠戾。遇到她,寵她、慣她,令人發指。 ...
50.9萬字8 128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