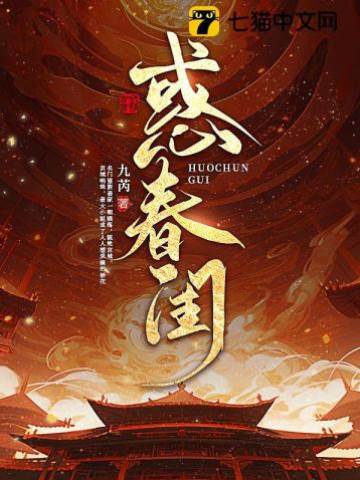《鳳鳴朝》 第26章
第26章
誰也沒想到, 第一個響應出繳助軍錢的世家會是郗家。
當揚州牧郗尹在朝堂上表態後,莫說大臣們,連庾太後也愣了一愣:“郗卿的意思是, 郗家願意以三百二十萬錢作軍資, 支持北伐?”
“自然。”郗尹慷慨陳詞, “複中州乃舉國大計, 匹夫匹婦尚且有責, 臣作為廟臣, 更要慷慨解囊。”
其實他心裏疼不已,天可憐見,這錢不是他想出,是他那兒子非要讓他出啊。
郗尹材資庸常,聽兒子的聽習慣了,昨日在家見郗符言之鑿鑿,似有他的道理,便也忍痛舍財了。
謝瀾安在太後側,瞥睫向郗符看去。
郗符老神在在地迎上探究的目。
就在二人視線一將分時, 太極殿外黃門侍郎唱報:“大司馬覲見陛下!”
謝瀾安心思微,指尖下意識輕敲玉帶, 京口離金陵不過百裏餘, 順水路南下半日可至, 他來得好快。
大司馬常年據守京口, 此次上京未提前奏報臺省, 打了殿中文武一個措手不及。帝也是愣了一愣,才道:“傳。”
隨著黃門侍郎應聲通傳,一雙烏金頭軍履踏政殿。
褚嘯崖披鎖子甲,腰掛秋霜劍, 從中軸道步步近前,以軍禮單膝跪拜,聲如洪鐘:“臣參見陛下,參見太後娘娘。”
早在先帝朝,褚嘯崖便獲得了劍履上殿,朝不趨的殊榮,他腰間那柄斬殺頭顱無數的屠鯢,雖未出鞘,已出兇殺森寒之氣。
帝命平,褚嘯崖起,魁梧碩實的軀仿佛一座黑塔崛起,帶鎧甲作響。
殿中一時針落可聞。
以氣士之言,這一國有龍氣,一軍有勝氣,一人之亦有氣象凝聚。褚嘯崖的兇戾氣勝了左右文武,他傲然一笑,向皇帝上陳北伐之決心,再述必勝之誓念,而後,那雙鷹隼般的利眼,狩獵般盯住垂帷之後。
Advertisement
人上朝,太後那半老嫗婆不算,他還是第一次看見。
只見這謝家小娘子長纖直,素腰一抹,頭戴獬豸冠,腰纏絳綾帶,真是好抖擻好神氣。
而那點屬于子的,全凝在冷若冰霜的臉上的那對秋水眸底。
神越冷,一對明眸便亮得越勾人。褚嘯崖閱無數,還從未見過這種剛并濟的樣式。
若非庾家二小姐致書提醒,他險些錯過。
“謝娘子仕右遷,褚某不曾一賀。”
褚嘯崖眼睛豪不避忌地在謝瀾安腰肢間流連,“只可惜謝荊州已回荊樊,否則卻可與之痛飲一番。”
謝瀾安眸底霜微凝,卻是一笑,聲如泠弦:“要飲酒何難,大司馬不妨與家叔相約于水,以胡人酒,豈不快哉?”
褚嘯崖哈哈大笑:“謝氏的氣度,果真個個不凡。有小娘子這句話,褚某便是想不大捷都難了!”
郗符聽見大司馬裏不甚尊重的稱呼,倏地皺起眉。
下朝後,他與謝瀾安一道出殿。
謝瀾安斜眉瞧他一眼,“太打西邊出來了?”
說的是郗家出錢的事。此事并非郗符心來,他做得了郗氏主,自然不缺敏銳的嗅覺。謝瀾安不惜得罪世家、反水皇帝也要向太後投誠,按理來說,便該傍住這個靠山,可他又留意到,謝瀾安調用了上一次北伐的戶部檔,而且何家一個末枝子弟,又在謝府出頻繁,這半個月幹脆住在謝府不出來了——他便奇怪,謝瀾安為何要用不起眼的何羨?
戶部是何興瓊的天下,想往裏人想都不用想,除非……是姓何的自己人。
可若真如他所料,謝瀾安既對太後忠心耿耿,為何又要多此一舉?
郗符暫時想不通,只是他了解謝瀾安下棋的路子,從來不落閑子。
Advertisement
三百萬錢換算白銀,也就是幾萬兩,對郗家而言不值一提,他便只當投石問路,押一注孤注。
搏大贏大,說不定有意外收獲。
他上冷冰冰:“我樂意。”
謝瀾安夏日換了把趁手的紫竹扇,合在掌心把玩,潤涼沁,玩味念叨著:“三百二十萬,有零有整,虧你想得出來,無不無聊啊?”
謝家出了三百萬錢,郗家就要出三百二十萬一頭。
可再無聊也沒有郗符日讓人盯著謝府門口,看謝瀾安都在和誰家士傑來往更無聊。
“我樂意。”郗符被引出了火氣,反相譏,“倒是謝家主,邊來往的不是樂癡文樂山,便是算呆子何夢仙,真沒人可用了嗎?”
謝瀾安才覺出哪來一酸味,忽聽後響起一道威鷙之聲:“謝娘子請留步。”
謝瀾安眼神清冷,掉轉扇柄收袖袋,轉過,一臉平常之:“大司馬,有何見教?”
郗符收斂神,注視著走近的褚嘯崖,下意識往謝瀾安前站了站。
褚嘯崖笑笑地凝視謝瀾安,子白勝雪,之下,更有凝脂剝荔之妍容。
“今日未見謝荊州,褚某實引為憾。好在謝娘子承繼家風,聞聽北伐一事,是娘子一力促?褚某于于理都該訂個筵席,請謝娘子賞如何?”
以二人份,他如此相邀實在無禮。
可他是掌管天下兵馬的大司馬,權勢異人,既然連出宮城都等不及,在殿前便將人堵了,就是沒給人拒絕的機會。
郗符強忍著一口氣,作笑道:“巧了,我正要請謝直指去長樂肆吃酒賞荷呢,席都訂下了。偏大司馬一步,在此給將軍賠個禮。”
“正是。”謝瀾安順話道,“赴大司馬的宴豈能隨意,我這也不合適。過兩日,過兩日由我做東宴請大司馬,必不負大司馬盛。”
Advertisement
褚嘯崖的目在這兩個臭未幹的年輕人臉上逡巡幾圈,眉角睨人,負手沉笑。
“我就喜看娘子這一。北府軍機繁忙,今日回京述職,明日我便要回去,不似郗主日日在金陵,吃酒不差這一日。”
郗符聽他說話不幹淨,目冷了下去,“你莫——”
謝瀾安扇點在他手臂上,沒讓郗符說下去。
眼珠輕轉,轉眼難全消,展扇一笑:“好啊,那我便卻之不恭了。宴席您請,地方我挑,如何?”
·
將近辰時末,郗符派遣的長隨奔至謝府報信。
阮厚雄去了驍騎營校場,阮伏鯨和謝策在府中,聞聽大司馬下朝後邀走了謝瀾安,臉立變。
玄白一聽就急了,跌手道:“主子邊只有允霜一個,樂游原湖心畫舫?怎麽找了這麽個四不靠的地兒,姓褚的是何居心?不行,我得去!”
謝策從最初的震驚回過神來,按住他,神沉穩:“你不可面。你如今對外面說的是傷未好全,若了馬腳,會給瀾安多事。方才沒聽郗家仆從說嗎,地方是瀾安選的,有算,不會自絕地,再說邊還有肖浪帶人跟著,褚嘯崖不敢來。府中不要,我去接人。”
阮伏鯨隨著他話音起,臉沉,“我與世兄同去。”
玄白急得無法,還在懊惱:“昨日肖浪稟報主子,說發現庾神從庾家的郵驛送了封信去北府,向來熱衷挑唆,也不知和今日的事有沒有關系。”
廳外是聞訊趕過來的文良玉和胤奚,胤奚恰好聽到這一句,腳步滯住。
耀盛的從他高的鼻梁灑下,卻宛如兜頭澆下的一盆冰。
他眼瞼下渡出兩片淺淡影,讓人看不清神。
文良玉聽說前因後果後,哎呀一聲,“那褚大司馬之前不是——”
Advertisement
話到一半,他省覺此為謝氏長輩之諱,忙收住口。胤奚看向他。
文良玉沒說完的話,謝策自然清楚,這也正是他擔心的原因。
他的姑母謝晏冬和王家三郎君和離後,褚嘯崖傾慕姑母的才名與出,曾向謝府求娶,還大言不慚地說不介意姑母是二嫁之。
會稽王尚且為拒婚,謝逸夏自然庇護妹妹,想連儒雅洵的王郎都看不上,與一個殘暴武夫,又豈有共同話題。謝氏的底氣是荊州十萬水師,比之北府不惶多讓,此事于是未。
可也讓謝家惡心了許久。
“我和你們一道去!”文良玉看著要走的兩人,連忙說。
胤奚聲音有些:“我也去。”
謝策心思微轉,迅速決斷:“不行。人數太多顯得煞有介事,知道哪類人最喜激將?豺豹!越是圍越激發,原本無事的,看到我們如此張保護瀾安,反而會引發他挑戰之興。對瀾安不妥。”
文良玉聽話,看著謝策與阮伏鯨聯袂而出,二人馬車都不等,一人一匹快馬向樂游原騁去。
被留在原地的胤奚,瞳仁黝黑,面無表地收掌心。
·
樂游原風張日,楊柳依依。
一艘繪彩的畫船,悠悠飄在河心。允霜在雅廂中倒酒。
從上了船,褚嘯崖的目就沒離過謝瀾安的臉。他笑著說:
“從前見娘子玉樹臨風,可怎麽也想不到會是個子。謝家風水真好,出了你姑姑和你這兩朵并蓮。”
允霜眼中的殺機一剎迸現。
可在一刀一劍從山海裏爬出來的梟雄,可不在意這點小意思。
見謝瀾安不語,褚嘯崖又略笑了笑:“我是人,不懂什麽賦比興,若說錯了,小娘子可別見怪。”
謝瀾安玉指拈箸,夾了片糖藕口,慢條斯理品著滋味,說:“大司馬英雄本,不見怪。”
褚嘯崖生相兇悍,那些怯怯的孩第一次見他沒有不怕的,可這個娘孤坐在他對面,還敢吃喝,膽氣果然不同常人!
褚嘯崖目含,起了興致,挲著酒杯說:“娘子選的這個地方好,無人打攪,適合暢談。就是悶熱了些,娘子不如摘冠,松快松快?”
“不敢在大司馬面前不修邊幅。”
謝瀾安極穩,這才擡眸,輕睇那張一臉橫的糙面,“這地方自然好,隔牆無耳,否則怎與大司馬談公事?”
“公事?”褚嘯崖微微皺眉。
“自然哪。”謝瀾安落箸,眸盈盈,“太後娘娘知大司馬英勇無匹,用人不忌,特命下請大司馬提攜提攜後輩。”
褚嘯崖放下酒杯,似笑非笑地看著,“提攜誰?”
謝瀾安隨口就來:“庾家的兩名嫡系子弟,想立些軍功,此次想隨大司馬一同出征,還請大司馬費心安排個職位。”
褚嘯崖咂出點味道來,怪道如此痛快地來赴宴,原來在這兒等著自己呢。
庾太後,呵,把京畿巡防的兵權攥在手裏還不夠,還想把手到軍中。
這哪裏是庾家子弟想立戰功,分明是太後派來監軍的。
褚嘯崖平生最恨人掣肘,當下冷了神:“軍中無閑職,只怕不妥。”
謝瀾安氣定神閑地出一只手,張開五指,又翻覆一下。
低聲音:“太後知大司馬為難,就怕大司馬多心,所以庾家願出這個數,來給門下的子弟鋪鋪路。”
兩手一翻,便是一千萬錢,折合銀子便是八萬兩。褚嘯崖了心,明知太後是打一個掌給一個甜棗,也難免躊躇起來。
那可是整整八萬兩,而且不走公賬,直接他的私庫!
原來太後也怕塞了人過來被他整治,所以這錢,一是給雙方的臺階,二是那兩名庾氏子弟的買命錢。看樣子,太後是鐵了心要沾一沾軍政了。
褚嘯崖心想:人收過來,放在他眼皮子底下,還不是隨他調配,白白便有八萬兩銀子庫,何樂而不為?
他面上不顯,故作沉片刻,方應允下來。
謝瀾安就等他點頭,轉頭:“允霜,泊船靠岸。”
褚嘯崖一愣,氣笑,聲戛氣道:“謝娘子這過河拆橋未免太快了,公事談完,私事還未談呢。”
“我哪裏敢因私廢公呢?”謝瀾安輕道,劍眉英目間竟出幾分純稚無辜的氣質,讓人近不得遠不得,“太後還在等我複命。”
褚嘯崖看得怔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69 章
重生之妖嬈毒後
這個是一個被渣男和渣女算計之後,奮起反擊,報復過後,卻意外重生,活出錦繡人生,收穫真愛的故事。蕭家嫡女,風華絕代,妖嬈嫵媚,癡戀太子。二人郎才女貌,乃是天作之合。十年夫妻,蕭紫語殫精極慮,傾盡蕭家一切,輔佐夫君,清除了一切障礙,終於登上了皇位。卻不料十年夫妻,十年恩愛,只是一場笑話。只是寧負天下人
407萬字8 84134 -
完結141 章

替嫁以后
瑩月出嫁了。 哦,錯了,是替嫁。 圍繞著她的替嫁,心計與心機開始輪番登場, 作為一群聰明人里唯一的一只小白兔, 瑩月安坐在宅斗界的底層,略捉急。
43.2萬字8.09 33001 -
完結816 章

回眸醫笑,朕的皇后惹不起
原本是現代一名好好的外科醫生,怎料穿到了一本古言書中,還好死不死的成了女主!哼哼,我可不是書里那個有受虐傾向的無能傻白甜,既然成了主角,那就掀他個天翻地覆吧!只是……這個帝王貌似對我有些別樣的“寵”啊!…
146.8萬字8 9032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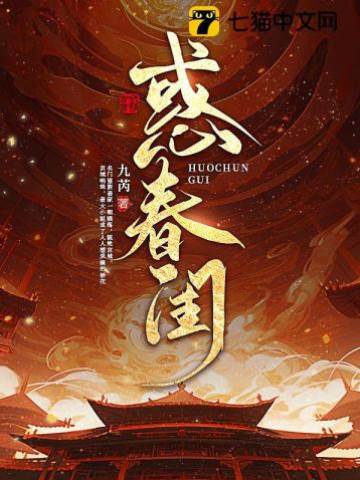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
完結256 章

誘妻為寵/溺寵為妻
蘇語凝成親那日,鑼鼓喧天。 謝予安目送着大紅花轎擡着她進了大哥的院子,他竭力忽視着心口的窒悶,一遍遍地告訴自己——解脫了。 那個連他名字都叫不清楚的傻子,以後再也不會糾纏於他了。 直到有一日,他看到小傻子依偎在他大哥懷裏,羞赧細語道:“喜歡夫君。” 謝予安徹底繃斷了理智,她怎麼會懂什麼叫喜歡!她只是個傻子! 他終於後悔了,懷着卑劣、萬劫不復的心思,小心翼翼幾近哀求地喚她,妄想她能再如從前一般對他。 然而,從前那個時時追着他身後的小傻子,卻再也不肯施捨他一眼。 **** 人人都道蘇語凝是癡兒,可在謝蘊清眼中,她只是純稚的如同一張白紙。 而這張紙上該有什麼,皆由他說了算。 謝蘊清:“乖,叫夫君。” 蘇語凝懵懂的看着他,甜甜開口:“夫君。”
40.4萬字8.18 44669 -
連載2247 章

乖,叫皇叔
【重生】【高度甜寵】【男強女強】【雙向暗戀】重生后的虞清歡覺得,埋頭苦干不如抱人大腿,第一次見到長孫燾,她就擲地有聲地宣誓:“我要做你心尖尖上的人。” 大秦最有權勢的王不屑:“做本王的女人,要配得上本王才行。” 結果,虞清歡還沒勾勾小指頭,某人就把她寵成京城里最囂張的王妃,連皇后都要忌憚三分。 虞清歡:夫君,虞家的人欺負我。 長孫燾:虞相,我們談談。 虞清歡:夫君,皇后娘娘兇我。 長孫燾:皇嫂,你放肆了。 虞清歡:夫君,有人覬覦你的美色。 長孫燾:小歡歡乖,讓本王進屋給你跪釘子。
358.4萬字8 58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