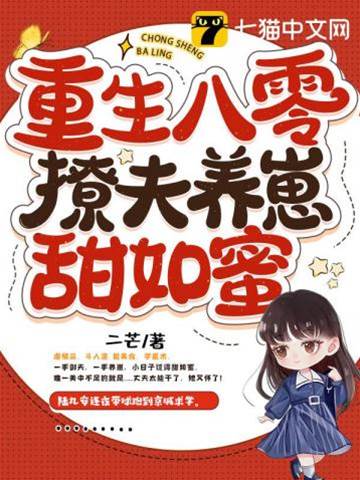《離婚后,顧總跪著求復合》 第369章 有良心的資本家
李導了小手手,有些糾結:“這麼好的場地,可是難找啊。還有,顧氏剛剛跟我們簽了一個廣告的合約呢。顧氏的新產品,等于是在我們的電視劇中首發。這是多大的榮耀啊,之念你要是能忍,就稍微忍忍。要不,咱還是忍到劇播完?”
蘇之念聽得忍無可忍了,咬牙切齒的說道:“老師!”
李導頓時輕咳了一聲:“我就是這麼一提。你要是實在不愿意,那就算了。但撐過這幾天,應該還是可以的吧?”
蘇之念直接說道:“我和顧景淵,昨天就鬧翻了。他既然沒有收回場地,也沒有撤回合同,顯然,他并不在意這些小事。老師你以后,不要再在他面前提起我就行了。”
昨天……就鬧翻了?
這一次。
茫然的換了李導。
可是。
昨天顧景淵離開之后,還主聯系了他啊?
知道蘇之念創作不順之后,還主提出讓參觀顧氏啊?
Advertisement
這是鬧翻?
現在年輕人的世界,這麼復雜了?
李導還要再問。
蘇之念已經抿著,一副不想談的樣子。
李導只能下了一肚子的好奇心,然后,一個人在那里揣測著這兩人到底是什麼況,越是揣測,越是抓心撓肺。
不過。
蘇之念顯然沒有給他解的意思。
他也只能自己憋著了。
很快到了公司。
“之念,你去忙劇本吧。拍攝的事,先不用你了。”李導說道。
蘇之念點頭應了下來。
知道輕重,現在這況,劇本是重中之重,如果不能把劇本寫出來,整個劇組的進度都要停滯。
而且。
顧氏提供場地,也不可能無限期提供。
兩方說好的,是半個月。
這半個月,得拍好所有虞策工作上的戲份,算下來,時間還是迫的。
蘇之念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就開始琢磨了起來。
但是。
這個新品的概念,是顧景淵提出來的。
Advertisement
蘇之念對于這個技,沒有任何了解,也沒有見過任何相關的事。
要讓憑空描述出來,著實是有些艱難。
抓掉了幾寶貴的頭發后。
蘇之念看著空空如也的本子,拿著保溫杯,出門去灌水。
外頭。
李導和其他人都在專心拍戲。
蘇之念沒打擾他們。
四看了看,發現了一個類似茶水間的地方。
剛進去。
就沉默了。
這顧氏就是顧氏。
一個茶水間,有必要建設的這麼豪華嗎?
各種茶水飲料就拍了整整一排,然后是點心水果,又是滿滿當當。
更夸張的是,里面竟然就是一個小型電影院,連座椅,都是昂貴的按椅。
蘇之念嘆了一下資本家有時候也還有良心的,然后,果斷找了位置,隨意找了個電影放著。
也沒有真的在看,腦子整個是放空的狀態。
以前寫不出稿子的時候,就喜歡這樣。
Advertisement
開著電視,也不管電視里放著什麼,只要有聲音就行。
然后就什麼都不想,就這麼安安靜靜地躺在沙發上。
現在這椅子,比的沙發,好像還要舒服一點……
蘇之念這麼想著。
眼皮子不知何時,慢慢合了上去。
很快,就沉沉睡了過去。
有人走了進來,輕輕在上蓋了一條毯子,然后,安靜地坐在邊。
猜你喜歡
-
完結1722 章

快穿之女配功德無量
從混沌中醒來的蘇離沒有記憶,身上也沒有系統,只是按照冥冥之中的指引,淡然的過好每一次的輪迴的生活 慢慢的她發現,她每一世的身份均是下場不太好的砲灰..... 百世輪迴,積累了無量的功德金光的蘇離才發現,事情遠不是她認為的那樣簡單
292.3萬字8 27087 -
完結719 章
穿書後我成了娛樂圈天花板
一覺醒來,秦暖穿成了虐文小說里最慘的女主角。面對要被惡毒女二和絕情男主欺負的命運,秦暖冷冷一笑,她現在可是手握整個劇本的女主角。什麼?說她戀愛腦、傻白甜、演技差?拜拜男主,虐虐女二,影后獎盃拿到手!當紅小花:「暖姐是我姐妹!」頂流歌神:「暖姐是我爸爸!」秦家父子+八千萬暖陽:「暖姐是我寶貝!」這時,某個小號暗戳戳發了一條:「暖姐是我小祖宗!」娛樂記者嗅到一絲不尋常,當天#秦暖疑似戀愛##秦暖男友#上了圍脖熱搜。秦暖剛拿完新獎,走下舞臺,被記者圍住。「秦小姐,請問你的男朋友是厲氏總裁嗎?」「秦小姐,請問你是不是和歌神在一起了?」面對記者的採訪,秦暖朝著鏡頭嫵媚一笑,一句話解決了所有緋聞。「要男人有什麼用?只會影響我出劍的速度。」當晚,秦暖就被圈內三獎大滿貫的影帝按進了被子里,咬著耳朵命令:「官宣,現在,立刻,馬上。」第二天,秦暖揉著小腰委屈巴巴地發了一條圍脖:「男人只會影響我出劍的速度,所以……我把劍扔了。」
69.3萬字8 47376 -
完結9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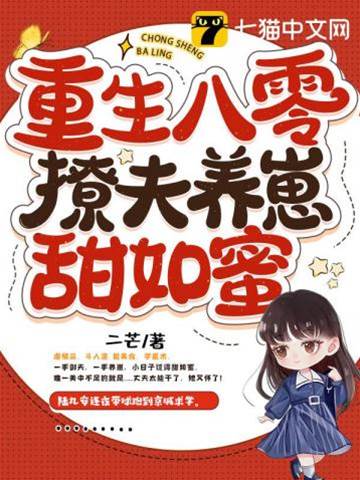
重生八零撩夫養崽甜如蜜
一場綁架,陸九安重回八零年的新婚夜,她果斷選擇收拾包袱跟著新婚丈夫謝蘊寧到林場。虐極品、斗人渣。做美食、學醫術。一手御夫,一手養崽,小日子過得甜如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丈夫太能干了,她又懷了!怕了怕了!陸九安連夜帶球跑到京城求學。卻發現自己的丈夫站在三尺講臺上,成了她的老師!救命!她真的不想再生崽了!!
174.3萬字8.18 74899 -
完結711 章

高考首富身份曝光,攻略高冷學姐
[都市日常](偏日常+1V1+無系統+學姐+校園戀愛)(女主十章內出現) “兒子,你爸其實是龍國首富!” 老媽的一句話直接給林尋干懵了。 在工地搬磚的老爸
123.7萬字8.33 18213 -
完結242 章

圓橙
直到離開學校許多年後。 在得到那句遲來的抱歉之前。舒沅記憶裏揮之不去的,仍是少年時代那間黑漆漆的器材室倉庫、永遠“不經意”被反鎖的大門、得不到回應的拍打——以及所謂同學們看向她,那些自以為並不傷人的眼神與玩笑話。她記了很多年。 而老天爺對她的眷顧,算起來,卻大概只有一件。 那就是後來,她如願嫁給了那個為她拍案而起、為她打開倉庫大門、為她遮風避雨的人。 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從來屢見不鮮。 連她自己也一直以為,和蔣成的婚姻,不過源於後者的憐憫與成全。 只有蔣成知道。 由始至終真正握住風箏線的人,其實一直都是舒沅。 * 少年時,她是圓滾滾一粒橙,時而微甘時而泛苦。他常把玩著,拿捏著,覺得逗趣,意味盎然。從沒想過,多年後他栽在她手裏,才嘗到真正酸澀滋味。 他愛她到幾近落淚。 庸俗且愚昧。如她當年。
36.8萬字8 10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