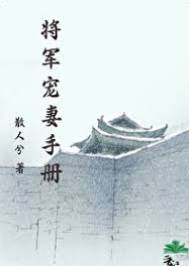《花開錦繡》 第268章 出門
俞敬修從俞閣老那裡回來,進門就看見了放在炕桌上的幾件嶄新的冬,花是他沒有見過的,瞧那應該是給男子穿的,他不由得多看了兩眼。
范氏不由得一陣心煩。
怎麼忘記了把這個收好?
又本能地不想讓俞敬修知道這是費氏給他做的裳——這些日子只顧著照顧珍姐兒,已經很久都沒有親手給俞敬修做過針線活了。
“想著這天氣越來越冷了,”范氏就笑道,“我想給相公多帶幾件冬。”說著,朝墨篆使了個眼,示意將服收好。
墨篆笑著去抱裳。
俞敬修卻走過去了角,道:“你的針線越發好了——這針腳縝平整。”然後抬頭了范氏,“以後不要再做這些了,傷眼睛不說,你還要照顧珍姐兒。家裡養著那些做針線的媽媽是幹什麼的?”眼底一片。
墨篆一怔,朝范氏去。
范氏看也不看墨篆一眼,笑道:“公公喊你去,都說了些什麼?”把這個話題給揭過了。
到了晚上,俞敬修在書房裡理一些信件,墨篆湊到了范氏的面前:“大,您看這服……”
“賞了下人吧!”范氏面有些沉地道。
墨篆應聲而去。
過了兩天,俞敬修定下了啟程的日子,俞夫人帶著束媽媽來看范氏給兒子準備的箱籠,正好俞敬修從衙門裡回來,想著范氏從來沒有做過這些事,怕母親挑出什麼病來,忙笑道:“天氣轉涼。范氏怕我寒,還特意給我做了幾件冬。”
范氏一驚。
俞夫人已笑著“哦”了一聲,很興趣地道:“都是用什麼料子做的?做的什麼式樣?”
范氏目有些惶恐地朝墨篆去。
Advertisement
墨篆心裡大僥幸。
那些冬不僅料子好,而且式樣也新。這樣的好東西,自然要賞給那些平日裡待恭敬有加的媳婦、婆子!至於賞給誰,還沒有思量好,加之俞夫人來得急。東西還沒有賞下去。
向范氏微微頷首。示意沒事,然後轉去拿了費姨娘做的那些冬。
俞夫人翻了翻,見那針線做得還算仔細。笑著朝范氏點頭:“辛苦你了!”十分滿意的樣子。
范氏不由長籲了口氣。
墨篆則在一旁著冷汗。
俞敬修就挽了母親的手臂,笑道:“娘,這下您該放心了吧!”
俞夫人笑著拍了拍兒子搭在自己臂上的手,沒再看下去。叮囑了俞敬修幾句,就和束媽媽回了正屋。
范氏卻惦記上了費氏。常做這做那的,有段時間費氏片刻也不得空閑。
費氏不免到吳姨娘抱怨:“……早知道這樣,我就不費這工夫了。馬屁拍到了馬上。”
吳姨娘聽了直是笑。
費氏就問:“你總在屋裡呆著,怎麼呆得住?平日裡都做些什麼打發日子?”
“做些針線活。”吳姨娘笑道。“我父親新娶了太太,又添了個弟弟,妹妹嫁了個坐館的秀才。我拿了些零頭布給他們做些小東西,多多補補他們。”
費氏奇道:“他們遠在舟山呢!”
吳姨娘笑道:“南京那邊常有人來。吳府那邊的管事也常到京都來,讓他們幫著捎過去就行了。”
費姨娘就笑道:“吳夫人對你倒沒有見外!”
吳姨娘笑了笑,沒有做聲。
兩人倒時常湊在一起說說話。不過是費姨娘說的時候多,吳姨娘總在一旁聽著。
到了臘八節那天,吳家送了臘八粥來,有一份是指定給吳姨娘的。吳姨娘不得要給些回禮,翻箱倒櫃地找了幾隻荷包、幾塊帕子讓那媽媽帶回去。
Advertisement
那媽媽就笑著問:“有沒有給趙太太的?我也好一塊捎了去。”
吳姨娘錯愕。
那媽媽笑道:“夫人說,趙大人不在家,趙太太閉門謝客。等閑人不得見。你既然能見到趙太太,想必趙太太對你也是另眼相看。若是有什麼東西要給趙太太,讓我直管捎回去。”
怕是想拿自己在趙太太面前說事吧!
既然趙太太不見客,自有不見客的道理。上次貿然闖進去已是失禮,怎麼能再給趙太太添麻煩。
“沒有。”吳姨娘笑道,“我一個妾室,怎好捎東西給趙太太?您回去後代我向夫人道聲‘多謝’。”說著,站起來送客。
那媽媽見吳姨娘不客氣,訕訕然地回了府,去稟了吳夫人。
吳夫人有些頭痛,了的媽媽來:“這些日子趙家有什麼靜沒有?”
那的媽媽笑道:“沈太太回來了!給趙太太帶了很多東西,這會還沒有走呢!”
吳夫人面喜,道:“走,我們去看看趙太太。”
的媽媽笑著應“是”,想著外面大風大雪的,服侍吳夫人披了件灰鼠皮的鬥篷,又拿了把油紙傘,扶著吳夫人去了趙家。
月川頗有些無奈,卻又不得不去稟了傅庭筠。
傅庭筠正和三堂姐坐在室臨窗的大炕上說話,聽說吳夫人來了,不由了額。
三堂姐卻笑道:“還是讓進來吧!這人雖然喜歡家長裡短的,可你這樣窩在家裡不出去,外面的靜卻是一點也不知道。有陪著說說話,倒也省了讓人去打聽消息。”
“這你倒不用擔心。”傅庭筠笑道,“我雖坐在屋裡,可阿森卻是每天都要和我說說話的。我就是不喜歡吳夫人那雙窺視的眼睛。”話雖這樣說,還是請了吳夫人進來。
Advertisement
吳夫人老話重提,要給三堂姐洗塵、接風,讓傅庭筠作陪。
請的是三堂姐,傅庭筠不好拿主意。三堂姐則爽朗地笑道:“好啊!那我就等夫人的帖子了。不過靠近年關了。我還是第一次在京都過年,我們家大人也剛到吏部,不免有些應酬。等開了春,我再回請夫人好了。”
吳夫人聽著自然是一團歡喜,索定下了初十的日子。
傅庭筠送走了吳夫人不免笑著問三堂姐:“姐姐葫蘆裡又賣的什麼藥?”
三堂姐抿了笑,道:“這是你三姐夫說的——吳大人那頭連著郝劍鋒,郝劍鋒那頭又連著好幾位從前跟著沈閣老的三品大員。如今錢閣老和陳閣老在閣的日子都不好過。皇上能問一次,能問兩次,總不能事事都過問。郝劍鋒等也不是要和皇上打擂臺。不過錢閣老、陳閣老的資歷太淺,不能就這樣立刻倒戈,又找不到合適的臺階下罷了。若是能讓郝劍鋒和肁先生搭上話,豈不是個現的臺階?郝劍鋒等人要面子。不願意在錢閣老、陳閣老面前服,肁先生可是皇上在潛邸的軍師。論資歷,曾是熙平二十三年丙辰科的進士,在肁先生面前服,可不算丟人!”
傅庭筠瞪大了眼睛:“這些日子三姐夫隔三差五的就來看孩子。還檢查孩子們的功課,空指點一下阿森,怎麼在我面前卻是一句話也沒有提?”又道。“三姐夫是想給郝劍鋒牽線搭橋嗎?”
“九妹夫不在家,他怎麼好跟你說這些?”三堂姐掩了笑。然後低了聲音道,“你三姐夫的意思,那郝劍鋒在吏部多年,人脈深厚,他若是走不通你的路子,肯定會想辦法找其他路子的,與其這樣,還不如你們賣個面子給他。趁著他為難之時與他好。還說,以郝劍鋒的能力,縱然不能閣拜相,在二品的位置上穩穩地站住那是絕對沒有問題的。趙凌外放,還是將軍,糧草、軍餉、軍功都得閣老們集議,若是有了郝劍鋒這樣的人相助,豈不是事半功倍?”
Advertisement
傅庭筠不認真思考起來。
趙凌又在貴州打了幾場勝仗,連陌夫人都親自登門恭喜。
在宣府的時候,趙凌就曾為了宣府總兵府的糧食、軍餉等事多次回京都與兵部的人涉。若是有個頂事的人能在朝中為趙凌說話,趙凌可以省事不。三姐夫資歷太淺,十年間能升到正三品已是不易。指著三姐夫,怕是黃花菜都涼了。若事如三姐夫所說的,幫郝劍鋒一把,既解了皇上之圍,又結了郝劍鋒,倒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這件事,還得和九爺商量商量。”慎重地道,“廟堂上的事,還是他們男人看得更清楚些。”
“那是當然。”三堂姐笑道,“不過,最好是能在年前年後,拖得久了,恐生變故。”
傅庭筠點頭。想著這件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轉移了話題,問起三堂姐回華的事來:“不是說過七七就回來的嗎?怎麼這個時候才回來?五堂姐們還好嗎?”
“唉!”三堂姐聽著,就苦笑著歎了口氣,“還好你沒有回去,你若是回去了,只怕也覺得丟臉!”然後說起華發生的事來,“……頭七都沒有過,為著開銷,大伯母和四嬸嬸就吵了一架。過了七七,我好不容易說服了母親搬到別院去守孝,不管大宅的那些事,結果一向不管事的六叔跳出來, 說要分家……我們幾個做姑的真是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沒等晚上上燈,就紛紛回了娘家。我卻被大伯母拉住,要我主持公道。還是母親裝病,我才得以。你說,這都是什麼事?”
傅庭筠嚇了一大跳:“怎麼是六叔提出來分家?舒家的人也不管嗎?”
舒家是六嬸嬸的娘家,除了嫡親兄弟舒明出了仕,這幾年又陸陸續續出了幾個進士。
三堂姐表怪異地了一眼傅庭筠,道:“好像就是舒家舅舅要六叔叔和六嬸嬸和大伯母他們分家的!”
※
大家周末愉快!
ps:看到有些書友留言,覺得趙凌這段時間出場太,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趙凌總得鬥鬥才能有資歷留在京中做大佬吧?正好趁著這段時間寫寫俞家的況……這種兩地分居的日子很快就會結束了。我可是親媽哦……o(n_n)o~
※
猜你喜歡
-
完結224 章

吾妹千秋
照微隨母改嫁入祁家,祁家一對兄妹曾很不待見她。 她因性子頑劣桀驁,捱過兄長祁令瞻不少戒尺。 新婚不久天子暴斃,她成爲衆矢之的。 祁令瞻終於肯對她好一些,擁四歲太子即位,挾之以令諸侯;扶她做太后,跪呼娘娘千秋。 他們這對兄妹,權攝廟堂內外,位極無冕之王。 春時已至,擺脫了生死困境、日子越過越舒暢的照微,想起自己蹉跎二十歲,竟還是個姑娘。 曾經的竹馬今爲定北將軍,侍奉的宦官亦清秀可人,更有新科狀元賞心悅目,個個口恭體順。 照微心中起意,宣人夤夜入宮,對席長談。 宮燈熠熠,花影搖搖,照微手提金縷鞋,輕輕推開門。 卻見室內之人端坐太師椅間,旁邊擱着一把檀木戒尺。 她那已爲太傅、日理萬機的兄長,如幼時逮她偷偷出府一樣,在這裏守株待兔。 祁令瞻緩緩起身,握着戒尺朝她走來,似笑非笑。 “娘娘該不會以爲,臣這麼多年,都是在爲他人作嫁衣裳吧?”
34.6萬字8 3590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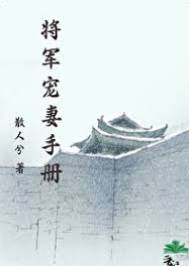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12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