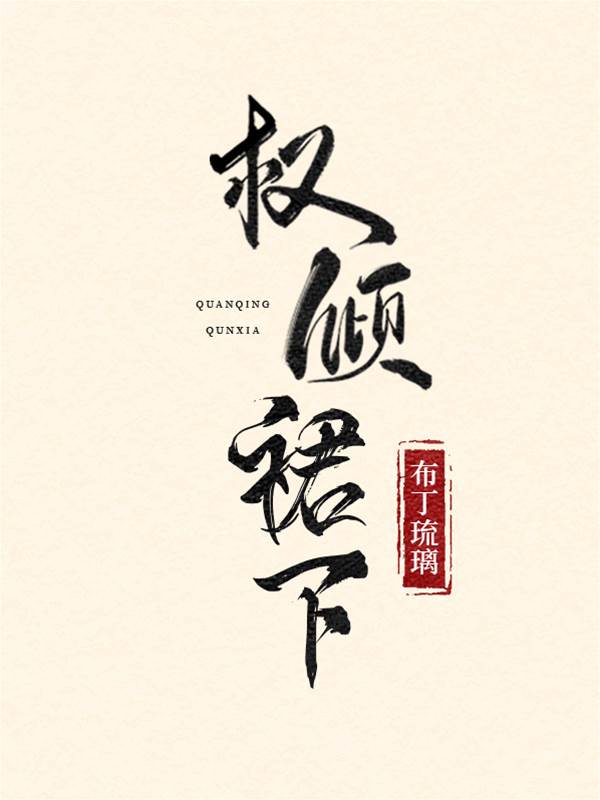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媚公卿》 第69章 套近乎?
下午時,外面傳來一個陌生的婢聲音,“阿容可在?”
平嫗迎上去,笑道:“在呢。”
一個十八九歲,圓圓臉,大眼睛的走了進來。這雖然做婢打扮,可一淡紫羅,笑容矜持,看起來比一般的郎還要像郎些。
這婢朝著平嫗了一眼,瞟向寢房中,笑道:“我家主母阮氏有請阿容。”
阮氏?陳元的嫡妻?
陳容一凜,連忙站起來,在房中應道:“請稍侯,陳容馬上來。”
那婢一笑,應道:“是。”
不一會,陳容便換了一套在平城時穿過的舊裳,出現在臺階。
那婢見出來,再次福了福,向後退出一步,示意先行。
陳容提步向前走去。
在的後,那婢領著兩個小婢,娉娉婷婷地走著,的作,著一種矜持和培養多年纔有的禮數。而這些,來自北方,父兄疏於管教的陳容,是不懂的。
陳容朝了一眼,剛把腳步放慢,學者那般碎步而行。轉眼間想到,自己又用不找結阮氏,再則,就算自己結,也改變不了什麼,何必邯鄲學步?
想到這裡,索放開腳步,快步而行。
幾個婢見步履生風,呆了呆後,連忙提速。
當陳容來的阮氏所在的院落裡,三個婢都有些氣吁吁了。
來到院落外,那婢了一口氣,朝陳容強笑道;“小娘子稍等,容我稟過主母。”
陳容點了點頭,側過頭打量著四周的景。、不一會,那婢的聲音傳來,“阿容,進來吧。”
“是。”
陳容應了一聲,快步院落。
那婢站在臺階上,含著矜持的笑容向陳容,見走近微微躬,道:“主母在裡面候著呢。”
Advertisement
“是。”
陳容越過,直直地走堂房中。
這堂房裝飾得富麗堂皇(堂房),最先映陳容眼簾的,是一座高達三尺的珊瑚,這珊瑚,不管殊澤還是完整度,都不比在平城時砸碎的那個要差——如此貴重之,被這般隨隨便便地擺放在紅木幾上。
陳容把目從珊瑚上收回,朝著堂房正中,的玉石屏之側,安坐在塌幾上的婦人盈盈一福,喚道:“伯母。”
這婦人四十幾歲,潤,臉上沒有毫皺紋,一張容長臉上,掛著疏淡的笑容。
在這個婦人後,站著一個陳容見過的婦,這婦二十七八歲,正是剛來那日拆穿裝病的。陳容知道,這婦是陳元的妾,是阮氏邊的人,自又明能幹,深陳元的寵,雖是妾,卻比一般的妾地位高多了。
阮氏微笑地看著陳容,朝著上下打量了一番,右手輕指,“坐罷。”
“是。”
陳容走到那塌幾,大大方方地坐下——從頭到尾,的作都帶著幾分率和魯。不知不覺中,阮氏蹙起了柳葉眉。
著自坐下後,便低著頭,一聲不吭的陳容,阮氏溫和地開口了,“阿容,伯母數日前剛剛抵達南城,一回來便忙於諸事,疏忽了你,你可有怪責?”
陳容聞言,連忙欠回道:“不敢。”
阮氏慢慢一笑,“阿容父兄不在,我便是你的母親,不必拘禮。”
陳容答道:“是。”
阮氏收回目,臉上笑容稍減,輕言細語地說道:“阿容,你還有一個月,便滿十五了吧?”
難不自己過來,是爲了婚事?陳容心中咯噔了一下。
Advertisement
再次欠了欠,答道:“是,伯母好記憶。”
阮氏低嘆一聲,道:“都快十五的小娘子了,哎。”
的語氣中,有著陳容聽不懂的責備。
對陳容來說,既然聽不懂,就當沒有聽見。當下,依然低收順目,卻是面無愧。
阮氏的眉頭,不由蹙得更了。
端起杯子,飲了一口人,徐徐問道:“阿容那一院,如今是誰管事?”
站在後的婦上前一步,欠了,恭敬地回道:“小姑子家厚,向管事要求一切供應,自己承擔。”
阮氏蹙眉道:“這個不行。”放下杯子,道:“我和伯父既已接手過來,豈能如此放任於?”
目轉向陳容,溫言說道:“我只有阿微一個兒,便再多一個,也是喜事。阿容,以後你的吃穿用度,全部照著阿微的份例,可好?”
陳容低眉斂目的,聞言猶豫了一下,道:“稟伯母,事是這樣的,前陣子郎主說府中糧,要求我減奴僕。可我這些奴僕,都是看著我長大的,阿容不願意裁了他們,便向郎主要求自行承擔一應支出。”
頓了頓,笑了笑,十分直接地問道:“如果伯母不會裁減我的奴僕,阿容自是一切願意。”
一直蹙著眉頭的阮氏,聞言暗暗搖了搖頭。
等陳容說完,輕嘆道:“我真是有罪,阿微也罷,阿容也罷,都是舉止疏,說話也……哎。”
按道理,一個長輩如此責怪自己,陳容應該站起來向請罪。可陳容也不知是聽不懂還是怎麼的,竟還是愣愣地坐在那裡,一不的。
阮氏的柳葉眉蹙得更深了。
轉眼看向那婦。
Advertisement
婦上前一步,在後低低說道:“也許正是這樣的子,王七郎纔會看重於。”
阮氏沉了一會,點了點頭。
再次看向陳容時,那笑容已真誠多了。
舉起人再次飲了一口,阮氏笑道:“阿容果真如你伯父所言,是個率真可的。”
陳元說率真可?陳容差點失笑出聲。
阮氏似是不想與久呆了,當下聲音微提,輕言細語的語調,快速二分,“阿容啊。”
“在。”
“你已十五歲了,也不小了,以後嫁了人,還是得多加註意。”
擡起頭,向外面喚道:“弄兒,去把三郎來。”
“是。”
在陳容的納悶中,不一會功夫,一個略帶沙啞的青年男子聲音從後面傳來,“母親找我?”
阮氏一聽他的聲音,便是笑逐開,慈地喚道:“三郎,來吧。”
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應聲。
他陡得看到陳容,不由一怔。
他很快便收回目,朝著阮氏施了一禮,恭敬地喚道:“兒子見過母親。”
“我兒過來坐罷。”
“是。”
落座後,青年的目轉向陳容,問道:“母親,是?”
“呀,便是阿容。”
“什麼?”
青年一驚,他好奇地盯著陳容,道:“便是那個彈奏求凰的阿容?”
阮氏拍了拍他的手,責怪道:“休要如此說你妹妹。”
含笑,向陳容說道:“阿容,這是你三哥,以後,你也和阿微一樣,把他當親哥哥吧。”
陳容依然低眉斂目地應道:“是。”
站起來,朝著青年福了福,溫順地說道:“見過三哥。”
陳三郎還在盯著上下打量,聞言站起來,還了一禮,笑道:“阿容不必多禮。”
Advertisement
阮氏滿意地一笑,聞言喚道:“阿容啊,你三哥,可是個多才多藝的,你以後要與他多多親近。至於那些舉止疏言語無狀的,還是走的好。”可能是看陳容著實遲鈍,這話已說得很直白了。
可說得這麼直白,陳容還是聽不懂。
愕愕地擡起頭來,迷糊地著阮氏,道:“舉止疏言語無狀?誰啊?”
在陳容的記憶中,除了自己,還真的不知道有哪個人,當得七這樣的評價。
阮氏盯著迷糊的樣子,眸子閃過一抹不耐煩。
而坐在邊的陳三郎,這時終於發現陳容的長相頗爲人,雙眼直勾勾地盯著打量個不休。在有點難堪的氣氛中,那婦站了起來,甜笑道:“好了好了,阿容,你伯母累了,我送你出去吧。”
陳容差點籲出一口氣,連忙站起,應道:“是。”
婦扭著腰肢,走在陳容的前面。來到臺階上時,低聲音說道:“阿容,常到你府中來的那幾個,外面平素是不屑的。哼,就算們份上是嫡,可是看那修養那樣貌,又哪裡比得上阿容你?”
至此,陳容才恍然大悟:原來阮氏說道是陳茜和陳琪啊,不對,陳微也是與自己走得近的。阮氏的話中應該包括。
婦見陳容終於明白了,笑容不再那麼僵,朝著房中瞟了一眼,又向陳容說道:“明日裡,那王七郎是不是約了你遊湖?”
陳容怔怔地點了點頭。婦見還是不明白,笑容一僵,無力地低聲音,說道:“明日,就讓你三哥送你去遊湖吧。”
陳容再次恍然大悟。
朝著婦福了福,恭敬的,乾脆地應道:“是。”
婦滿意地點了點頭,親切地道:“回去吧。”
“是。”
婦目送陳容遠去的影,大搖其頭。
那婢走到後,忍笑道:“奴還是第一次見到,這般遲鈍的郎。”
婦點了點頭,嘆道:“誰人家瑯琊王七看重呢?你也知道,子啊建康,王家的聲威,連皇室都不能相比!哎,三郎若是能得到王七郎一字之贊,對他的這次建康之行,是大有好啊。”
第一更求紅票。(……)
方便您下次從本章繼續閱讀
猜你喜歡
-
完結23 章

法醫狂妃:王爺,躺好彆動!
首席女法醫冷夕月,穿越成寧王李成蹊的棄妃。 剛剛醒過來,就遇到冤案。 她帶著嫌疑人家屬偷偷去驗屍,卻被王爺拎小雞一樣捉回去狠狠訓斥。 她費儘心思追查死因,最後嫌疑人卻跪地求她不要再追查下去…… 找出真相,說出真相,她執意要做逆行者。 可糊塗王爺整日攔著她就算了,還弄來個“複生”的初戀情人來氣她…
4.4萬字8 7755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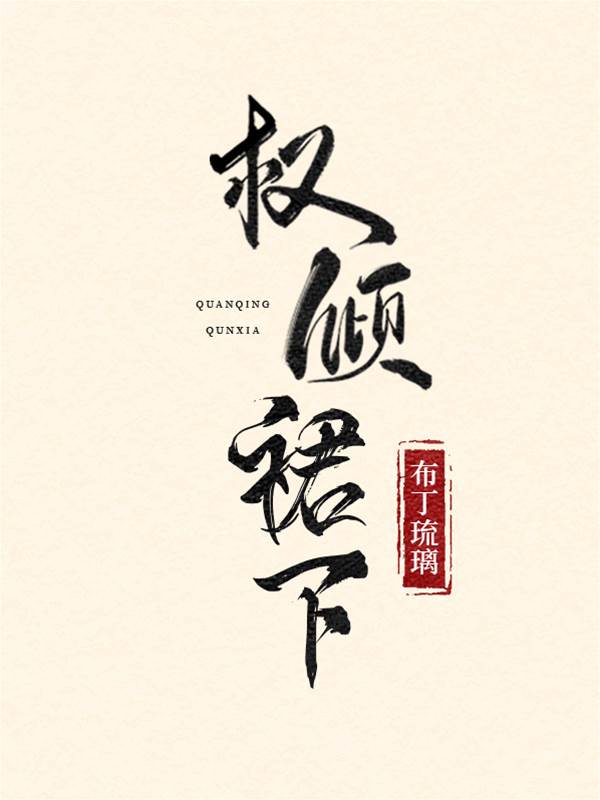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1817 -
完結429 章
乞丐醫妃:馭夫有道
穿越成乞丐,救了個王爺?這是什麼操作?江佑希不由暗自腹誹,別人都是穿越成公主王妃,她倒好,鞋兒破帽兒破身上的衣服破? 神仙運氣呀。 還被這個惡婆娘冤枉和敵國有勾結,勾結個毛線,她連去敵國往哪個方向都不知道啊! 火速止住謠言,她毫不留情地報復......了惡婆娘,在王府混的風生水起。 她真是馭夫有道啊! 馭夫有道!
108萬字8 10198 -
完結454 章
山河美人謀
有仇必報小驕女vs羸弱心機九皇子未婚夫又渣又壞,還打算殺人滅口。葉嬌準備先下手為強,順便找個背鍋俠。本以為這個背鍋俠是個透明病弱的‘活死人’,沒想到傳言害人,他明明是一個表里不一、心機深沉的九皇子。在葉嬌借九皇子之名懲治渣男后。李·真九皇子·策“請小姐給個封口費吧。”葉嬌心虛“你要多少?”李策“一百兩。”葉嬌震驚,你怎麼不去搶!!!
108.6萬字8 101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