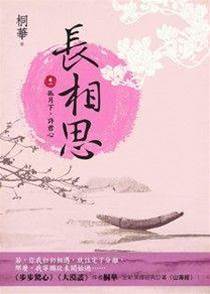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扶搖皇后》 璇璣之謎 第十五章 順藤摸瓜
孟扶搖在半空,擡手就要迎著旋目撕下面。
卻有一道黑影突然橫撞過來!
那影子來得離奇,竟然是從側殿裡飛出來的,腳一蹬踩著窗戶飛越而起,人在半空白一亮,三丈外青鋒冷颼颼的瘮人,手中竟然是絕世神兵。
那影還在丈外,名劍寶已經到了孟扶搖前,竟是直取擡起的手腕,孟扶搖冷哼一聲擡手一剪,那手出去堅實如玉,生生將劍剪斷。
手指一拈拈住那長劍的劍尖,也不反手,就那麼抓著劍尖對那突如其來的人當直搗過去。
那人卻並不戰,絕世名劍也不要了,一個流利的轉直撲回大殿,從旋著的窗戶直撲而進,一手抓住旋飛大殿,同時擡一踢將打開的長窗重重踢上。
砰一聲窗戶再次閉,旋又給拎進去了。
孟扶搖再次要擡起撕面的手立時停住,一時氣得面鐵青。
這半路殺出的程咬金是哪個混賬?
明擺著並不想和決一死戰,只是不想讓旋看見,這麼拼死阻攔著,明擺著也是個知人。
這個時候,阻攔尋知真相的知人,八就是當年害過自己的仇人!
不管五歲之前發生了什麼,現在可以確定,絕對不是什麼好事,就算不論五歲之前的事兒,五歲之後被死老道“摧殘”十年,爲練武吃盡人間至苦,十五歲起飄零江湖盡欺辱,都是拜這些混賬所賜!
孟扶搖的火,蹭蹭的冒上來,一擡便奔了過去。
玉衡卻突然袖向地面一劃。
他袖劃出如同鋼板,在青石臺階上劃出一溜明亮的火花,他手指一擡,那一串火花如一串星鎖鏈般突然躍上了他指尖,爍爍閃亮舞不休,火花裡玉衡眉目明滅,邪笑道:“我是了傷,可是你兩個,好像也不是什麼全盛狀態,正好,那麼就讓我來告訴你,十強前五和後五之間的真正區別。”
Advertisement
他突然緩緩轉過,毫不顧忌的將背對上了孟扶搖。
孟扶搖一眼看見他的背,頓時心中一驚,那背心裡雖然衫劃裂約傷痕,但是記得自己短刀時下手極狠,就算立刻了出去,但以的功力還是能對玉衡造不輕的傷害,可是現在玉衡這一轉,那傷痕卻已不再流,甚至那狹長的傷痕,似乎還在以眼能見的速度在迅速癒合。
這是一種何等神奇的復原能力!
孟扶搖一驚未畢,背對的玉衡突然手一甩,手中那串不滅的星火鎖鏈在半空中甩出一道燦亮的弧,明明只是虛,竟然生生甩出剛猛的真氣和呼嘯的風聲,那麼似可裂天地般,狠狠下來!
“啪!”
十丈寬闊的天井地面生生被劈裂,孟扶搖點起的那叢火剎那熄滅,三十丈外外殿檐角上燃著的燈籠唰的一,蒙燈籠的紙呼的一收,上蠟燭呼呼燃起,一團團火球似的墜落,滿院的春花花瓣齊齊被扯裂,扯裂的那一刻便已經無聲了齏。
孟扶搖飛揚的角,被這狠厲的一劈劈得向上揚起,遮住了的臉。
而四面黑暗,所有源都被熄滅。
森冷的風已到!
風聲裡有人邪邪一笑,那笑聲近在耳側,約裡不覺得有什麼作發生,臉上卻突然一涼一痛。
他想毀了的臉!
側有人飛速掠來的袂聲,大概是長孫無極,“啪”的一聲對掌聲,震的連地面都似晃了晃。
孟扶搖本就怒火滿,此時更是忍無可忍,也不管臉上還在痛,擡手就是一掌也劈了過去。
那掌黑暗中劈下,掌心裡一截黑的鋒刃斜斜逸出。
弒天!
Advertisement
“啪——”
大力狂涌,如巨石錘心海浪沒頂,又或是一面牆生生當頭砸下,砸出萬頃波濤檣櫓灰飛煙滅,砸出千層巨浪萬皆齏,砸得孟扶搖眼前一黑頭一甜,全剎那繮一涌。
子突然被人大力一扯,風聲一急,黑暗中異香氤氳更濃幾分,隨即聽玉衡有點詫異的道:“你——好!原來你是——”話說到一半突然止住,哈哈一笑。
孟扶搖卻已經被長孫無極扯了出去。
子被扯一道飛揚的旗,在午夜的風中呼啦啦的展開,流星般越宮闕千層,從瓊樓玉宇之巔劃過。
後,璇璣皇后憤然跺腳,厲喝:“爲什麼不殺了他們以絕後患!去追,去追啊!”
玉衡默然不語,半晌他擡起手,捂住,咳嗽一聲。又一聲。
隨即緩緩擡起袖,捂住脣,從袖後聲音有些嘶啞的道:“五洲大陸人才輩出……我果然……老了……”
“去追啊!去追啊!”璇璣皇后猶自不滿,催促不休。
玉衡放下袖,轉眼看一眼,那一眼緒翻涌,惆悵……無奈……後悔……憂傷……
半晌他道:“寧兒……我真後悔不該將你縱這樣,將來我若再護不了你,你怎麼辦?”
璇璣皇后停住口,似被那聲久已無人呼喚的閨名,默然半晌道:“你今天怎麼了?失魂了?兩個小輩就嚇你這樣?他們不也吃了虧?你好歹十強者第四,怎麼這麼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
玉衡笑了笑,沒有回答,只道:“你這子,我勸過多次你總不聽,如今你聽我最後一次,改了吧。”
“改什麼?”璇璣皇后聲音又尖利起來,“你爲什麼護不了我?你不是答應我保護我,從生,到死的嗎?”
Advertisement
“自然。”玉衡很平靜的道:“從生,到死,你死的時候,只能葬在我邊,家的陵墓,不許你去。”
“你在說胡話。”璇璣皇后瞟他一眼,傲然道:“我和他生同衿死同,他的安陵旁邊的位置是我的,只能是我的,整個安陵,都是我和他的,沒有人可以更改。”
“不許。”玉衡淡淡道,“我不許,你若葬安陵,我就毀了整個安陵,挖出你們的,把他的拿去喂狗,把你的吃下肚,你想葬安陵,我就讓你連個葬之地都沒有。”
“你……”璇璣皇后被他用平淡語氣說出的骨悚然容所驚嚇,霍然回首瞪著他,玉衡的目在月裡濃濃淡淡,依舊是那副不不不知真心假意的神,然而相這許多年,對玉衡的子多也明白幾分,想了又想,才小心的試探的道:“你開玩笑的,你開玩笑的是吧?”
玉衡定定的看著,眼底掠過一失,隨即卻笑了,道:
“是,開玩笑。”
----------
孟扶搖被長孫無極牽著手,飛快的越過重重屋脊。
長孫無極拉著奔得飛快,一圈一圈的頂風狂奔——孟扶搖剛纔和玉衡那一對掌,真力震積淤在丹田,必須儘快發散出來。
奔到第三圈時,孟扶搖嘔出一口淤,長孫無極才停下來,舒口氣道:“好了——”
孟扶搖擡頭,激的看他一眼——他永遠最清楚的狀況,甚至不需要把脈。
隨即目亮亮的笑道:“剛纔那一掌,好像震開了我丹田一些積淤,再等幾天我全部復原,將宗越的藥力全數吸收,我應該很快就能升級了,哈哈,和十強者打架就這個好,打一場上一級,玉衡啊玉衡,且留你先得意幾天,準備棺材吧!”
Advertisement
長孫無極卻不管在得意什麼,一擡手掀了面,皺眉道:“臉上沒傷吧?”
剛一掀開就嚇了一跳,孟扶搖滿臉是,紅彤彤的怕人,再襯上齜牙咧的笑容,實在令人不敢消,仔細一看才放下心來,原來是鼻子破了。
後知後覺的孟扶搖捂著鼻子,對著一手鮮紅詫異的道:“咦?我鼻子流了我咋不知道?哎呀,多虧我鼻子高,天塌下來有它擋住,不然塌一點,的就不是鼻子,八是我的眼睛了。”
長孫無極無可奈何的看了一眼,一頂下頜道:“仰頭。”掏出巾帕給拭去臉上,道:“沒見過子這麼不注意自己容貌的。”
“要好皮囊何用?”孟扶搖攤手,“徒惹煩惱,還容易被人輕視,不是花瓶也是花瓶,但凡你做出什麼業績,必然是你賣弄相得來,個人能力全部抹殺,還有……”突然笑一笑,慢慢道:“醜一點有醜一點的好,清靜。”
長孫無極正給臉的手一頓,半晌擡眼看,挑眉道:“敢孟王認爲我等追逐你,都是因爲閣下絕頂容姿。”
孟扶搖一聽就知道太子殿下生氣了,訕訕的笑,眼睛撲閃撲閃著不說話,大有“我覺得皮相還是很重要的八你們喜歡我和這個有關係的但是人家臉皮薄不好意思直接說你就認了吧”的意思。
長孫無極收回巾帕,嘆了一口氣道:“幸虧是我……換那個火子的傢伙,八就直接讓你再次出。”
孟扶搖不服氣,頭一昂道:“錯了嗎錯了嗎?”
“大錯特錯!”長孫無極冷笑,“你這個說法實在侮辱了我們。”
“真嚴重。”孟扶搖咕噥,“好吧我承認你們意氣高潔,從來不爲他人皮相所。”探頭看看,見四面都是低矮的連排房屋,圈著矮矮的牆,皺眉道:“這是什麼地方?”
“好像是太監僕役住的地方。”長孫無極道,“你知道的,皇宮中有些犯錯被黜生有疾病或者年紀老邁的太監宮,一般都會另闢地方集中居住。”
“其實就是扔一邊自生自滅。”孟扶搖頓時明白,嘆口氣道,“都是可憐人……咱們走吧,過幾天找個機會再解決掉那些混賬。”
剛轉,長孫無極卻突然“咦”了一聲。
孟扶搖回看去,便見長孫無極目落在屋檐之下,那裡屋角的暗影裡,蹲著一個人,看背影是個老者,白髮散的披在肩上,正用草桿兒,在地下畫著什麼。
這誰半夜不睡門外畫畫?孟扶搖好奇的瞅了一眼,正想走開,那老太監突然“荷荷”兩聲,扔了草桿向後便倒。
孟扶搖趕掠下去扶住,一扶之下先皺了皺眉,十分討厭太監上的尿味道,一擡眼看見老太監滿面污髒,太長時間沒洗的頭髮紛的披下來,被臉上沒盡的飯粒粘住,辨不清五眉目,此時正張著,雙眼渾濁的瞪著,角邊流下涎水來。
看那樣子是中風,或者什麼疾病發作,孟扶搖拍拍他的臉,道:“老丈……老丈……”
那老者努力睜開眼,目及的臉,眼珠子突然凝住了,僵在眼眶裡一不,木木的定在那裡,孟扶搖差點以後他看見自己就死了,嚇了一跳,連聲呼喚,老太監掙扎著,似乎想呼,又似乎想掙,但是僵木的彈不得,所謂的大力掙扎不過是輕微的抖,看在孟扶搖眼底,還是中風發作的癥狀。
“死人!又竄出去發瘋!”
後突然有開門的聲音,一個衫凌神麻木的婦人嘟嘟囔囔大步出來,罵罵咧咧道:“死老瘋子,半夜三更的不睡覺,整天在外頭!”蹬蹬蹬的過來,劈手從孟扶搖手中抓去了那老太監,也不看孟扶搖一眼,橫拖豎拽的便將老太監枯木般的子拽走,一腳踹開門將人扔進去,再一腳把門反踢,砰的一聲整間屋子都抖了三抖。
孟扶搖看得好氣又好笑,對後長孫無極道:“我第一次知道我原來是明的。”
猜你喜歡
-
完結585 章

侯府真千金她重生了
重回十年前的江善(周溪亭),站在前往京城的船只上,目光冷淡而平靜。她是被人惡意調換的文陽侯府的真千金,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里的容妃娘娘是她姨母,溫潤如玉的二皇子表哥是太子之位的熱門人選,出生既頂端的她本該萬千寵愛、榮華富貴且波瀾不驚地過完一生。但十六年前的一場人為意外,打破了她既定的人生......等她得知身世,回到文陽侯府,取代她身份地位的江瓊,已經成為父母的掌心寶。前世她豬油蒙了心,一心爭奪那不屬于自己的東西,不論是父母的寵愛,還是江瓊身份高貴的未婚夫,這一世,她只想快快活活地活一...
107.9萬字8 330761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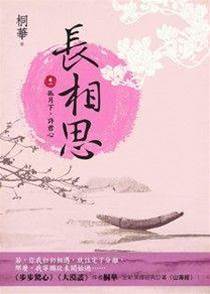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1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