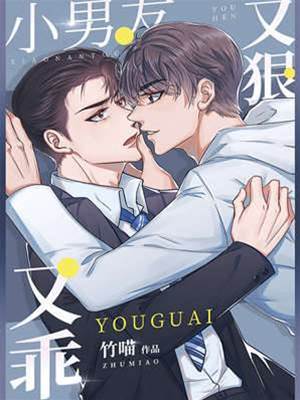《民國小商人》 第76章 仙君打架
尚玉樓到的那天,南坊剛巧下第一場雪。
尚玉樓帶了戲班的人坐了兩輛大車,天麻麻亮就趕到了南坊區,寒風卷著雪花,吹得尚老板鼻尖通紅,瞧見謝等人拱手問好的時候,手指關節也凍紅了。
“諸位,好久不見,好久不見!”
“尚老板風采依舊!”
兩邊互相謙讓幾句,這才進了戲樓。
白虹起已包下場子,連帶對尚玉樓戲班裡的人也安排妥當,在南坊經營多年,這裡人員混雜,白姑娘做這些事兒向來周全。
尚玉樓每到一個地方演出,除去票房、報館一類需要打點的地方,最要的就是自己隨帶著的一尊菩薩和一個小香爐,帶著戲班眾人更焚香,認認真真拜過之後,才能踏實幾分。只是今日燒香的時候,尚玉樓右眼接連跳了幾次,心裡莫名有點發慌。
謝去給他送了一遝白巾,尚玉樓正在勾臉,隔著鏡子就瞧見他,臉畫了一半就站起來親自去接,笑盈盈道“謝管事,怎麼是你送來?快坐、快坐!”
謝這一年變的不止是容貌,人也長高了,站在尚玉樓跟前比他已高出些許,不再是之前那個半大孩子模樣。
他把白巾放下,對尚玉樓十分客氣“尚老板見外了,還是同之前一樣喊我一聲小謝就行。”
尚玉樓從善如流,改了稱呼,一邊吩咐人把白巾發下去。
謝好奇“冬日不冷,要這麼多白巾是?”即便是武生,冬日打完一場也不見得大汗淋灕,需要這麼多巾汗。
尚玉樓靦腆道“說來慚愧,尚某最近手頭有點,這戲服領子上都是綾羅綢緞,用上一兩次就髒了,這一年算下來也是不花銷,我就琢磨著反正臺下看到的都是一抹白,拿這白巾裹上剛剛好。”他一邊說著,一邊把白巾折疊好,裹了一圈在領子那,果然簇新雪白,別說遠看,近看也沒什麼病。
Advertisement
謝角了,把笑意去。
尚老板鐵公一隻,這摳門的子還真是幾年如一日,從未變過。
一塊白綢做的戲服領子又不耐髒又氣,放時間久了還容易發黃,幾次就廢了,價格還不便宜,有些角兒用的,能作價一塊大洋;而白巾就不同了,這是最便宜的料子,還吸汗,路邊人力車夫每人脖子上都搭著一條,一錢兩條。
而且即便用幾次不白了,那也能當抹布件,實在是一樁節省劃算的買賣。
尚玉樓戴著“巾圍領”滋滋,陪謝說了一會話,又去勾臉了。
謝來這裡也不全是為了見他,送下東西之後,視線在戲班裡轉了一圈,很快就落在不遠幾個半大小子上。
那幾人瞧著十來歲出頭的年紀,妝了猴兒妝,清一畫了倒栽桃的一張猴臉,正依靠在牆邊扎馬步練基本功,瞧見謝看過來一個個眼楮都亮了。
謝走近了,看了他們一圈,瞧了打頭的那個問“小糖?”
那男孩咧直笑,使勁兒點頭!
這邊練功的一群半大小子,比四年前長大了不,雖上了妝面一時看不清誰是誰,但從他們那份兒熱裡不難認出,正是當初白明禹救下、謝親手排了一場《白猿獻壽》送進尚玉樓戲班的那些孩子們。
謝用目數了一下,也難得小糖帶得用心,十一人,竟一個都不。
謝從懷裡拿了一個荷包出來,給了為首那個男孩,眼楮裡難得帶了一笑意,低聲道“不錯,給你們帶的,拿去吃吧。”
小糖收了荷包,鼻尖了,聞到甜的味道混著陳皮清香,打開果然瞧見滿滿一荷包藥糖,五六的,一瞧就有食。他們唱戲,吃東西上有講究,自就約束極嚴格,能吃的糖果也就偶爾幾顆藥糖,這裡頭帶了薄荷和熬的羅漢果,能養嗓子。
Advertisement
小糖想站起來同謝說話,但還未起來,謝手就按在他肩上略微用力“練你們的,我就來瞧一眼,見你們都好,也就沒什麼事了,先走一步。”
眾年依依不舍,但也都聽謝的話,點頭應了。
下午時分,尚玉樓登場。
戲樓裡請的人會來這裡,就已心裡有數,他們也都是人,輕易不願得罪白家,雖吃了點啞虧,但白家人又設宴又請人打圓場,也就認了,權當掏錢朋友,一時間吃酒的吃酒,聽戲的聽戲,賓主盡歡。
尚玉樓連唱兩場,博得滿堂彩。
等到華燈初上,宴席也進行到了最熱鬧的時候。
還剩最後半場的時候,後臺出了事故。
原本要唱一出《大鬧天宮》,但偏偏後臺一個武生不甚扭傷了腳。
所有打戲裡,猴戲最難,也最看真本事,別說傷了腳,即便完好無損也都得時刻小心,戲裡翻騰的多,打鬥也多,且南坊一時半會也找不到武行來接班,只剩一半收尾,若是砸了東家的買賣,他們戲班聲譽也完了。
尚玉樓急的團團轉,算來算去,怎麼都一人。
不過還有一刻鐘就要登臺,就算大變活人也來不及了。
尚玉樓咬咬牙,只能讓人去找白家的人,打算實在不行自己再唱一場,替換了劇目。
謝聽信趕到後臺,尚玉樓見他十分慚愧,躬行禮“小謝,實在對不住,我這裡人手不齊,剛才一個孩子傷了腳,不能登臺了,不如我再上去唱一回?當然,這是我戲班失誤,兩回也是應該,全聽主家的。”
若是白虹起安排的,也就罷了,但這出戲是臺下一位老掌櫃點的,已唱了一半,實在不好改。
謝旁的一人問道“給他換個不打的角,隻跟著跑兩步呢?”
Advertisement
尚玉樓苦笑道“若要上,也是可以,只怕下來之後腳就廢了。”
謝過去蹲下看了下,扭傷腳的年正被小糖等人圍著,他們見謝過來讓開一個位置,小糖挨在謝邊低聲飛快道“樓梯上被人抹了油,原是不會傷這麼狠的,他個子高,墊在下頭接了我們兩個人才……”他年紀尚小還不會遮掩緒,說到後面帶了鼻音,見尚玉樓過來低聲道“班主不讓說。”
尚玉樓是個戲癡,對戲、對戲班要求都嚴格,戲班出了事,這人也不會怨怪到主家上,開口依舊是想辦法找補,還是想自己上臺。
謝聽他嗓子沙啞,知道他奔波趕路,今日唱上兩場已是極限,再累要傷了嗓子,搖頭拒絕了。
他沉片刻,道“你找個隻翻跟頭不開口唱的,我去。”
尚玉樓愣了片刻,驚喜道“你肯去?”
謝點頭。
尚玉樓立刻重新安排了,回對謝道“小謝,你還有什麼要求?”
謝想了想,道“給我找把趁手的兵,結實點的。”
尚玉樓“啊?”
前臺,宴席上。
鑼鼓響了一次,還未有人登場,引得下頭人紛紛議論,坐在後排的也不知是哪一家,還吹了口哨,催著人出來。
前頭琴師額頭上冒了汗,鑼鼓又響一遍,這回,角兒登場了。
隻剛一亮相,迎頭一個倒彩。
尚玉樓隔著幕簾,掀開一隙查看,眼神很快落在最後一排,那裡黑乎乎的一時也看不清坐的都是什麼人。他從藝多年,還是頭一回踫上這種事,一邊擰眉一邊低聲吩咐戲班裡其他人要格外小心,但話還未說完,聽見前面接著又是一個倒彩。
尚玉樓心想不好,今日這是有人故意找岔子。
Advertisement
越是擔心什麼,就越來什麼。
一把茶壺從臺下猛地擲過來,正沖口中唱詞的“猴王”門面,那人偏躲過,但裡的唱詞也被突如其來的驚嚇打斷,一時破了功。
後排果然又是一陣哄笑,有人站起,一黑綢卷了袖子指了臺上嚷道“瞧瞧,也不過如此罷了!這白家請大夥兒看的戲,也不過如此!”
有這麼一個茶壺帶頭,跟著就扔了其他東西,有些落在臺上,有些砸到前排宴席賓客的桌上,把客人嚇了一跳,好些都急急忙忙要走,但到了門口,卻被堵住了路,不讓出去。
後排的人走上前來,為首的是三十來歲的男人,一黑綢緞錦袍,臉蒼白眼神鷙。他盯著臺上,正一邊轉手上的翡翠扳指一邊好,他這邊喊一聲,後跟著的十幾個黑打手也跟著喊一聲,只是聲音不齊,還有吹口哨的,一聽就是故意喝倒彩。
他們這一鬧,其余賓客也不敢再坐著了,額頭上都冒了汗,瞧了左右跟白家人低聲道“我,我忽然想起家裡還有些事,實在耽擱不得,不若我先回去?改日再設宴,回請白掌櫃。”
白家作陪的人也瞧出有人鬧場,連忙讓護衛送了對方離開。
半路上卻被那幫打手攔住,走在前頭的男人開口道“各位掌櫃的慌什麼,再聽一會,好戲還在後頭。”
賓客裡有認出他們是幫會打扮的,不想惹事,拱手道“這位好漢,我們只是來吃頓飯、聽個戲,不如放我們回去吧?”
黑男人似乎很滿意他膽小的樣子,心大好笑了幾聲。
他不發話,後的幾個打手就不放人,他們統一打扮,人也長得壯,顯然有備而來,在那推推搡搡就不讓人通過。
黑男人咳了一聲,低聲說了句什麼,他後的打手抓起旁邊桌上的一隻茶壺,又扔上了臺!
這次被臺上的一位仙君妝扮之人用手中齊眉反手打下,茶壺摔到對方腳下,濺起熱水,正撒在黑男鞋面上。
黑男人臉不好,罵了一聲“找死!”
他後兩個打手跳上臺來,一腳把臺上的案臺椅子踹倒,罵道“我看你們幾個臭唱戲的是活得不耐煩了——”他話音未落,就被“仙君”迎頭劈了一,哀嚎一聲就地滾了一圈。那打人的武生上了油彩,模樣英俊凌厲,氣勢段十分醒目,帶著不把對方放在眼裡的高傲,踢又踹翻一個,也不等臺下人有反應,一聲不吭,擺提起向腰際一塞,手持一齊眉,一個箭步跳下臺來,直奔鬧事之人。
擒賊先擒王。
打,就打當中帶頭喊得最響的!
謝一下去,臺上那幾個武生也不含糊,尤其是小糖等人,半大小子一把子力氣,也都起家夥,跟謝一同蹦下臺去與對方那幫打手們纏鬥起來。
兩邊都是十幾人,謝這邊一人能打個,手上子穩準狠,專門敲狗,一掃一片。
他這裡手,白明禹也跟著下了手,他邊常年帶了倆護衛,來宴席上也隻做小廝打扮,這會兒趁其不備撂倒了幾個打手。
那幫流氓不是對手,被打得吱哇,當中那個黑男人被謝打了七八,狼狽地在地上滾著也躲不過,被打急了眼想從懷裡掏家夥,謝手疾眼快一悶敲他前,把人打得差點吐出一口,跟著挑了對方懷裡的槍掃到一邊,喊道“白二,接著——!”
事發突然,但白明禹和他配合默契,拿腳踩了手槍撿起來。
“你可知我是誰?!你敢這麼對青龍會的人,小心我讓你吃不了兜著走,你不要以為我們就來了這麼幾個人,”黑男人又咳了一口,恨恨道“實話告訴你,大當家說了,你們今日誰敢為白家做事,就要砍斷他兩條!”
謝一腳踩他腦袋上碾著向地板,挑眉冷笑“回去告訴你們大當家,他但凡敢白家一下,我先挖掉他的兩隻眼楮!”
黑男人又痛又怕,他從未見過這樣的狠人,一時反而有些害怕了。
謝雖然放了狠話,但也對這人說的話留了心思,場地快打完了,忽然聽到戲院門口傳來聲響。
門推開,走進來一行人。
瞧見是幾個穿黑服的男人,謝心裡咯 一下,跟著卻瞧見那些人神慌張,雙手舉高在耳邊,後面跟著的卻是手持步槍、穿統一軍服的人,黑的槍管毫不客氣抵在他們腦後。
這幫人很快被按在牆邊控制住,後頭走進來的是一隊軍人,前後簇擁之人,卻沒有穿軍裝,隻穿了一件雪青貂皮大氅,量極高,步子緩而堅定,咳了一聲道“抱歉,今日宴席招待不周,外頭已清理乾淨,諸位可自行離去,改日白某再發帖,還請諸位賞。”
他讓人護送其余賓客離去,門外那些黑打手和場被控制的,一並捆起來,由後衛兵押走。
戲院裡頓時清理乾淨,隻余推翻的桌椅、撒落一地的瓷片水漬還未收拾。
白明禹站在那躬問好,給九爺請安。
戲班裡的人回了後臺,謝剛想跟著混過去,就聽到不遠九爺淡聲道“兒留下。”
謝腳步未,站在那,低頭不吭聲。
腳步慢慢走近,眼前映悉的靴子,謝手心冒汗,不知為何頭髮。
九爺站到他跟前,拿手抬起他下,仔細瞧了一會。
看得太久,謝忍不住抬眼飛快看了對方,視線相撞,一顆心跳得更快了。
九爺拇指輕輕挲他下,忽然笑道“怎麼,一年不見,不認得了?”
謝一白戲服,腰束得不足一握,面上的妝是尚玉樓所繪,因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仙君,並未多著墨,隻抹了眼尾一抹紅。謝模樣太過搶眼,即便如此,也是全場最俊俏的一個仙君,若不是臺上打鬥突然,只怕已得了不喝彩,這會兒“仙君”被抓了個正著,一雙眼楮水汪汪的,半點沒有剛才打架的氣勢,瞧著乖順的很。
猜你喜歡
-
連載9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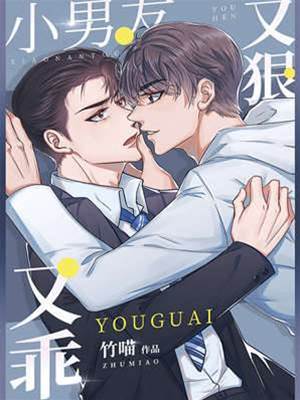
小男友又狠又乖
江別故第一次見到容錯,他坐在車裡,容錯在車外的垃圾桶旁邊翻找,十一月的天氣,那孩子腳上還是一雙破舊的涼鞋,單衣單褲,讓人看著心疼。 江別故給了他幾張紙幣,告訴他要好好上學,容錯似乎說了什麼,江別故沒有聽到,他是個聾子,心情不佳也懶得去看脣語。 第二次見到容錯是在流浪動物救助站,江別故本來想去領養一隻狗,卻看到了正在喂養流浪狗的容錯。 他看著自己,眼睛亮亮的,比那些等待被領養的流浪狗的眼神還要有所期待。 江別故問他:“這麼看著我,是想跟我走嗎?” “可以嗎?”容錯問的小心翼翼。 江別故這次看清了他的話,笑了下,覺得養個小孩兒可能要比養條狗更能排解寂寞,於是當真將他領了回去。 * 後來,人人都知道江別故的身邊有了個狼崽子,誰的話都不聽,什麼人也不認,眼裡心裡都只有一個江別故。 欺負他或許沒事兒,但誰要是說江別故一句不好,狼崽子都是會衝上去咬人的。 再後來,狼崽子有了心事,仗著江別故聽不到,在他看不見的地方悄悄說了很多心裡話,左右不過一句‘我喜歡你’。 後來的後來,在容錯又一次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江別故終於沒忍住嘆出一口氣: “我聽到了。” 聽力障礙但卻很有錢的溫文爾
56.5萬字8 6649 -
完結388 章
穿成男頻文裡的惡霸炮灰
《帝業》一書中,男主霍延出身將門,因朝廷腐敗,家破人亡,入慶王府為奴。 慶王世子心狠跋扈,霍延遭受欺辱虐待數年,幾次差點傷重而亡。 直到亂世來臨,他逃出王府,一步一步執掌兵權,霸圖天下。 登基後,將慶王世子五馬分屍。 樓喻好死不死,穿成下場淒慘的慶王世子。 為保小命,他決定—— 廣積糧,高築牆,緩稱王。 種糧食,搞建設,拓商路,興兵甲,在亂世中開闢一條生路。 漸漸地,他發現男主的眼神越來越不對勁。 某一天敵軍來犯,男主身披鎧甲,手執利刃,眉目英俊宛若戰神降臨。 擊退敵軍後,他來討要獎勵—— 浮世萬千,惟願與君朝朝暮暮。
81.3萬字8 10096 -
完結253 章

助理建築師
建築系畢業生張思毅回國求職期間,在咖啡館與前女友發生了爭執, 前女友憤怒之下將一杯咖啡潑向他,他敏捷躲閃避過,卻讓恰巧起身離席的隔壁桌帥哥遭了秧。 隔日,張思毅前往一家公司面試,竟然發現面試自己的人正是替自己挨了那杯咖啡的帥哥! 心如死灰的張思毅本以為這工作鐵定沒戲,不料那帥哥「不計前嫌」地錄用了他,還成了他的直屬上司。 當張思毅對帥哥的善良大度感激涕零之時,他還不知道,自己「悲慘」的命運這才剛剛開始…… 張思毅:「次奧,老子就害你被潑了一杯咖啡,你特麼至於嘛!TAT」
65.8萬字8 298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