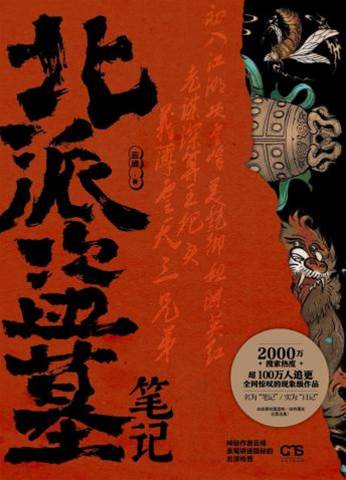《黑水屍棺》 第七十六章 耿師兄
仙兒也留意到了壬雅的眼神,就試探著對壬雅說話:「你能看見我?」
壬雅好像沒聽到仙兒的話,還是目不轉睛地看著,過了好久才說了一句:「好漂亮的姐姐!」
果真能看見仙兒!
我有些驚奇地問壬雅:「你也能開天眼嗎?」
的眼睛還是盯著仙兒,上卻對我說:「對啊,我從生下來就有天眼呢,羨慕吧……咦?你剛才說『我也能』,難道你也有天眼啊?」
一邊說著這番話,還將視線挪到了我的臉上,盯著我看了一會,突然吐了吐舌頭:「你長得好兇。」
看到梁厚載的時候,說梁厚載好看,看到仙兒說仙兒漂亮,到了我這,卻說我長得兇。
我招誰惹誰了我!
雖然我也知道,這些年跟著師父練功,上的氣催生出了一子微弱的煞氣,的確會讓人有點不舒服,外加我的眼睛長得小,遠看上去就是一條,梁厚載也說,我這雙眼睛很得我師父的髓,尤其是我看人的時候,跟我師父瞇起眼來看人的時候一樣一樣的。可我麵板白啊,不是說一白遮百醜麼,我也不至於這麼不招人待見吧。
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有人評論我的長相,上來就說我長得兇,過去我還以為自己對相貌這種事不在意,可這時我才明白,其實我還是在意的。
仙兒一下就樂了,賊兮兮地沖我笑:「你看,我就說你不討孩子喜歡吧,你長得太兇。哈哈哈哈,長得兇,完了,你這輩子註定要孤獨一生了。」
仙兒的話本來就弄得我心裡一陣煩,壬雅這時候又不早不晚地問了我一句:「你不會是來打劫的吧?師姐,這裡有個劫道的!」
呂壬霜轉過頭來,狠狠瞪了壬雅一眼:「蕭壬雅,不要胡鬧!」
Advertisement
這這才知道壬雅這丫頭姓蕭。
看得出來,呂壬霜對於壬雅來說還是很有威懾力的,壬雅當場吐了吐舌頭,之後就跑到壬霜邊,抱著壬霜的胳膊,一副撒的模樣。
仙兒好像對壬雅很有好,這時也從我肩膀上鑽了出去,找壬雅聊天去了。
自從仙兒為我的伴生魂之後,這還是第一次離我這麼遠,在離開我的那一剎那,我整個人都變得昏昏沉沉的,好像裡有什麼東西被帶走了一樣,就連走路的時候,兩都莫名地有些發。
呂壬霜帶著我們進了東市的一條小路的時候,我就聽仙兒在對壬雅說:「我跟你說啊,你年紀還小,不要這麼早男朋友。你看那個梁厚載,一臉桃花相,你可不要和他一起玩。」
壬雅忽碩忽碩地眨著眼睛,看著仙兒,說:「我才沒看上他呢,就是看他很靦腆的樣子,想逗逗他來著。哎,你怎麼住在那個打劫的上啊?」
仙兒:「我是他的伴生魂。你是不知道他那人,可討厭了,你不要跟他說話。」
壬雅竟然還很認真地朝仙兒點頭:「嗯,我纔不理他呢,一看就不是好人。哎呀,姐姐你是他的伴生魂啊,那你可不慘了,要天天和他在一起?」
仙兒裝模作樣地嘆了口氣:「唉,可不是嗎,我從今以後,怕是都要跟著他了。」
仙兒說話的時候,轉過頭來朝我微微一笑,給了我一個莫名其妙的眼神。
我看不懂的眼神,隻是有種覺,覺這次仙兒看我的時候,沒有了那種慣有的玩笑意味,反而多了一份很奇怪的溫和,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溫和,總之就是和對視的時候,心裡好像有什麼東西被了,心窩裡暖暖的。
Advertisement
沒多久,壬霜就帶著我們來到了小路盡頭一間店鋪,進門的時候,我發現店門上也掛著一盞的燈籠,可那就是一個禿禿的燈籠,上麵一個字也沒寫。
屋裡的擺設很簡單,一張老木頭打的長桌,還有幾把椅子,在屋子的當中央,坐著一個穿唐裝的中年人,此時他正端著一盞茶,細細品著。
壬霜朝那個中年人行了禮:「耿師叔。」
壬雅也著臉朝中年人笑:「師父。」
眼前這個人,就是之前壬霜向我提過的耿有博師兄,他不慌不忙地抬起頭來,分別朝壬霜和壬雅笑了笑,之後又轉向了我,用很平和的語氣對我說:「是有道師弟吧,幾年不見,長大了。」
不管是舉手投足,還是說話的神態,耿師兄的上都著一種事不驚的沉靜,聽到他說話的時候,我的心都跟著平靜了下來。
我也學著壬霜的樣子,朝耿師兄抱了抱手:「耿師兄。」
和莊師兄、馮師兄在一起的時候,我向來是很隨意的,從來沒有這麼鄭重地行過禮。可在麵對耿師兄的時候,我卻會不自覺地鄭重起來。
耿師兄朝我揮了揮手:「師弟,過來坐。」之後他又對壬雅說:「壬雅,去,打些熱水回來。」
別看蕭壬雅在我們麵前是一副口無遮攔的樣子,可在師父麵前,卻顯得十分乖巧,耿師兄話音剛落,就跑出去打水了。
我坐在耿師兄旁的位子上,耿師兄又招呼梁厚載和呂壬霜,讓他們自便,之後才對我說:「我聽說,今年的大市,九封山的人也要來?」
耿師兄說話的時候不帶任何的**彩,可我卻能覺到,他是接下來可能要和我商量什麼事。
說句實在的,自從我拜師門以來,能見到的同門,不是我的師叔師伯,就是我的師兄,要麼就是壬霜、壬雅這樣的師侄。對於長輩和師兄來說,我隻不過是個沒長的半大小子,對於師侄們來說我雖然年齡小,在師門中卻有著高於他們的輩分。
Advertisement
長輩和師兄們對我嗬護有加,師侄們對我都很尊敬,隻有耿師兄會把他放在和他同樣的高度,和我商量一些事。
我也是進師門以後第一次有種很平等的覺,不得不說,這樣的一份平等,在一瞬間就拉近了我和耿師兄的距離。
壬雅這時提來熱水,衝上了茶,我端起茶盞,小小抿了一口,才對耿師兄說:「我也是之前聽馮師兄提過這事,不過我也是第一次來鬼市,也不知道九封山是幹什麼的。」
「是個很特殊門派。」耿師兄一邊用左手的食指輕輕敲打著桌子,一邊說:「九封山的那群人,是咱們這個行當裡訊息最靈通的一群人。嗬嗬,今年他們一來,我的生意,怕是沒得做嘍。」
耿師兄說這番話的時候,苦笑了兩聲,可我發現他說話的時候還很正常,笑起來的時候,那聲音就異常的乾,就好像有人掐著他的嗓子,讓他難以發出聲音來。
耿師兄喝了一口茶,似乎是想潤潤嚨,過了片刻之後才又問我:「我柴師叔過去沒跟你提過九封山的事嗎?」
如果換是莊師兄或者馮師兄問我這句話,我肯定會很直接地說「沒有」。
可在麵對耿師兄的時候,我的嗓音卻變得特別矯:「確實沒有提起過。」
我就覺,如果我不這樣作態的話,就對不起耿師兄的那份沉穩淡雅似的。
我甚至都覺得自己平時說話的樣子有點低俗不堪了,可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覺。
梁厚載大概也有同樣的覺。別看梁厚載長得文靜,可他平時喝水吃飯的樣子,比我師父也好不到哪去。可如今他卻穩穩地坐在椅子上,手裡捧著茶盞,一口口地抿著,顯得不慌不忙。
我知道,梁厚載現在的樣子,絕對是他著自己裝出來的。
Advertisement
就在一分鐘之前,我還覺得耿師兄大概是個很親和的人,可現在,我卻想離開他的店鋪了,我不是討厭耿師兄,就是怕萬一我哪句話說得不合適,會讓他看不起我。
耿師兄似乎還想問我什麼話,好在這時候店裡來了客人,耿師兄隻能放下茶盞,帶著些歉意地對我說:「有道師弟不如去西市看看,我記得那裡有一家養行,你肯定會興趣。」
其實耿師兄這就是在下逐客令了,正好我也不打算待下去,就向耿師兄道了別,由壬霜帶著去了西市。
這就是我和耿師兄第一次見麵的全部過程,很短暫,也沒有產生什麼太大的集。甚至在一段時間以後,我差點就把耿師兄的樣子給忘了。
可就是這無比短暫的一次見麵,讓耿師兄記住了我,在我二十歲到二十五歲的那五年裡,耿師兄給予我的幫助和影響,一點也不比莊師兄和馮師兄。
當然,那些都是後話了。
聽聞耿師兄提到了「養行」,我就很想去看一看。
早在遭遇銅甲的時候,梁厚載就提到過養人,也就從那時候開始,對於養這個神而古老的行當,我心中就充滿了好奇。
我們之前路過西市的時候,這裡還沒有幾家店鋪開張,可這才過了多久,那些土房的門樑上就已經掛滿了紅的燈籠。
西市這裡的門頭,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做什麼生意的都有,我一邊走著,一邊走馬觀花似地掃視著燈籠上的文字。
猜你喜歡
-
完結3158 章

鎮妖博物館
世之反常為妖 物之性靈為精 魂之不散為詭 物之異常為怪 司隸校尉,舊稱臥虎,漢武帝所設,治巫蠱之事,捕奸滑之徒。 全球範圍內的靈氣和神秘復甦,人類摸索著走上修行道路,潛藏在傳說中的妖精鬼怪一一浮現,陰影處仍舊有無數邪魔晃動,一間無人問津的博物館,一面漢武帝時期的刻虎腰牌,讓衛淵成為當代最後一位司隸校尉,帶他前往古往今來諸多妖異之事。 古今稀奇事,子不語怪力亂神,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姑且斬之。 一柄八面漢劍,斬盡魑魅魍魎。 生死當定,天道存心。 當最後衛淵終於能在和平歲月裡,躺著木椅瞇眼曬太陽的時候,背後的博物館裡已經封印了無數的妖魔鬼怪。
983.9萬字8 13598 -
連載144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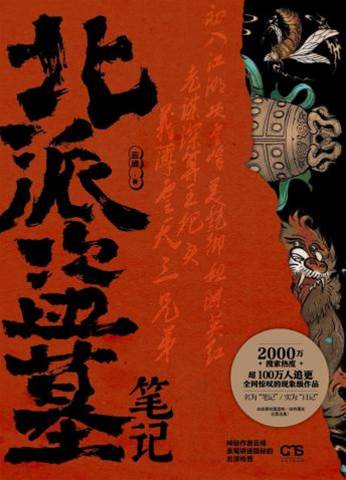
北派盜墓筆記
【盜墓+懸疑+鑒寶】我是一個東北山村的窮小子,二十世紀初,為了出人頭地,我加入了一個北方派盜墓團伙。從南到北,江湖百態,三教九流,這麼多年從少年混到了中年,酒量見長,歲月蹉跎,我曾接觸過許許多多的奇人異事,各位如有興趣,不妨搬來小板凳,聽一聽,一位盜墓賊的江湖見聞。
298.6萬字8.18 107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