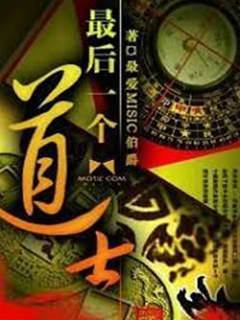《喪屍危機末日》 第27章 掙扎!(下)
“別……別過來!”
張鬱倒坐在地面上,拼命地後退著,一邊後退還一邊瘋狂地大,然後還拿著刺刀刺向那一雙雙手,企圖讓它們的手臂膀遠離自己。張鬱甚至還看見了只剩下骨架的手掌,最令他噁心的是,那隻剩下了骨架的手掌竟然還在不停地著,似乎還想在一瞬間將張鬱揪扯住,然後盡地撕咬扯啃。
“啊啊啊!”
張鬱也不敢再刺刀進行攻擊或是阻擋那些手臂了,一邊大著一邊在公路上匍匐了起來,他的目標就是要爬進公路兩邊的樹林中,然後利用樹木進行掩護,就這般將大部分的喪阻攔在外邊。
張鬱也不再仔細分析這個方法的功機率有多大了,只有一個念頭在腦海中浮現著,只要等到安傑過來,那就得救了。
張鬱甚至也不明白,他爲什麼會對安傑有那麼大的信任,他甚至還堅信著,安傑一定有辦法能從這個喪堆中突圍出去。
(呵呵,沒想到,我也會有依賴別人的那麼一天啊……)
(安傑,你這個混蛋究竟在幹嘛啊!)
張鬱用牙齒狠狠地咬住下脣,頭也不回拼命地匍匐著,事實上,張鬱本就不需要回頭,一回頭首先見到肯定是一雙雙乾枯的手臂膀,接著絕對就是手臂膀之上猙獰的面龐,那些面龐不得一下子就將張鬱撕扯碎片。
Advertisement
“嗷嗚!”
張鬱還沒有反應過來,三四隻喪竟然就直直地撲到了他的上,接著就齊刷刷地張開了猩紅的,對著張鬱的軀就狠狠地咬了下去。
“啊!”
張鬱此時纔回過神來,驚恐地大了一聲,連忙就將翻轉過來,雙手橫握著獵槍,就快速地朝著它們的塞了過去。
“咔咔咔!”
絕對是彩到的一個場面,那些喪的離張鬱的軀已經不過七八公分了,只要再向下推進一的距離,那麼張鬱絕對就會痛得死去活來。但就是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刻,張鬱的那桿獵槍竟然就直直地塞進了它們的中,讓得它們的利齒就直直地 咬在了槍桿上。
張鬱沒有毫的放鬆,或者說,他本就不敢放鬆毫,附近的喪也朝著他撲了上來,如果待到喪越聚越多的時候,他絕對會落到一個被撕扯無數碎片的下場。
以此同時,咬住了槍桿的那幾只喪也在拼命地著,揮舞著雙手朝著張鬱撲來,張鬱自然是不可能就這般,由得它們的牙齒掙掉獵槍槍桿,一旦它們的牙齒離開了那裡,沒有任何東西塞住的,下一個目標可就是自己了啊。
“啊!”
張鬱拼命地大著,然後發起被它們死死制著的大,往這幾隻喪的下狠狠地踹了過去,企圖將它們踹開。但是,這幾隻喪竟然出其地勇猛,本就不理會張鬱的攻擊,依舊嗷嗷大地啃咬著槍桿,然後拼命地往張鬱的臉蛋推上來,它們的脣部甚至都已經被磨得爛掉了一塊,暗紅的凝固就這般滴在了張鬱的服上。
Advertisement
張鬱是徹底地沒有毫的辦法了,那幾只喪的,甚至都已經被他踹掉一塊塊大了,其中一隻喪的腹部,甚至還被他一腳踹開了一個大豁口,腥臭、膩膩的大腸一下子就落到了張鬱的部。但是反觀這幾隻喪,依舊拼命地啃咬著那桿獵槍,它們牙齒甚至都被畸形了,但它們還是瘋狂地推了上來。
“啊啊啊!”
張鬱的面容已經快要擰麻花狀了,他聲嘶力竭地大喊著,然後雙手也加大了力量,將那桿獵槍又再度推離了二十多公分, 這時,張鬱才鼓著眼睛死死地盯著那幾只喪,恨不得將它們全都碾醬。
與此同時,有幾隻喪搖搖晃晃地走到了張鬱的腦袋瓜子前,接著,它們更是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況下,忽地就扭曲起了麻花一般的面龐,擰大了就朝張鬱撲了下來。
霎時間,張鬱的眼角餘立即就瞥到了這幾隻新加的喪,更令張鬱難忘的是,那幾只喪扭曲的面龐,竟然,竟然是朝著他這邊撲來的。張鬱嚇了一跳,眼睛猛地就瞪了一個汽車燈般大小,然後就瘋狂地扭起了子,試圖掙扎掉上的這幾隻喪。
張鬱的掙扎依舊沒有毫的作用,它們依舊死死地制著他的,他幾乎就快要發瘋了,眼見著那幾只喪越來越接近,眼見著只有不到幾步之遙。張鬱更是瘋狂地扭著子,眼睛死死地盯著那幾只喪,試圖在它們到來之前掙掉上的制,張鬱額頭上甚至都冒出了黃豆般大小的汗滴,全上下幾乎都是在瘋狂地抖著。
Advertisement
“啊啊啊!”
終於,那幾只喪終於是到達了張鬱的腦袋前,張鬱並沒有放棄掙扎,他的眼睛死死地盯著那幾只喪,死死地盯著它們扭曲麻花一般的面龐。
“嗷嗚!”
在張鬱驚恐的目中,那幾只喪瘋狂地嘶吼著,猛地就撲了下來,然後扭曲著面龐張開了,以尖銳的利齒就朝著他的面龐撕咬了過來。
(終於,要結束了嗎……)張鬱的呼吸竟然變得急促了起來,也終究是閉上了絕的雙眼,等待著痛苦的降臨。
“嘭嘭嘭!”
正當張鬱絕地閉眼等死之際,三道槍聲立即就從前方傳了過來,激地張鬱打了一個激靈,立馬就睜開了眼睛。
“啊!”
就在張鬱睜開眼睛的那剎那間,他立即就嚇得大了起來,臉蒼白得如同白紙一般,就連俊俏的面容也變得扭曲了起來。
首先映張鬱眼簾的竟是一張近在咫尺的猙獰面龐,這張臉有一半幾乎都是腐爛的了,臉上還存在著幾道猙獰的綻口。這並不是嚇得他大的原因,就在他剛剛睜開眼的那剎那,這張噁心的面龐,竟然直直地對著他的腦袋就撲了下來,然後徑直地覆蓋在了他的面龐上,任何一個人都會被這突兀的覺嚇到手腳發。
被嚇到,放棄了掙扎!
猜你喜歡
-
完結5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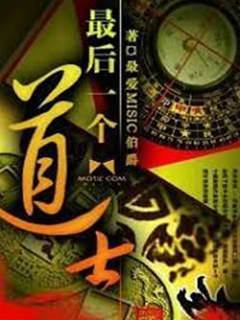
最後一個道士
查文斌——中國茅山派最後一位茅山祖印持有者,他是中國最神秘的民間道士。他救人於陰陽之間,卻引火燒身;他帶你瞭解道術中最不為人知的秘密,揭開陰間生死簿密碼;他的經曆傳奇而真實,幾十年來從未被關注的熱度。 九年前,在浙江西洪村的一位嬰兒的滿月之宴上,一個道士放下預言:“此娃雖是美人胚子,卻命中多劫數。” 眾人將道士趕出大門,不以為意。 九年後,女娃滴水不進,生命危殆,眾人纔想起九年前的道士……離奇故事正式揭曉。 凡人究竟能否改變上天註定的命運,失落的村莊究竟暗藏了多麼恐怖的故事?上百年未曾找到的答案,一切都將在《最後一個道士》揭曉!!!
129.6萬字8 14479 -
完結3506 章

六指詭醫
先天左手六指兒,被親人稱為掃把星。出生時父親去世,從小到大身邊總有厄運出現,備受歧視和白眼。十八歲受第三個半紀劫時,至親的爺爺奶奶也死了,從此主人公走上了流浪之路。一邊繼續茍延殘喘自己的生活,一邊調查謎團背后的真相,在生與死的不斷糾纏中,我…
661.4萬字8 13677 -
完結168 章

鬼王的嬌妻養成計劃
"死了幾千年的老鬼終于娶上媳婦了ヾ(◍ ° ㉨ ° ◍)ノ゙ 可是,媳婦才六歲怎麼辦? 只好慢慢的養著唄,陪著唄~"
43.4萬字8 84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