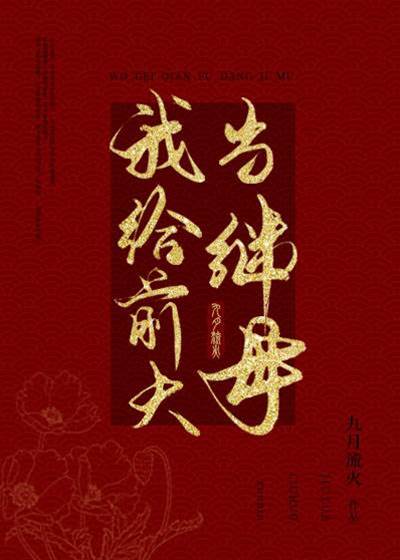《他定有過人之處》 第四章
長孫信開始頭疼。
此行之所以選擇幽州,除去這裡適合開探之外,也是長孫家有心暫時遠避長安朝局鋒芒。
隻是他萬萬沒想到,剛到這裡就讓妹妹遭遇了故人。
山宗這個人,當年在貴族子弟裡是名滿二都的厲害人,風頭無限。山家又是一方名門豪族。作為一樁世家聯姻,神容嫁給他算得上金玉良緣了。
隻是才半年這二人就勞燕分飛,實在出人意料。
神容當初返家時,張口就道夫君死了,長孫信是不信的。
那天追著神容返回的,還有一隊本該護送的兵馬和山宗的侍從。
長孫信特地見了那侍從,才得知前後詳細山宗不是死了,而是走了,給了和離書就離開了山家。
侍從隨之向他呈上一張單子,說是夫人走得太急,落下的。他們一路追來,正是為了這個。
單子上列著山宗給神容的補償。
當朝有律,凡夫婦和離,夫家需一次給清方三載糧。
山宗這張單子直截了當,給神容的,竟是他在山家所有。
哪怕坐吃山空,也足夠神容富足一生的。
長孫信這才相信山宗是真離開了山家。
不是簡單的離開,而是一下離了這豪門大族,走得乾乾凈凈。
若罵他薄寡義,還真未見過天底下哪個男人能對外放之妻做到如此慷慨的。
可他的確翻臉無,一句婚後沒有夫妻意就輕言別離。
長孫信卻最想罵他狡猾!
他離了山家,要問責就該找他本人,若是家族之間追拉牽扯,倒顯得長孫家不講道理。
長孫信甚至都有點欽佩他這說走就走的魄力。
山家那頭如何,因著顧及神容心,長孫家刻意沒有打聽。
後來隻聽說山家長輩對神容是極其不捨的,似乎還有來趙國公府走的意向,但也隻是聽說。
Advertisement
隻因那年國中多事,先是先帝立儲一番波折,險些釀出兵諫,之後北疆又有外敵侵擾。
朝局中,長孫家和山家都忙於應付,一時誰也顧不上誰。
而這樁本該掀起軒然大波的大族和離也無人太過關心,就這麼翻了篇。
一晃三年,全家上下都心照不宣地預設那人就是死了,免得惹他家小祖宗不高興。
誰想,那人如今竟然“詐了”……
驛館客房,長孫信想到這裡,皺著的眉頭還沒鬆。
也不知那姓山的是如何做到的,在這裡做了這麼久的團練使,竟一點風聲也沒有。
他朝旁看,神容坐在方方正正的小案旁,正低頭看著從祖傳木盒裡請出來的那捲書。
打從軍所裡回來,連著兩日,沒見有過笑臉。
長孫信打小就疼,又怕連捲上的字也看不進去了,那可就要壞大事了,湊近道“阿容,你若覺得不自在,我便幽州署安排,勒令那軍所的人都不得靠近咱們,離那姓山的越遠越好。”
神容從書卷裡抬起頭來“我為何不自在?我無過無錯,該不自在的是他,要迴避也是他迴避才對。若真如此行事,倒顯得我多在意他似的。”
長孫信視線在臉上轉了轉“你不在意?”
“不在意。”神容低頭,繼續看卷。
恰巧,門外來了個隨從,說是幽州刺史派人來請郎君了。
長孫信起,又瞄神容,見神如常,稍稍放了心“你既無事便好,我還需去見一見幽州刺史,如今幽州節度使的職銜是空著的,此地首便是刺史,後麵我們的事不得還要借他助力。”
神容隨意應了聲,聽著他出了門。
待到屋安靜,手上書卷合了起來。
其實早又想起軍所裡那一幕來,當時他就坐在那裡看了半晌,什麼意思?
Advertisement
越想越不對味,隨手扔開了靠著的墊。
“主?”紫瑞聽到靜,從門外往裡看。
神容端正跪坐,裝作剛才什麼也沒乾過,雲淡風輕地問“東來傷好了?”
“還在養。”
“那你還不去照應著?”
紫瑞忙稱是,離開了門口。
神容將那墊又扔了一遍。
冷不丁的,外麵傳來個男人炸雷似的呼喊“快點兒!人馬上到了……去去去,管那些狗屁貴人做甚,擾了他們算什麼,誤了事纔要命!”
這聲音嘎的很,一下神容回想起來,是那日吵醒的那個。
收起書卷,走去窗邊。
院角裡鉆出個大鬍子男人,風風火火地朝後方大呼小“快啊!媽的,腳了不!”
神容正倚在視窗看著,一名護衛悄然過來,請示是否要將他們驅逐。
搖頭,他們都退下。
好好的探地風被耽擱了,正好沒出氣呢,現在既然遇上了,若再聽見一句不敬的,定要逮著這欠的殺一殺威風。
大鬍子還沒再開口,院外遙遙傳來了別人的喚“來了來了!”
接著是一陣馬嘶。
有人從外進了驛館,不止一人,腳步鏗然,仔細聽,像是馬靴踩地,混著兵甲護相擊之聲。
神容循聲看去,果然有隊兵穿廊進了院,領頭的還很眼。
可不就是那日在軍所裡擋了半天路的漢子。
那大鬍子看到他就喊“胡十一,是你來收人?”
漢子回“屁,可不止我來!”
神容白了二人一眼,扭開頭。
餘裡瞄見那大鬍子一溜煙跑了過去“山使,您親自來了。”語氣忽然恭謹無比。
“嗯。”
一下轉回頭去。
迴廊口,男人攜刀臂下,緩步而。
他是低著頭進來的,手中拿著張黃麻紙在看,一黑的腰胡,束發利落,長如鬆。
Advertisement
大約是出於警覺,站定後他便抬頭掃視院,隻兩眼,目就掃到視窗。
神容視線不偏不倚與他撞個正著,不自覺扶著窗框站直。
山宗與以前一樣,一張臉廓分明,目銳利,上似永遠帶著幾分不羈。
忽然想起很久前的一個午後,的母親取了一份描像去房裡,神神地給看。
瞄了一眼,輕描淡寫地評價“尚可。”
其母笑道“我還不知道你,能說出尚可,那便是很滿意了。”
沒承認,隻在母親將描像合上前又悄悄多看了一眼。
一張男人的側臉,走線如刀,英朗不可方。
據說是畫師煞費苦心才從描來給瞧的。
後來婚時站他側,瞄到的也是這張側臉。
對這張臉記得太清楚了,所以哪怕曾經他寥寥幾次返家都很短暫,彼此隻是倉促地見過幾麵,也能在軍所裡一眼認出他來。
也隻是一眼的事,山宗便轉過了頭“貨呢?”
大鬍子立即喊“快!貨了!”
他先前大呼小催著的幾個同伴陸續從院角鉆出來,推推攘攘地押著幾個披頭散發、裝束特異的人,那幾人被一繩子綁著串在一起,如死魚一般被扯過來。
山宗手裡的紙一,丟給胡十一“去驛丞張了。”
胡十一走了,大鬍子往他跟前走兩步,之前囂張氣勢全無,還賠了一臉的笑“山使,一共五個,兩個奚人,三個契丹人,咱們從邊境那裡捉到的。”
他點頭“乾得不錯。”
大鬍子頓時眉飛舞,彷彿了天大的褒獎。
山宗提上刀“將貨接了,自行去我軍所領賞。他們的住我要搜一遍。”
大鬍子忙給他指路,一麵絮叨“也不知怎麼就來了群狗屁貴人,將地方全占了,害得哥兒幾個隻得挪窩去那犄角旮旯裡。”
Advertisement
“是麼?”山宗笑了聲,往他指的那頭去了。
神容默默看到此時,盯著他走去的方向,回味著他那聲笑,忽也一笑,擺一提,轉出屋。
大鬍子正與山宗帶來的兵接那幾人,忽見遠那間頂寬敞的客房裡走出來個年輕人,曳地,臂挽輕紗,目不斜視地從旁邊經過。
他呆了一瞬,口就問“什麼人?”
“你罵過的貴人。”
大鬍子一愣,就這麼看著過去了。
神容此時沒有心管他,剛穿過院落,又有兩個護衛悄然跟來,再次被遣退。
獨自走過長廊,直到最偏僻的角落裡,看見幾間擁的下房。
門皆開著,似是被踹開的,鎖歪斜地掛著,搖搖墜。
剛走近,一襲黑的男人矮頭從正中那間走了出來。
神容與他撞個正著,隔了幾步站定。
輕輕掃了他兩眼,忽而開口“團練使是何等軍職?”
山宗撞見毫不驚訝,居然還配合地答了話“總領一方駐軍,負責練兵鎮守。”
神容如何不知,故意裝的罷了,挑著眉頭嘆“你離了山家,僅憑一己之力就坐穩了這一方軍首,可真是我欽佩。”
若是聽不出這話裡的反諷,那便是傻子了。但山宗提起角,拍了拍手上灰塵,還接了一句“那確實。”
神容蹙眉,猜他是不是又在敷衍自己,忽而想到一點,眼珠微“是了,你定是想裝作不認識我了。”
山宗眼睛看了過來。
長孫神容,他豈能不認識?軍所裡看見的第一眼就認出來了。
但他開口卻說“難道你我應當認識?”
神容臉緩緩繃了起來“我倒是認得你啊,山、宗。”
他的名字自口中說出來,有種別樣的意味。
兩人互相看著。
正當此時,胡十一找了過來,又一腳停住,因為看見了神容“是你!”
他心想頭兒分明已經道過歉了,這人莫非還不依不饒?聲氣道“這位貴人,今日咱們是來收押敵賊的,其他事可糾纏不起!”
神容隻瞄著山宗,並不搭理他。
胡十一吃了一癟,隻好向山宗稟報正事“頭兒,令已驛丞上了,山路一封,斷不會再外人進去了。”
神容立時看過去“你們要封什麼?”
“封山。”山宗眼從上轉開,換手提刀,往外走。
神容看著他從旁經過,他袖上護臂過臂彎裡的披帛,皮和,若有似無地牽扯了一下。
……
外麵敵賊收押,兵馬收隊,準備返回軍所。
胡十一追上山宗腳步“頭兒,我先前好似聽見那人直呼你大名了,你就隨去了?”他不知緣由,隻當神容猖狂。
山宗踩蹬一,坐上馬背“你耳朵靈。”
胡十一睜圓眼“若知道你在這幽州地位,斷不敢如此小瞧你!方纔你就該借機將那人逞過的威風回去纔是啊!”
山宗笑“你當我閑的是不是?”
胡十一在他笑容裡噤了聲,退後不瞎出主意了。
山宗振韁,策馬上路,莫名想起方纔那一聲喚名。
一個盡寵的高門貴,早該與他毫無瓜葛,如今怎會在這邊關之地重逢?
他定有過人之
猜你喜歡
-
完結284 章

末世歸來之全能醫後
驚爆!天下第一醜的國公府嫡女要嫁給天下第一美的殤親王啦,是人性的醜惡,還是世態的炎涼,箇中緣由,敬請期待水草新作《末世歸來之全能醫後》! 華墨兮身為國公府嫡女,卻被繼母和繼妹聯手害死,死後穿越到末世,殺伐十年,竟然再次重生回到死亡前夕! 麵容被毀,聲名被汙,且看精明善變又殺伐果斷的女主,如何利用異能和係統,複仇虐渣,征戰亂世,步步登頂! 【幻想版小劇場】 殤親王一邊咳血一邊說道:“這舞姬跳得不錯,就是有點胖了。” “你長得也不錯,就是要死了。” “冇事,誰還冇有個死的時候呢。” “也是,等你死了,我就把這舞姬燒給你,讓你看個夠。” 【真實版小劇場】 “你可知,知道太多的人,都容易死!”殤親王語氣冷漠的恐嚇道。 華墨兮卻是笑著回道:“美人刀下死,做鬼也風流啊。” “你找死!” “若是我死不成呢,你就娶我?” 【一句話簡介】 又冷又痞的女主從懦弱小可憐搖身一變成為末世迴歸大佬,與俊逸邪肆美強卻並不慘的男主攜手並進,打造頂級盛世!
49.9萬字8 16744 -
完結88 章

宮鬥不如養條狗
"狗皇帝"被"擋箭牌"寵妃收養,跟在寵妃身後經歷各種殘酷宮鬥並找到真愛的過程
26.9萬字8 9166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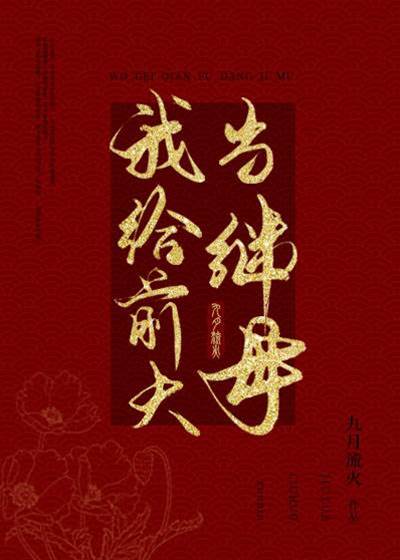
我給前夫當繼母
【微博:晉江九月流火】林未晞死了一次才知,自己只是一本庶女文中的女配,一個用來反襯女主如何溫柔體貼、如何會做妻子的炮灰原配。 男主是她的前夫,堂堂燕王世子,家世優越、光芒萬丈,而女主卻不是她。 女主是她的庶妹,那才是丈夫的白月光,硃砂痣,求不得。 直到林未晞死了,丈夫終於如願娶了庶妹。 她冷眼看著這兩人蜜裡調油,琴瑟和鳴,所有人都在用庶妹的成功來反襯她這個元妻的不妥當。 林未晞冷笑,好啊,既然你們的愛情感動天地,那我這個姐姐回來給你們做繼母吧! 於是,她負氣嫁給了前夫的父親,前世未曾謀面的公公——大齊的守護戰神,喪妻后一直沒有續娶,擁兵一方、威名赫赫的燕王。 後來,正值壯年、殺伐果決的燕王看著比自己小了一輪還多的嬌妻,頗為頭疼。 罷了,她還小,他得寵著她,縱著她,教著她。 #我給女主當婆婆##被三后我嫁給了前夫的父親#【已開啟晉江防盜,訂閱比例不足70%,最新章需要暫緩幾天,望諒解】*************************************************預收文:《難消帝王恩》虞清嘉穿書後,得知自己是女配文里的原女主。 呵呵……反正遲早都要死,不如活的舒心一點,虞清嘉徹底放飛自我,仗著自己是嫡女,玩了命刁難父親新領回的美艷小妾。 這個小妾也不是善茬,一來二去,兩人梁子越結越大。 後來她漸漸發現不對,她的死對頭為什麼是男人?他還是皇室通緝犯,廢太子的幼子,日後有名的暴君啊啊啊! ***本朝皇室有一樁不足為外人道的隱秘,比如皇室男子雖然個個貌美善戰,但是卻帶著不可違抗的嗜血偏執基因。 慕容珩少年時從雲端摔入塵埃,甚至不得不男扮女裝,在隨臣後院里躲避密探。 經逢大變,他體內的暴虐分子幾乎控制不住,直到他看到了一個女子。 這個女子每日過來挑釁他,刁難他,甚至還用可笑的伎倆陷害他。 慕容珩突然就找到了新的樂趣,可是總有一些討厭的,號稱「女配」 的蒼蠅來打擾他和嘉嘉獨處。 沒有人可以傷害你,也沒有人可以奪走你,你獨屬於我。 他的嘉嘉小姐。 註:男主偏執佔有慾強,祖傳神經病,女主虞美人假小妾真皇子與作死的嫡女,點擊作者專欄,在預收文一欄就可以找到哦,求你們提前包養我!
36.9萬字8.36 64041 -
完結109 章

懷嬌
被譽為世家望族之首的魏氏聲名顯赫,嫡長子魏玠品行高潔,超塵脫俗,是人稱白璧無瑕的謫仙,也是士族培養后輩時的楷模。直到來了一位旁支所出的表姑娘,生得一副禍水模樣,時常扭著曼妙腰肢從魏玠身前路過,秋水似的眸子頻頻落在他身上。這樣明晃晃的勾引,魏…
27.2萬字8 4658 -
完結730 章

萌妃天降:腹黑邪王惹不得
聽說,容王殿下點名要娶太傅府的那位花癡嫡女,全城百姓直言,這太驚悚了! 這幾個月前,容王殿下不是還揚言,要殺了這個花癡嗎? 太傅府,某花癡女看著滿滿一屋的聘禮,卻哭喪著臉,“來人啊,能不能給我退回去?” 京城貴女們紛紛爆起粗口,“求求你要點臉!”
131.4萬字8 76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