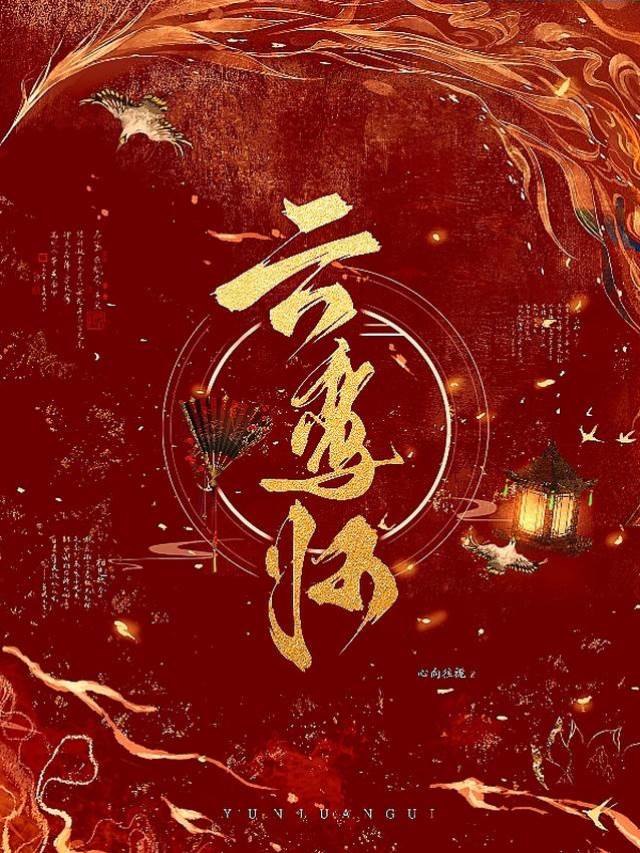《問鼎宮闕》 第39章 葡萄
賀玄時定一定氣,一壁著手心的一壁信手翻來。
書頁展開的那一刻,就把手鬆開了。
從他肩頭往前傾,兩個人一併看,他哈地一聲笑了:“《碩鼠》,碩姬?”
話剛出口,一記拳捶在他肩上:“難聽,臣妾不要!”
他卻興致地要提筆寫下:“可是你說要順應天命的,老天說了,你就是碩姬,要不鼠姬也行,你自己挑一個。”
便聽說:“尚宮局都是擬三個封號來選,皇上也得給臣妾翻三次!”
賀玄時撲哧笑出聲。
反應倒快。《詩經》裡好字眼那麼多,若真翻三次,不論怎樣都能翻出個好看的。
這玩法也有趣,他以哄的口吻連應了幾聲好,的手就又蒙了上來。
這回他剛一翻,便覺即刻向前湊了過去。
《采綠》。
他又笑:“綠姬?”
拳又捶他,眸也一瞪,接著手指書:“‘終朝采綠,不盈一匊。’臣妾喜歡那個盈字。”
“好,那先寫下來。”他欣然提筆,寫下一個“盈”字,想一想,又不懷好意地將“鼠”字也寫在了紙上。
鼠字剛寫兩筆就聽到一聲冷哼,背後的人頗是不滿,胳膊卻從肩頭搭來,將他一摟,口吻嗔:“皇上故意氣臣妾,臣妾偏不生氣。”
一已看穿人心就不讓他得逞的味道,酸溜溜的小聰明。
他含笑不說話,筆桿在額上一敲:“你自己翻一個。”
“不,臣妾手氣一貫不好……”這樣說,眼睛忽而一轉,又改了口,“哎,也好,臣妾自己翻一個!”
他出探究,不知又再什麼念頭,已很有興致地將書拿了過去,他便側坐過,抬手蒙了的眼睛。
低低一笑,抬手便翻,隻翻開薄薄兩頁。
Advertisement
待得他把手挪開,著那樣黛眉一挑,頗帶幾分謀得逞的得意,將書遞給他:“喏!”
他接來一瞧,書的第一頁是蓋著翰林院紅章的扉頁,第二頁有個簡單的書目,這是第三頁,也就是《詩經》的第一首。
《關雎》。
他捲起書來又拍額頭:“這作弊!”
“怎麼是作弊,臣妾可也是一下翻到的!”不承認,眉眼彎彎,一雙笑眼裡瞧著有甜的味道,“臣妾自問形尚可,‘窈窕’的‘窈’字可好?”
聲音,眉目含。
他原還想與繼續逗趣,卻被這聲音擾得心裡也了,深吸氣點點頭:“很適合你。”
儀態萬千而又靈越人,是為窈窕淑。
他提筆將這個字也寫下來,而後直接換了隻筆,蘸上硃砂,直接將“窈”字圈了。
繼而又是笑意促狹,將紙往樊應德那邊一遞:“給尚宮局送去。”
紙上還有“盈”和“鼠”兩個字呢。
樊應德摒著笑一躬就往外去,夏雲姒短暫地滯了一瞬便反應過來,忙提步去截他:“樊公公!”
樊應德走得倒不快,很快就被攔住,卻索著聖意不肯將紙給,躲來躲去地惹得著急。
夏雲姒圍追堵截,好一會兒才將紙搶到手裡。
背後不遠笑音清朗傳出,輕鬆爽快。
封號定下來,接下來便要等禮部擇定吉日行冊封禮了,但在行冊禮之前,封號與位份也都會先一步曉諭六宮,方便宮中稱呼。
“窈姬。”昭妃聽聞這個稱號的時候,冷臉在正殿的主座上沉默了良久。
窈窕淑,君子好逑。
皇上對還真是上心。
兩旁幾個平日跟隨昭妃的嬪妃都不敢說什麼,各自安安靜靜地坐著。
半晌,聞得一聲黯淡的輕笑:“好個窈姬,真是有本事,我們終是比不過的。”
Advertisement
幾人侷促不安地抬頭,相視一,又一同向昭妃。
其實昭妃在窈姬那裡落於下風已不是一天兩天,卻是頭一次這樣表出分明的頹喪。
胡徽娥艱難僵笑:“娘娘別氣餒……皇上心裡必還是念著娘孃的,對窈姬不過是一時新鮮。”
昭妃淡淡地瞟了一眼。
從前說皇上對夏氏好不過是看在佳惠皇後的份上照顧妻妹,如今眼瞧著不是那樣了,又說不過是“一時新鮮”。
何嘗不知們是在哄,也是在自欺欺人地哄自己?隻看皇上目下這勁頭,究竟是不是那麼簡單便清楚了。
胡徽娥見接話,不由麵上訕訕,兀自又思量了會兒,纔再度開口:“要興風作浪便由著去。隻是……臣妾覺得娘娘這樣按兵不也不是法子,采菁的事不明不白,皇上在氣頭上連娘娘一併怪罪也就罷了,娘娘總該想個法子為自己說說話不是?”
昭妃秀眉微擰,輕輕地沉下一口鬱氣。
采菁的事當真是不明不白,竟從不知采菁何時搭上了玉竹軒的如蘭、又為何膽大包天地要去給夏雲姒下毒。宮正司回話說人贓並獲、鐵證如山,還說采菁供出了采苓,道是為采苓辦的事,似乎也算個解釋,可又總覺得采苓沒有那樣的膽子。
其中更還有兩張大概永遠也說不清楚的惡毒符咒,采菁最終都沒招供。
卻也是這兩頁符咒,讓皇上愈加疑。
坐在下首的儀貴姬目有些閃爍,端起茶盞借著抿茶稍作遮掩,再放下茶盞時已深如舊:“胡妹妹的話不錯,隻是皇上現下一心繫在窈姬上,旁人貿然去討聖駕歡心,怕是反要弄巧拙。臣妾倒覺來日方長,聖恩也不急這一時,反是苓采那邊……娘娘若能有個孩子養在膝下更為要。”
Advertisement
在座幾人不約而同地都一瞧。
這是實在話。昭妃承寵幾年都沒能有孕,皇長子與皇次子那邊皇上又不肯鬆口,采苓這一胎昭妃當真是看重的。
本來昭妃將一切都安排好了,想借著采苓除掉夏氏再保住采苓的胎,未想竟突然殺出個順妃攪局,反惹得皇帝疑到昭妃頭上。
采苓遷去了順妃邊,孩子眼瞧著也要歸了順妃。昭妃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一切算計全便宜順妃了。
儀貴姬口吻輕慢:“且不說苓采若生個皇子該是多麼尊貴,就是得個公主,養在娘娘膝下總也比沒有強。皇上素來關心孩子,哪個宮有個孩子,皇上自會多去走,娘娘困局到時便也迎刃而解了。”
“這話貴姬娘娘說得輕巧。”胡徽娥秀眉鎖,一味搖頭,“娘娘瞧瞧當下的局勢,也知皇上斷不會輕易將孩子由昭妃娘娘養了。”
“哎,萬事無絕對麼。”儀貴姬淡泊抿笑,目投向昭妃,“皇上當日將采苓遣去順妃,是因覺得娘娘您犯了錯。可若目下順妃犯了錯呢?或許娘娘不僅能將孩子爭回來,還能洗從前的嫌隙也未可知。”
這話說得有竹,昭妃抬眸看,笑不改,清清淡淡地靜等昭妃發問。
之後的十幾日,整個玉竹軒都炙手可熱。
這十幾日裡皇帝都未再召幸過嬪妃,雖明麵上說的是政務繁忙,個中細由夏雲姒卻清楚。
——那日坐在城樓上,以退為進,說出的雖是不求他專寵,卻也表出了想得一心人真心相待的意思。他現下又在興頭上,自會肯事事順著,讓滿意。
夏雲姒並未因為他不召幸嬪妃就忙於投懷送抱,卻也沒有太過拿喬。他到底是萬人之上的帝王,耐心是有限的,張弛有度的拒還迎能讓他神魂顛倒,吊倒了胃口可就是另一番景了。
Advertisement
炎夏午後,去清涼殿時他恰正小睡,音問了樊應德他起床的時辰,樊應德道說也快了,最多再過一刻便要起來看摺子。
夏雲姒就端起桌上的琉璃小碗,躡手躡腳地到床邊。
琉璃小碗裡盛著碎冰,碎冰裡鎮著葡萄。坐到榻邊,仔仔細細地將薄皮剝凈,遂送到他邊。
輕輕一,涼意在上綻開。賀玄時蹙了下眉,轉而品到些許清甜。他眼皮微抬,的笑靨就映眼簾,令他一下子清醒了。
他含著笑張口將拈著的葡萄吃掉,翻了個,手一把將擁進懷裡:“膽子越來越大,看朕睡著也敢來搗。”
話是責備,卻全然不是責備的語氣。夏雲姒側倚進他懷中,笑容溫:“臣妾問了樊公公,樊公公說皇上快起了,臣妾纔敢來的!”
他在額上輕輕一啜:“可是有事?”
“沒事。”搖搖頭,口吻越發溫,“臣妾自己在玉竹軒待得沒趣兒,就尋過來了。”
這是近來常會有的說辭——有時是說“自己待著沒趣兒”,有時又是有些蒜皮的小趣事急急拿來與他分。
這樣的做法,自是為從細枝末節讓他覺得時時想著他,意無限,似水。
若這一切都是真的,應是甜得很,應該也會覺得甜得很。
可當下當然覺不到。
會這樣做,不過是回憶著姐姐與他的過往,照貓畫虎地在學陷在意裡的孩子什麼樣。
所幸學得還不錯,雖不足以騙過自己,卻足以騙過他。
他手往床邊小幾上一探,從琉璃碗中又出顆葡萄,同樣細心地剝了皮,反手喂進口中。
檀口輕啟,將碧盈盈的葡萄吃進口中。酸甜從清涼裡綻開,迅速遍佈滿口。
但往下一咬,不甚咬破了葡萄籽,頓覺又苦又,比方纔的甜要真實得多。
將這顆葡萄囫圇吞下去,眼簾低低垂著,手指輕佻地絞著他的領口:“皇上多躺一會兒,陪臣妾說會兒話再去看摺子,好麼?”
問鼎宮闕
問鼎宮闕
猜你喜歡
-
完結1159 章

慕南枝
前世,李謙肖想了當朝太後薑憲一輩子。今生,李謙卻覺得千裡相思不如軟玉在懷,把嘉南郡主薑憲先搶了再說……PS:重要的事說三遍。這是女主重生文,這是女主重生文,這是女主重生文。
220.9萬字8 26428 -
完結226 章

首輔大人的白月光是我
尹湄剛到京城時,做了一場噩夢。夢中她被太子看上,陰鷙殘忍的太子將她當做玩物,她不堪折辱自盡而亡。眼看夢境一一實現,尹湄拼盡全力自救。★一場春日宴,宴中哥哥設局,將她獻給太子。尹湄記起這日來了不少權貴,包括首輔大人和瑞王。首輔大人沈云疏雖是新貴權臣,可傳聞他心狠手辣不近女色,恐怕難以依仗。瑞王溫和有禮寬以待人,是個不錯的選擇。尹湄好不容易尋到瑞王,可藥性忽然發作,她誤打誤撞跌進了一個人懷里。他松形鶴骨,身量頗高,單手桎住她宛如鐵索,“姑娘身子有異,可需幫忙。”“謝,謝謝大人,您真是良善之人。”“……”等到她醒來,看著身邊躺著那位朝中如日中天的權臣沈云疏,哭紅了眼,“不是這麼幫……”不是不近女色嗎?★新任首輔沈云疏在官場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心思深沉,人人畏之,卻討好無門,不知其所好。無人知曉他已重活一世。他仍記得上一世,太子邀他入府觀看“美景”,見尹家那位雪膚花貌的美人被太子鎖在金子鑄成的床上,滿身血痕、雙眸無光。待他終于手刃太子大權在握時,卻聽聞她自盡于東宮,香消玉殞。這一世,他顧不得什麼禮法人倫,在她身邊織了一張大網,只靜待她掉入陷阱。心機白切黑深情首輔X嬌軟可愛有點遲鈍的求生欲美人
34.3萬字8.18 44444 -
完結179 章

世子寵妻錄
林紈前世的夫君顧粲,是她少時愛慕之人,顧粲雖待她極好,卻不愛她。 上一世,顧家生變,顧粲從矜貴世子淪爲階下囚。林紈耗其所能,保下顧粲之命,自己卻落得個香消玉殞的下場。 雪地被鮮血暈染一片,顧粲抱着沒了氣息的她雙目泛紅:“我並非無心,若有來生,我定要重娶你爲妻。” 重生後,林紈身爲平遠軍侯最寵愛的嫡長孫女,又是及榮華於一身的當朝翁主,爲自己定下了兩個目標—— 一是:再不要把一手好牌打爛。 二是:不要與前世之夫顧粲有任何牽扯。 卻沒成想,在帝都一衆貴女心中,容止若神祇的鎮北世子顧粲,竟又成了她的枕邊人,要用一生護她安穩無虞。 * 前世不屑沾染權術,不願涉入朝堂紛爭的顧粲,卻成了帝都人人怖畏的玉面閻羅。 年紀尚輕便成了當朝最有權勢的重臣,又是曾權傾朝野的鎮北王的唯一嫡子。 帝都諸人皆知的是,這位狠辣鐵面的鎮北世子,其實是個愛妻如命的情種。 小劇場: 大婚之夜,嬿婉及良時,那個陰鬱淡漠到有些面癱的男人將林紈擁入了懷中。 林紈覺出那人醉的不輕,正欲掙脫其懷時,顧粲卻突然輕聲低喃:“紈紈,爲夫該怎樣愛你?”
28.6萬字8 16229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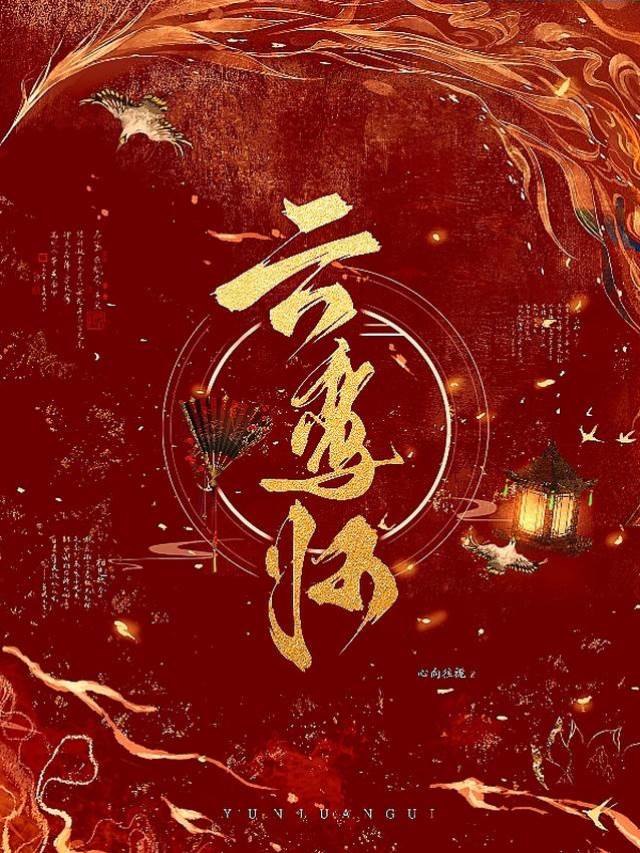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