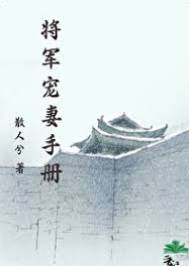《問鼎宮闕》 第70章 大選
幾日後,便是除夕。
百與藩王都照例京覲見,覃西王也到了。依著蘇氏鬧事的時間算,他該是離京城不遠時接到的申斥的摺子。於是在京當日,就上折做了辯解。
那日是臘月二十九,賀玄時沒什麼事,就把寧沅到紫宸殿查了一番功課。
說是查功課,但其實因為過年,也並不算多麼嚴厲。寧沅背文章有些記不住的地方他提醒一下也就過去了,答得好的問題倒都有賞。
平時查功課可鮮見他這麼好說話,是以寧沅被考得歡天喜地。
夏雲姒坐在一旁,邊吃著燉燕窩邊笑看眼前的父慈子孝,一時竟真有愜意油然而生。
在將那碗燕窩用完時,樊應德捧著一摞摺子進了殿。明天就是除夕了,這個時候摞呈進來的摺子通常都是京員的問安折,賀玄時便隨口道:“先放著,朕初二再看。”
樊應德卻躬:“皇上,最上頭這本是覃西王殿下的。”
夏雲姒眉心一蹙,皇帝神亦是一頓。
將手裡查問功課的書還給寧沅,他跟夏雲姒說:“你來看吧,說給朕就是。”
夏雲姒便上前將那本摺子拿了起來,餘下的由樊應德原樣捧走。
拿起摺子,翻了個大概。
頭一頁都是問安的話,過年問安也就那麼些詞,看不出什麼花來。
後麵就是解釋蘇氏所言之事了。
夏雲姒原以為宗親被皇帝申斥,無論如何也要告個罪,結果竟沒有。
覃西王隻是辯解說從未有過那樣的事,自己更不曾授意過貴妃與昭妃什麼,昭妃所言俱是胡言語。
用詞慷慨激昂,端得是義正辭嚴。
將這些一句句念給皇帝聽,皇帝聽罷沉良久。
“皇上?”終是喚了他一聲。
他喟嘆著搖頭:“上元之後,朕會賜死蘇氏。”
Advertisement
也就是這樣了。
即便蘇氏那日突然求見說出那樣的話聽來實在不像是編的,但在讀了覃西王所言之後,就料到是這樣的結果。
說到底,佳惠皇後已故、蘇氏又是廢妃之。不論他們的兄弟之是真也好、是假也罷,為了這樣的事對覃西王步步都沒有道理。
最無傷大雅的辦法,就是將蘇氏推出去。
於是在正月十六晌午,蘇氏沒了命。
昔日寵冠六宮的昭妃娘娘,最終就這樣伴著一卷草蓆長眠地下了,比采苓的下場還不如。
平日裡並不太額外召見嬪妃的順妃為此專門召集了六宮,聲俱厲地告誡眾人,若再什麼糊塗心思,蘇氏的下場便是們日後的下場。
但不論蘇氏從前是如何的叱吒風雲、這般死去如何令人唏噓慨嘆,這慨嘆也都不會持續太久。
——再過幾個月,便又是大選的時候了。
新一屆正值妙齡、如花似玉的家人子很快就會進宮來填補這幾年故嬪妃的空缺,誰還會在意一個罪人是如何下葬的?
是以在二月末,太後的旨意傳遍六宮。趕在新人宮之前,將六宮嬪妃大封了一遍。
位列九嬪之首的許昭儀位晉正二品妃,賜號為莊。
夏雲姒自從三品充華晉至正三品婕妤,老資歷的宋充華與儀貴姬亦位晉婕妤;還有位婉貴姬,晉至充華。
燕貴姬憑著養在膝下的皇次子一躍從正四品晉從二品九嬪之列,日後便該稱燕修容了。
隻不過,修容是九嬪之中最末的一個,這其中是否含著皇帝對皇次子的不滿,旨意中自不會明說,留待眾人細品。
除卻一乾主位,位份較低的嬪妃中也有不得了晉位。
周妙自從五品人晉至從四品姬,封號是一個字。
Advertisement
唐蘭芝位晉一例,至正五品宣儀。
當中隔了幾位夏雲姒不太相的,再往後看含玉自從七品經娥晉至了從六品寶林。
這旨意不免令含玉喜極而泣,又唏噓不已:“真沒想到,我也還有能位至寶林的一天。”
夏雲姒嗔道:“沒誌氣。這才寶林罷了,早晚能到貴姬當個主位的!”
三月末,家人子名冊呈進了宮。
名冊照例是謄抄三份,太後、皇帝與掌權宮妃皆要過目,賀玄時一如既往地沒心思看,便揮手讓樊應德退下。
轉過,卻見坐在案邊的夏雲姒脊背得筆直,緒顯而易見。
他嗤聲而笑,又揚音一喚:“樊應德!”
剛退到殿門邊的樊應德忙停住腳,隻見皇帝招手:“拿回來,給婕妤看看。”
“諾。”樊應德躬,夏雲姒辨出皇帝語中的嘲笑,雙頰一紅:“臣妾看它做什麼!”
說話間,樊應德已將那厚厚一摞名冊呈到了麵前。一翻眼睛,並不接,皇帝踱過去,拿起一本拍在額上:“快看,家世也好名字也罷,有你瞧著不順眼的便先劃了。免得人家進了宮,你又醋壇子打翻。”
“……臣妾哪有那樣善妒!”眸怒瞪,他更加滿目好笑:“沒有比你更會妒的了。”
“嘁……”不滿地翻翻眼睛,不理他也不施禮,起就賭著氣走了。
素來都是這樣。
嬪妃們大多對他過於恭敬。可過於恭敬了,往往更會教人不當回事。
自在一些,才能維持住初時想要的那種覺,讓他覺得並不好拿。
兩個月後,這摞厚厚的名冊減到隻剩三。
餘下的這三,便是要宮殿選的了。
“時間過得可真快。”在殿選的吉日定下來的那天,夏雲姒第一次慨起了時,“我還記得自己殿選那日的景呢,這一眨眼的工夫倒已過了三年,真是可怕。”
Advertisement
莊妃坐在榻桌一側,手裡繡著一隻香囊。聽到這樣說,不笑了聲:“你這話說的……我陪大小姐慕王府那日的景也還歷歷在目呢。日子都是這般一天天過的,有什麼可怕?”
確實,宮裡不就是這樣?
人去人來,花謝花開。
一茬人老去或者離世,轉眼就會有一批新的補進來。不論皇帝活到怎樣的歲數,後宮裡都仍能百花爭奇。
然夏雲姒搖搖頭:“我隻是怕自己老去太快,達不心中所想,便已走到盡頭了。”
莊妃抬頭看,靜靜地看了半晌,斷然搖頭:“不會。”
夏雲姒微挑淡笑:“娘娘倒對我很有信心?”
莊妃長嘆:“新人有新人的好,可你有你的本事。”
頓聲片刻,神黯淡了些,又說:“我有時會想,皇後孃娘若有你的三分心計,是不是就能活到現在了。”
夏雲姒沉默以對。
曾也這樣想過,為姐姐的早逝傷心難過之餘,也懊惱於的純善。
可這樣想多讓人失?姐姐是個善人,早早的香消玉殞;並不善,卻順風順水、風無限。
世間原不該是這樣。
一如三年前一樣,殿選在六月末舉行。
皇帝也照例沒心思親臨,給順妃與莊妃同去辦。
這一日,滿後宮都盯著毓秀宮的靜,夏雲姒心中亦不太安生。
到了傍晚,殿選終於結束,便徑直去慶玉宮求見了莊妃,周妙與不謀而合,前後腳進的瑜芳殿。
“坐吧。”莊妃勞了一整日,剛歇下腳,邊喝著茶邊請們坐。
周妙一落座便問:“如何,這次可有十分出挑的新宮嬪麼?”
莊妃直截了當地點頭:“有。”
二人俱是神一。
莊妃輕嘆:“我與順妃共是留了五人的牌子,餘下四位都還好,隻有位葉氏……當真是傾國之。一進殿,我們便都愣了一愣。”
Advertisement
後宮從不缺人,饒是莊妃與順妃都不算容貌多麼出挑的,也都稱得上一聲貌,更見多了旁的人。
能讓們有這樣的反應,那便是真的“傾國之”了。
而偏偏是這樣的人,們奉旨去殿選的反倒不好強撂了的牌子。若不然訊息總免不了傳出去,就算皇帝不在意,對名聲也終究不好。
周妙重重嘆息,可見滿是愁緒。夏雲姒倒不甚在意,一來原也姿不差,二來,在這後宮之中又原也不是姿頂尖兒。
既然得寵原也不是全憑姿容,當下又何必太為這些勞心傷神?
隻又問莊妃:“可還有覃西一地的家人子選麼?”
莊妃搖頭:“全撂了牌子了。多是順妃做的主,我瞧著,倒像是皇上私下授意過。”
這便好,夏雲姒微微鬆了口氣。
新人宮是大事,可這事再大,在看來也不敵覃西王的事更值得掛心。
蘇氏當日所言絕非子虛烏有,雖然皇帝不信,可覃西王那邊不是信了、便是以此為說辭要謀奪什麼。
如此這般,如果覃西王借著大選再送進來幾個人兒,那便必定對不利。
如今覃西一地來的都被撂了牌子,倒令久懸的心放下了些。
若這真是皇帝授意的,那就更好。
三日之後,新的冊封旨意下至各宮。
莊妃所說的葉氏名喚淩霜,乃是此番大選中封得最高的,與三年前的夏雲姒一樣,封的才人。
除此之外還有位趙氏,今年才十五,但因是戶部尚書的兒,可謂家世極好,便也封了才人。
此外的三位位份就不高了。
一位鄭氏封的是正七品經娥、一位尹氏封的正八品淑。還有位裴氏隻封了從八品,已是大選時能封的最低的位份。
新宮嬪仍是在五日後宮,照例先到掌事宮妃拜見各宮嬪妃。
這日夏雲姒自是按品大妝,與一眾嬪妃一併看著新宮嬪向順妃叩拜。
有那麼一瞬,有那麼點恍惚。
彷彿看到三年前的自己。
問鼎宮闕
問鼎宮闕
猜你喜歡
-
完結224 章

吾妹千秋
照微隨母改嫁入祁家,祁家一對兄妹曾很不待見她。 她因性子頑劣桀驁,捱過兄長祁令瞻不少戒尺。 新婚不久天子暴斃,她成爲衆矢之的。 祁令瞻終於肯對她好一些,擁四歲太子即位,挾之以令諸侯;扶她做太后,跪呼娘娘千秋。 他們這對兄妹,權攝廟堂內外,位極無冕之王。 春時已至,擺脫了生死困境、日子越過越舒暢的照微,想起自己蹉跎二十歲,竟還是個姑娘。 曾經的竹馬今爲定北將軍,侍奉的宦官亦清秀可人,更有新科狀元賞心悅目,個個口恭體順。 照微心中起意,宣人夤夜入宮,對席長談。 宮燈熠熠,花影搖搖,照微手提金縷鞋,輕輕推開門。 卻見室內之人端坐太師椅間,旁邊擱着一把檀木戒尺。 她那已爲太傅、日理萬機的兄長,如幼時逮她偷偷出府一樣,在這裏守株待兔。 祁令瞻緩緩起身,握着戒尺朝她走來,似笑非笑。 “娘娘該不會以爲,臣這麼多年,都是在爲他人作嫁衣裳吧?”
34.6萬字8 3604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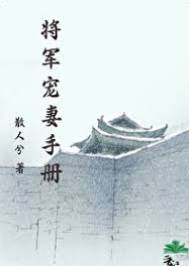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13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