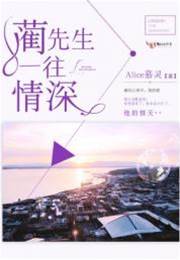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以愛情以時光》 第884章 愛你,永遠比別人多24小時
在毒的方面,駱向東跟紀貫新這麼些年一直半斤八兩難分高下,但是說到哄人開心。兩人本不是一個風格。
除了樑子衿之外。這些年駱向東也沒認真哄過別人,奈何他送個花送個禮,一幫人已經覺得自己被寵上天了。
到了樑子衿這兒。他也確實是實心實意。什麼都願意給,但這並不代表他有多浪漫。最起碼。對比紀貫新而言,駱向東心底暗罵了他十萬八千回。臭顯擺。
樑子衿不是羨慕路瑤,只是羨慕這世上有個男人能對自己的老婆這麼好。所以在駱向東面前嘀咕了幾句。駱向東就不了了,正好在國的事忙完,他直接助理訂了飛爾蘭的機票。
樑子衿私下裡也有跟路瑤聯繫。路瑤會把婚紗照的原圖發給樑子衿看。當駱向東這頭確定他們隔天會飛爾蘭之後。樑子衿興的給路瑤打了個電話,說是他們也要過去。
可路瑤卻失的道:“子衿姐。你早說啊,我們剛訂了明天晚上去國的機票。”
樑子衿也是又驚訝又失落。“啊?你們要來國?我們現在就在國呢,這麼說咱們不是又要錯開了?”
路瑤道:“是啊,要不我們去國找你們也好。”
樑子衿道:“我是看見新聞說你們在爾蘭領了結婚證,我也想跟向東過去領一份,那邊好玩兒嗎?”
路瑤說:“好玩兒的,你們來了之後可以去多克教堂……”
兩個人有了共同語言,聊起來沒完沒了。另一邊,駱向東給紀貫新打了個電話,紀貫新接通之後,‘喂’了一聲。
駱向東一張俊的臉上沒有任何表,語氣卻是挑釁的,他說:“結個婚而已,用不用搞得全世界都知道?”
Advertisement
紀貫新聞言,嗤笑著回道:“花你家錢還是佔你家地方了?”心也不怕爛肺子。
駱向東說:“結婚是兩個人的事兒,小心做太過,就有秀的嫌疑了。”
紀貫新‘哼’了一聲,然後道:“你沒病吧?半宿半夜打電話過來,就是想讓我罵你兩句的?”
駱向東嫌棄的回道:“我跟子衿明天去爾蘭,看看那邊的結婚證到底比國的金貴多。”
紀貫新拖長聲‘哦’了一句,“你這態度不是不爽我,是不爽要帶子衿來爾蘭是吧?那行,我待會兒幫你勸勸,就說你不樂意來,彆強迫你。畢竟嘛,老公跟老公不同,誰讓當初沒戴眼鏡看上你了呢?”
紀貫新損起人來眼睛都不眨一下,明知道駱向東不是這個意思,偏要往他上潑髒水。
駱向東聞言,立馬不甘示弱的回擊,“你用不著在這兒吃不著葡萄嫌葡萄酸,我老婆戴不戴眼鏡也不會看上你,這點你心裡比誰都清楚。新婚燕爾的,注意點兒你邊的人,別跟往事兒過不去。”
倆人一個比一個毒,還句句暗藏玄機,一個回覆不好,就容易給自己整裡去。
駱向東話音落下,紀貫新立馬嘲諷的回道:“說誰跟往事兒過不去呢?我老婆年輕又漂亮,溫又賢惠,啊,我最喜歡也最不喜歡的一點,就是太聽話,沒轍。”
駱向東哼了一聲,“老牛吃草還偏說的這麼不要臉,好歹也三十四歲的人了,膝下連個一兒半的都沒有,就算是老來得子,你這年齡也過了點兒吧?”
雖然駱向東這話是開玩笑,而且紀貫新知道他一點兒惡意都沒有,就是毒,可心裡,還是難免一痛。
Advertisement
路瑤的近期都不適合孕,不然他能憋到現在還不給個孩子?
只是這個中緣由,他不方便跟別人講,所以也只是稍微一頓,隨即打哈哈似的回道:“駱向東,你給我等著,別以爲你一對雙胞胎兒子就有多了不起,再了不起,也架不住子衿不給你生二胎的機會,你這輩子註定沒有兒命。”
說罷,他又換上得意洋洋的口吻,兀自炫耀似的說:“我就不一樣了,我爸連我兒的名字都想好了。瑤瑤也喜歡孩子,等我倆結婚之後,三年抱倆,到時候你就等著哭去吧。”
紀貫新也到了駱向東的痛點,他沉聲回道:“大話先別說的這麼早,等你三年抱倆再說吧,生不生的出兒還不一定呢。”
紀貫新道:“反正不用你出力。”
駱向東臉更臭,直接掛斷了電話。
其實他給紀貫新打電話,無外乎是想表達一下對他新婚的‘祝賀’,用這樣的方式,紀貫新應該可以收到吧?
路瑤跟紀貫新在爾蘭修整好之後,又專門包機帶著一衆工作人員,直飛國。他們這次要去的地方,是費爾班克斯。
如果說土耳其的藍礁湖是世界上最的海灘之一,那麼費爾班克斯,就是地球上最妙的地方之最。
這裡緯度極高,是北最接近北極圈的主要城市之一,擁有世間罕見的極晝和極夜現象,冬季更是常見北極。
如今正是三月初,北極活積極的月份,只要來這裡住上三晚,百分百的可能會看見北極。
路瑤已經先後被紀貫新給了兩次,以爲如此高的起aa點,再往後,可能沒什麼會讓太心的了。但還是低估了紀貫新送給的驚喜,只要他願意,他能分分鐘讓開心到跳起來,也能讓心到流淚。
Advertisement
路瑤永遠都不會忘記,當一行人從費爾班克斯的機場出來之時,整個天空全都是藍綠的,中間夾雜著濃淡調和到極其的淡黃和淺紫。
很多的隨行工作人員,都是沒有親眼見過北極的。在如此炫的天空之下,一衆人直接站在機場門口,走不路了。
路瑤更是忍不住手捂住,一張漂亮的臉上映照著奼紫嫣紅的斑斕彩。
太了,得令人無法呼吸,更無法用語言去形容。
紀貫新攬著的肩膀,見黑的瞳孔中泛著晶亮,竟是比天空中的星星還要璀璨。
習慣的手著的頭頂,紀貫新出聲說:“別哭,哭了就看不清楚了。”
路瑤聞言,果然瞪大了眼睛,這輩子第一次親眼見到北極,一分一秒都不願意錯過。
在機場門口站了能有十分鐘的樣子,紀貫新好笑的道:“別看了,它又不會馬上消失,先去住的地方。”
路瑤反覆認真的確定,“真的不會消失嗎?”
紀貫新‘嗯’了一聲,然後道:“頂多過幾個小時變個樣子,這裡的極能持續半年時間,不用怕。”
路瑤真想說,要不咱們以後都住在這兒吧,可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別說他們五月份就要結婚了,就算是定居,也不能爲了看景就來這麼個陌生又偏僻的國外城市。
忍住心底對這裡的嚮往,跟著紀貫新一塊兒上了機場門口早就等候的車子。
後有工作人員在興的聊天,都說謝藉著路瑤的,們才能看到這麼麗的景緻。
而路瑤則是看向邊的紀貫新,發自心的說了句:“貫新,謝謝你。”
紀貫新寵溺的看了一眼,故意的回道:“謝我幹嘛?哪有老公不寵媳婦的?”
Advertisement
兩人坐在私家車後座,路瑤第一次沒有顧忌車前還有司機在,不自的手抱住紀貫新,然後主揚起下,在他脣上狠狠地親了一口。
紀貫新順勢環住的腰,加深這個吻。路瑤只是想淺嘗輒止的,沒想到被紀貫新給後來者居上,他靈活的舌尖強的撬開的脣齒,吻得旁若無人,香豔無比。
路瑤想躲,可是紀貫新不許,愣是把吻得癱在懷裡,手去掐他,他這才鬆開。
車沒開燈,但是路瑤能想象到自己的臉有多紅。嗔怒的看了眼紀貫新,氣他這麼放aa。
紀貫新則是俊臉一側,直接用英文對著前排的司機說:“我老婆,我特別,一看見我就想親,這沒錯吧?”
司機從後視鏡中看了一眼,典型國人的做派,攤開一隻手,笑著回道:“當然沒錯,恭喜你們,新婚快樂。”
紀貫新重新側過頭來看路瑤,眼神中帶著幾抹得意和挑釁,那樣子像是說,他沒錯。
來了國外,路瑤也勸自己放開一點兒,一手跟紀貫新十指相扣,另一手攀著車窗邊緣,側頭往外看。
天空還是麗而炫目的,一條很亮的帶,像是被人給甩出去一般,從地平線直奔天際。
路瑤癡癡地著,心中想的是,願一輩子白首不分離。
“現在是極夜,這裡會有二十四小時的黑天,你願意看,待會兒我陪你躺在牀上從天窗看個夠。”
路瑤點點頭,應了一聲。
紀貫新看著弧度和的側臉,想到穿著婚紗的模樣,心中越發的。
手起耳邊的碎髮,他輕聲說:“我不知道天長地久,到底有多長多久,但是我希我對你的,永遠都比別人多二十四小時。”
猜你喜歡
-
連載1164 章
穿到跟殘疾大佬離婚前
遲清洛穿進一本狗血小說,成了商界殘疾大佬作天作地的小嬌妻。小嬌妻驕縱任性,飛揚跋扈,還紅杏出牆。遲清洛穿來當天,原主正因為爬了娛樂圈太子爺的床上了熱搜。大佬丈夫終於同意跟她離婚。遲清洛:“老公我愛你,之前跟你提離婚是我一時糊塗。”輪椅上的大佬眸色深沉:“你糊塗了很多次。”不不,從今開始,她要改邪歸正,渣女回頭金不換。可是漸漸的大佬好像變得不一樣了,對她說抱就抱,說親就親。嗯?大佬不是淡薄情愛,隻把她當擺設的麼?遲清洛眨眨眼:“好像有哪裡不對。”大佬將小嬌妻圈入懷中,指腹摩擦著她的唇珠,聲音嘶啞:“哪裡不對?”
104.7萬字8 56339 -
完結845 章

寵婚入骨
許家多年前送去鄉下養病的女兒許呦呦回來了,回來履行與林家的婚約婚禮前夕新郎逃婚去國外找他的白月光,眾人:哇哦……【吃瓜表情】許呦呦:哦豁。下一秒,白皙細軟的小手攥住男人的衣袖,甜糯糯的語調:“墨先生,您可以娶我嗎?”……墨深白商業巨擘清心寡欲,神秘低調,在波雲詭譎的商場叱吒十年,無一家報刊雜誌敢刊登他的一張照片,也沒有一個異性能讓他多看一眼。所有人都說墨深白娶許呦呦一定是協議婚姻,一年後絕對離婚。許呦呦津津有味的吃著自己的瓜,只是吃著吃著就發現好像不對勁啊。逛街購物不需要買單,吃飯不用點餐,不管走到哪里大家熱情跟她打招呼:墨太太好。後來墨深白的白月光回來了,前未婚夫深情表白:“呦呦,只有我是真的愛你,回我身邊,我不嫌棄你。”許呦呦還沒來得及回答被男人霸道的攬入懷中,低音性感撩人:“寶貝,你沒告訴他,這裡有了我們愛的結晶。”溫熱的大掌貼在她平坦的小腹上。許呦呦紅了臉,渣男紅了眼……【無腦瑪麗蘇先婚後愛文|專注虐男二】
142.9萬字8.18 230629 -
完結11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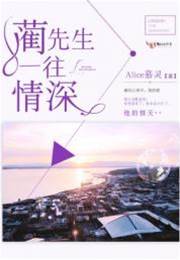
藺先生一往情深
曾有記者舉著話筒追問C市首富藺先生:“您在商界成就無數,時至今日,若論最感欣慰的,是什麼?” 被眾人簇擁,清俊尊貴的男子頓步,平日冷冽的眸難得微染溫色,回答:“失而複得。” - 人人都說她死了,藺先生心裡有一個名字,彆人不能提。 他走她走過的路,吃她喜歡吃的食物,人前風光無限,內心晦暗成疾。 情天眉眼寂淡:有些愛死了,就永遠不在了。 他眼眸卻儘是溫然笑意:沒關係,沒關係。 她的心再冷,他捂暖。 世人隻知商場中藺先生殺伐決斷手法冷酷,卻從不知,他能將一個人寵到那樣的地步。 - 但後來 人來人往的步行街頭,商賈首富藺先生仿若失魂之人,攔著過往行人一遍遍問—— “你們有冇有看到我的情天……” 他的情天,他的晴天。 · ·寵文·
138.8萬字8 78848 -
完結855 章

報告總裁,你老婆又跑了
黑暗中,他鉗住她的下巴,“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她自輕自賤“知道名字又如何?你只要一分不少的把錢打到我卡上就行了。” 本以為拿到錢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當一切沒有發生。 誰知那古怪男人從此卻陰魂不散的纏住了她。
167.7萬字8 38200 -
連載176 章

軍婚撩人:首長大人請深吻
她代替姐姐嫁給了那個據說身有隱疾的年輕軍長。他的寵,他的溫柔霸道,讓她毫無抵抗的臣服。卻原來爾婚我詐,不過是一段遠的要命的愛情。幾年後,她攜子歸來,撩撥的他欲火焚身。他反身把她壓在辦公桌上,“老婆,按照一夜七次的頻率來算,你已經欠我很多了,要不咱們還是先還債吧!”
30.5萬字8 2625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