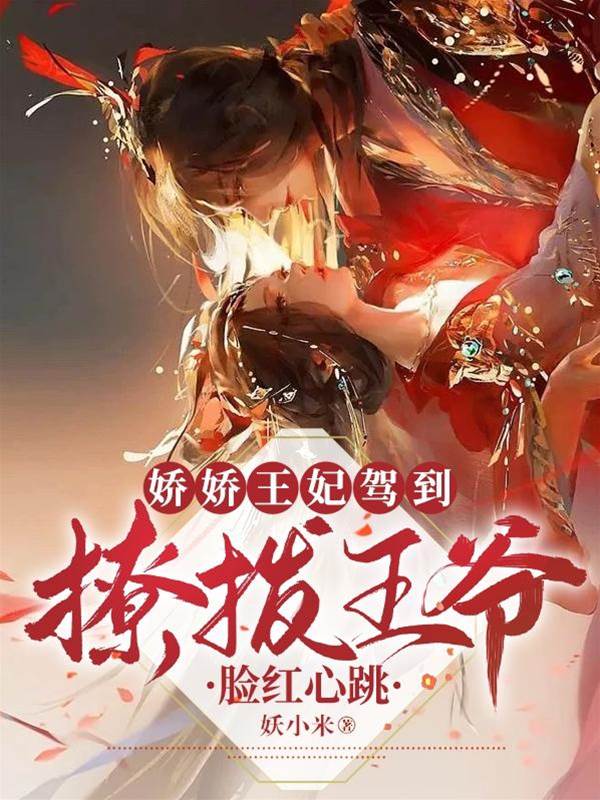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咬定卿卿不放松》 第96章 096
但他還是晚了一步,的舌尖已經到了他。
陸時卿驚得幾乎提鼠竄了去,幸虧元賜嫻反應快,及時松了手,才沒把他折斷。
經此一嚇,原本備足的勇氣都被他竄沒了,回味起方才一瞬的古怪,有些惱地看他:“你就不能別一驚一乍的,我安安靜靜……”幫他辦了嘛。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這下好了,提不起勁了。
陸時卿腦袋里一遍遍閃過方才皓齒朱間,鮮滴的小舌冒頭的一幕,再回想短暫的一剎刺激,神痛苦地忍耐道:“你怎麼什麼都學……”
元賜嫻心道早先趁他不在家,把手邊陪嫁過來的避火圖都給翻爛了,什麼世面沒見過,只是到底對這事微有抵,才一直沒嘗試,剛剛見他火燒眉還一心顧念,一時容就起了心思。
結果反倒被他嫌了。
不太高興地撇撇:“那我不學就是了。”
陸時卿知道是誤會了,想跟解釋,無奈上火苗跳躥得厲害,實在憋不住,只好道:“等我會兒。”說罷還是轉頭疾步走向了凈房。
元賜嫻郁卒地點點頭,等了兩炷香才見他出來,倒是已然恢復了自若的神態。
看一臉憋屈,陸時卿上了床榻,撐著手肘明知故問:“怎麼了?”
元賜嫻到底不是藏心事的人,瞅著他道:“你不喜歡我學那些啊?”
“喜歡。”他默了默,拿拇指了的下,“但是不想你這樣。”
應該說,是不舍得這樣。
聽他語氣難得有點意的味道,元賜嫻大約明白了他拒絕的原因,道:“我又不覺得臟……”
“我知道。”
不過他只要知道就夠了。
悶悶地說了句“好吧”,手拉上了被褥,等闔上眼卻到邊人湊了過來,在耳邊低低道:“如果真想來,也該是我先。”
Advertisement
“……”
元賜嫻懂了他話中深意,不由得渾一抖,隨即聽他好整以暇地問:“你抖什麼?”
咬咬牙擰一下他的胳膊:“誰抖了?是胎,胎!”
陸時卿“哦”了一聲,下。
好大一下胎啊。
這一夜雖相安無事,元賜嫻的舉卻到底在陸時卿心底投了漣漪,他愈發沒了從前的架子,就是一心想對好,往死里好。
等過了幾日,著休沐,他在書房辦公,聽仆役說元賜嫻正人備水,想趁白日暖和,不易涼沐個發,便下人們帶話去,在庭院里等他給洗。
陸時卿將公事結了,收拾起桌案上一疊要文書,正準備出時,忽聽道那頭傳來了三下叩門聲,便停下步子,轉開啟了機關,果見暗門那頭來了鄭濯。
此前蔡禾遭難,為免平王對假徐善的份起疑,這條道一度廢置許久,直到后來危機消解,才重又被倆人用了起來。
陸時卿惦記著元賜嫻,語速便有些快:“我難得休沐一日,你還來串門?”
鄭濯被他這開門見山的不善口氣說得一噎,朝他后看了看,問道:“怎麼,我擾你好事了?”
他現在能有什麼好事可做啊,招呼他進來后道:“好事倒是沒有,就是在等我給沐發。”
鄭濯聞言差點腳下一絆,驚道:“你家婢都領完工錢散了?”
陸時卿瞥瞥他,淡淡道:“你懂什麼。”
這夫妻趣。他近來新學的。
鄭濯心道他這孤寡老人可能的確不懂了,府上幾名被徽寧帝塞來的姬妾不是花瓶子就是監視他的耳目,也不值他費什麼心思。
他想了想道:“那你先去忙吧,別等急了。”
Advertisement
陸時卿聽了前半句還覺他善解人意,等他說完,心里就不是那麼舒坦了。怎麼,他很關心元賜嫻?
見他臉上起了霜氣,鄭濯便曉得了他在想什麼,拍了下他的肩膀:“我關心我干兒子。”
陸時卿“嗤”他一聲。
誰說他兒子要認他做干爹了?再說了,他怎麼知道一定是兒子?
他覷他一眼,到底知道他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必然帶了什麼消息,問道:“消息要不要,等兩炷香不會死人的話,我就先去了。”
鄭濯失笑:“死不了,我在這里等你,給我上壺茶,要夠味的,再把五木拿出來,我一個人也好打發打發時辰。”
陸時卿無奈看他一眼。好端端一個正經皇子,偏喜歡賭戲。卻到底把茶和五木都給了他,然后才繞到屋后庭院找元賜嫻。
元賜嫻不曉得鄭濯來訪,見陸時卿磨蹭半天才來,坐在廊下怨道:“你再不來,我自己都能洗好了!”
陸時卿低咳一聲,回頭看了眼書房的后窗,也不知道里頭鄭濯有沒有聽見這種掉他臉皮的話,道:“有點事耽擱了。”
也就沒再多怨,問道:“做什麼在庭院里洗?”
他指了下天邊懸日:“天氣好,曬曬太。”說完招呼到天井,“來。”
元賜嫻也的確不喜歡悶在屋里,難得十一月里上如此暖和的天,出了廊子曬到太,便覺整個人舒暢無比,脾氣也沒了,笑盈盈地在仆役事先備好的人椅上躺了下來。
陸時卿繞到長椅后邊,拆了頭上的簪子,一手松散的長發,一手拿起一個水瓢。
元賜嫻貓似的瞇著眼,懶懶提醒道:“我頭發很臟了。”
因為天冷,陸時卿怕在這當頭涼,便不給經常沐浴。頭發臟一點,他也不在意,夜里照樣靠靠得起勁。
Advertisement
陸時卿輕輕撓了下的頭皮:“知道。”卻也毫沒有停手的意思。
元賜嫻心道真是一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啊,花了一年不到的功夫把陸時卿弄到手,就能得他接下來三五十年的伺候,實在太劃算。
陸時卿不曉得在想什麼,但看角上揚,一副心滿意足的模樣,心底竟也覺這清閑日子當真舒坦,忍不住跟著一笑,邊從水桶里舀起一瓢差人濾好的皂莢水,給發,邊問:“涼嗎?”
元賜嫻閉著眼搖搖頭:“剛好。”
幾瓢水下去后,他就開始給發了,興許是他的力道恰好,加上日頭曬的,元賜嫻很快有了困意,迷迷糊糊道:“要是我睡著了,就把我抱回去,小心著孩子。”
陸時卿手上作不停,淡笑道:“你不怕著我?”
元賜嫻一下就給氣清醒了,睜眼質問道:“你嫌我重?”
他還沒來得及答,就先見一癟:“我辛辛苦苦懷胎十月是為了誰?現在倒好,段也走樣了,臉也生了橫,竟被這要當爹的嫌棄……”
陸時卿一看就知是好久不演戲,心里了,扯了下角道:“我要是嫌棄你,誰給我生下一胎?”
“還貪,這都一次給你生太平了,合你心意湊了一雙!”元賜嫻腦袋一歪責他。
他把的頭擰回去:“別。”然后繼續道,“你要是生了一男一怎麼辦,我還是不舒服。”
“……”強詞奪理!
倆人扯著扯著就過了陸時卿跟鄭濯說好的時辰。虧得鄭濯原就是坐在了后窗邊,隔著鏤窗將庭院里的靜瞧得一清二楚,看他的確未洗完,也就沒著急,只是一個人玩五木到底無趣了點,便時不時抬頭看一眼他們。
Advertisement
他看庭院里種了兩株對稱的槐樹,葉子都落了,原本瞧上去有點蕭瑟,但被這仲冬的煦日一照,竟莫名蒸騰出幾分生機來,像籠了一片濃綠一般。
再看樹下鬧得起勁的倆人,元賜嫻似是被陸時卿氣著了,兩指一彈,將發間一點皂莢沫子彈到了他的鼻尖。
陸時卿中了招被氣笑,抬手想,卻像是因了滿手膩的皂莢,一時有點猶豫。
元賜嫻見狀,笑著從袖子里揀出一塊帕子,然后仰著脖子,長了手臂幫他輕輕一抹。
他約聽見說:“好了,不鬧你了。”
陸時卿便是一副苦大仇深卻忍氣吞聲的模樣,繼續給。
他看到這里收回了眼,低頭瞧著落在窗柩的淡金日照,抿一笑,眼底卻微微有幾分悵然之。
給人沐發,好像真是件有意思的事啊。
約莫再過一炷香,陸時卿才給元賜嫻洗完了發,拿手巾給拭了兩遍后道:“還不夠干,等會兒再人給你。”
元賜嫻回頭不爽利地瞅他:“人家送佛還送到西呢,你這半道就要丟了我啊!”
他無奈一笑:“時辰太久了,書房有人等我。”
“誰?”
他一指書房后窗,示意自己看。
元賜嫻順他所指去,就見鏤窗另一頭,鄭濯正坐在那里,抿著手中茶甌里的茶,察覺到的目,他偏過頭來,朝頷了頷首,淡淡一笑作招呼。
“……”
這麼大個皇子坐在不遠,卻大搖大擺躺著,這可了不得。元賜嫻下意識想把自己撐起來坐端正,卻見鄭濯打了個手勢,示意別了。
陸時卿也按住了:“你跟他客氣什麼。”
元賜嫻心道是他太不客氣了,早知鄭濯干等著,也不會耽擱他這麼久,沖他皺皺鼻子道:“你還不快去。”
陸時卿差人送回去,然后起回了書房,一眼看見鄭濯因庭院里來了下人,手腳利落地將窗子闔實,就朝他飛了個眼刀子道:“你倒挑了個好位置盯梢。”
鄭濯笑笑:“承蒙陸侍郎夸獎,不才兵法學得尚可。”
“說吧,什麼事?”
鄭濯這下不嬉笑了,斂道:“回鶻出事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82 章
九重華錦
重活一世,掩一身驚世才華,藏身鄉野,隻待時機報了血海深仇。奈何,小小農家也是好戲連臺。為了活命,免不得心狠手辣。麻煩解決,正想煮壺粗茶閑雲野鶴再做謀劃。莫名其妙,又成了什麼林家落魄的嫡小姐。這便也罷,竟將她配人。實在懶得理會,偏生的有人不知死活,隻好略施手段圖個清靜。沒成想,被人從頭到尾看了一場熱鬧。
274.2萬字8 71795 -
完結285 章

壞壞王爺溺寵絕色王妃
一朝穿越,竟然成了一個小萌寶的娘親,這是不是很驚悚的事情,不過沒關系,有什麼事情是能難得住我二十一世紀王牌特工的。 帶著萌寶出賣色相換取錢財的財迷娘親,打皇子,斗嫡妹,她玩的得心應手。 可是為什麼這個男人這麼的難對付,論腹黑等級,她甘拜下風,論不要臉的功力,她那是小巫見大巫。 “龍少辰,你信不信我現在就殺了你?” 某男手牽萌寶,笑得一臉狡黠,“娘子若是下得去手,舍得咱們寶貝沒有爹,那就……動手吧!” 且看腹黑穿越女如何帶著萌寶玩轉古代。
75.9萬字8 28616 -
完結287 章

重生后寒門醫妃被迫在京城搞內卷
她是侯府嫡女,本應在寵愛中長大,卻在出生時被仆人掉了包流落鄉間,養父母把她當牛馬,在榨干她最后的價值后,把她虐待致死。帶著空間重生歸來,她甩掉渣男,吊打白蓮花,脫離養父母,讓虐待她的人萬劫不復。當侯府接她回家時,她以為她終于可以感受到親情了,誰知侯府只是想讓她替養女嫁給瘸腿王爺。想讓她當瘸腿王妃?對不起,她醫術高明,轉身就治好了王爺的腿。想讓她在宮斗中活不過三集?不好意思,她勢力龐大,武力值爆表,反手就把對手拉下馬。想讓她和王爺沒有孩子?抱歉,王爺說他們要一胎二寶。可是,她想跟王爺說:“我們是...
53.3萬字8 48006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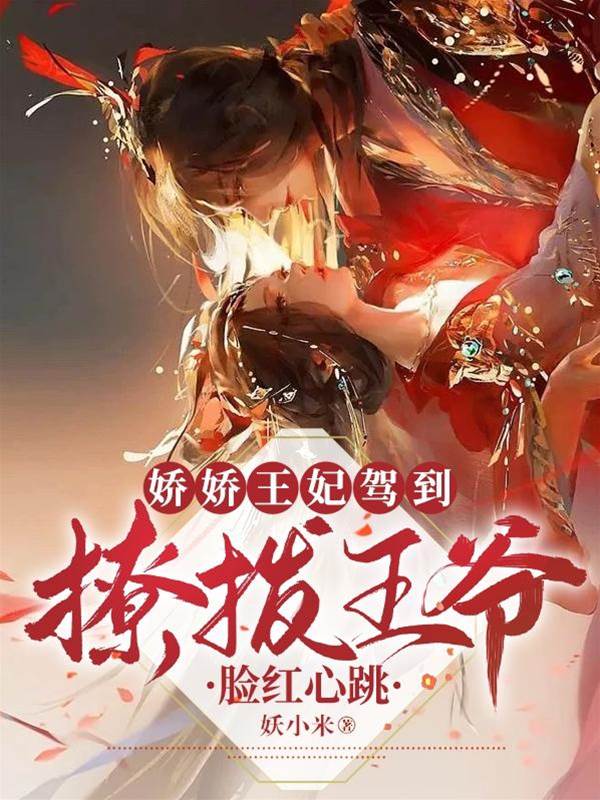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6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